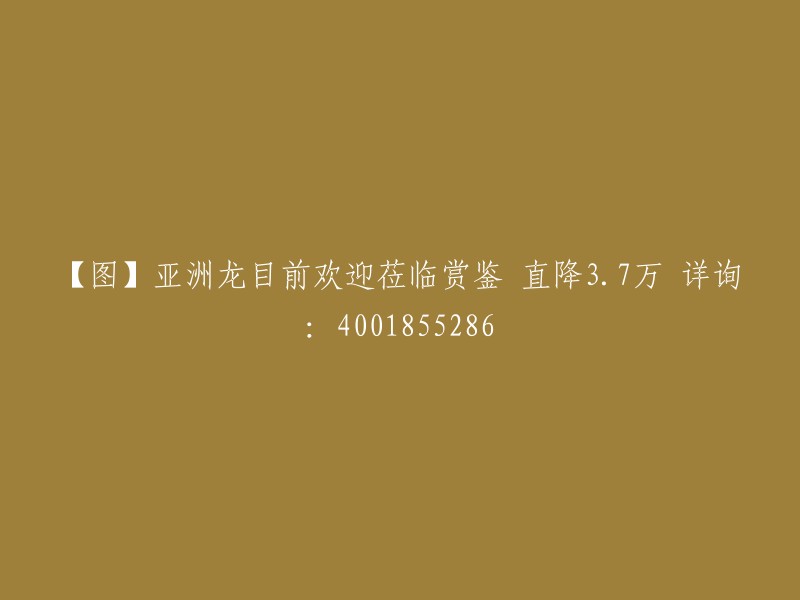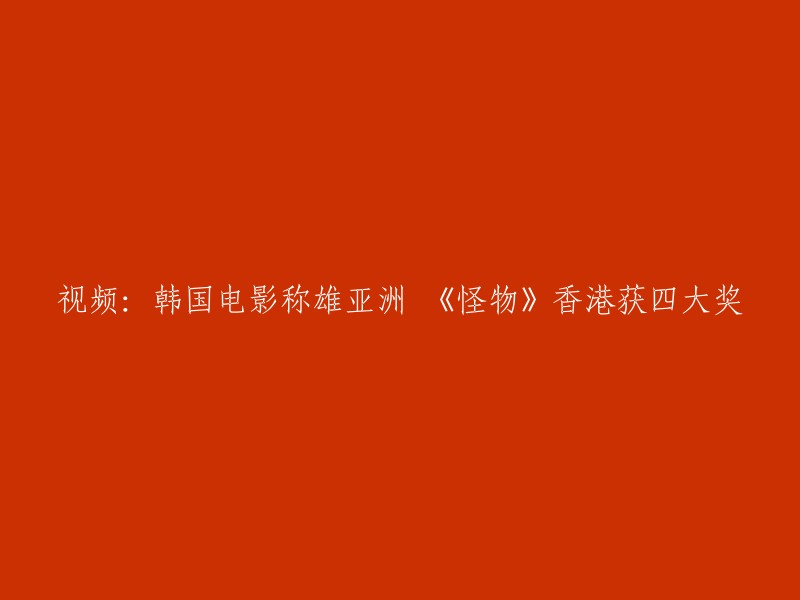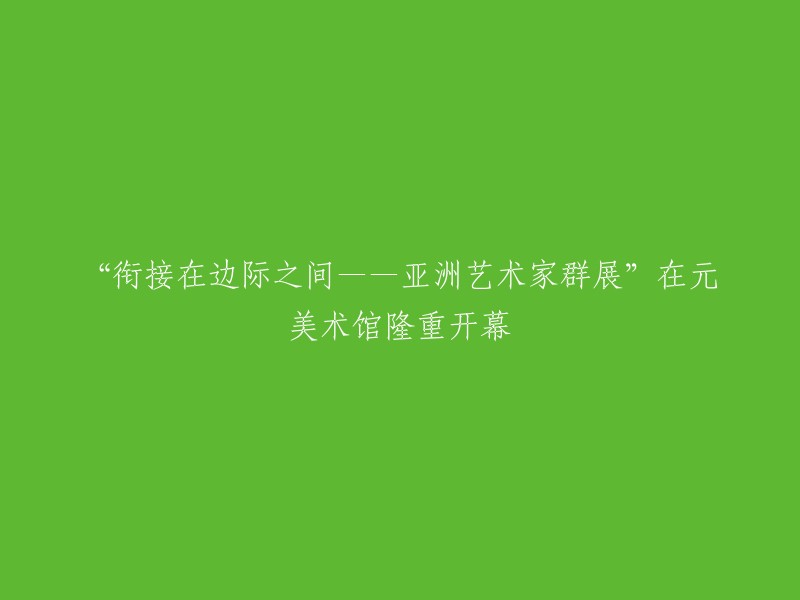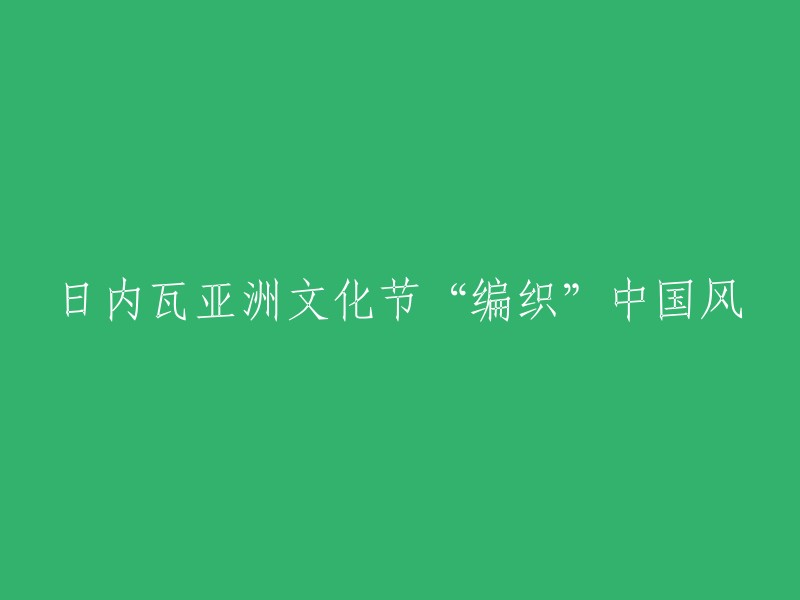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艾滋病三个字会与五叔联系起来。那时是1990年寒假的一天,我在家里对着火盆写作业,临近中午时,门外响起一串自行车的车铃声,我探头一看,是五叔和五婶。他们刚新婚不足十天。五叔高声喊道:“走吧,跟我们一起去镇上下馆子去。”听说要下馆子,我来了精神,不再怕冷,也不顾我妈的反对,迅速起身,朝门外奔去。
五婶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只得坐在前面的单杠上,硌是挺硌,但谁让我嘴馋,要跟着他们去下馆子呢。去往镇上的路,当时是条土路,坑坑洼洼,很是不平,有人无聊时数过,骑自行车的话,要历经大大小小500多次颠簸。行至半程,车子猛然一轻,速度快了许多,等我和五叔反应过来,回头一望,只见五婶从自行车后座上摔了下来,正狼狈坐在满地灰尘里。
五婶体态丰腴,臀部肉厚,不见得摔得有多疼,五叔还没从自行车上下去扶她,她已经追了上来,边拍打裤子上的灰尘边解释着说,头发盖住眼了,她就只是抬起双手拢了拢风吹乱的头发,谁知刚好是下坡,又遇上一道不浅的水沟,她就从车上被颠了下来。这事本该就此结束,可未曾想到,几分钟之后,五婶突然啜泣起来,后来干脆放声大哭,“真是倒霉到顶了,在家得不到好脸色,坐个自行车也要摔跟头。”
五叔只好停下自行车,对五婶进行劝说和安抚。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得知,五婶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她原本还是新媳妇,可奶奶从她嫁过来的第二天开始,就不停支使她干这干那。今天早上,她偷懒多睡了一会,起床后,发现五叔和奶奶已经吃过早饭了,她掀开锅一看,锅里是有饭的,只是已经加上了冷水。五叔心疼她,又怕没吃早饭的五婶,会被奶奶支使着做午饭,就带着她去镇上下馆子。
我起初以为,五叔五婶带上我一块去下馆子,是源于我可爱,或者是出于亲我疼我,后来才知道,我被他们“利用”了。五婶个子不高,龅牙,算不得漂亮,不过性格很温柔;绝对不傻,但看着也不算特别灵光,属于憨厚型的。五叔则五官比例不错,一米八出头的个子,显得风度翩翩。两人无论怎么看,都是五婶高攀了五叔。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在那个农村还是靠媒人介绍步入婚姻为主的年代,五叔五婶的自由恋爱,显得很新潮和不多见。
那天,我和五叔五婶三人,到小镇上后,五叔选了一家没有招牌的饭馆。他表示:“饭馆不在门面和装潢,好吃才是硬道理。我在镇上读初中时来这里吃过面条,味道在镇上的饭馆里是首屈一指。”
五叔先是点了三碗扯面,吃至一半时,狼吞虎咽的五婶说,她早饭没吃,等于是两顿饭合一顿,一碗面只能吃个半饱。五叔闻言站起身来,朝后厨走去。回来时,讨好地对五婶说,他还要了六个香喷喷的羊肉大包子,他本来想再点一份青椒炒肉的,可是店里只卖面条和包子,羊肉包子还在灶上蒸,要过一会才能端上桌。又说,镇上卖羊肉包子的只有这一家,味道好得没法形容。
直到我们吃光了面,又坐了一会,羊肉包子才姗姗来迟。我大约是吃饱了,并未觉得那羊肉包子有多好吃,皮厚馅少,而且不是纯羊肉的,还加了胡萝卜等,我讨厌胡萝卜的味道,于是吃了两口便不再吃。
五婶吃饭有些吧唧嘴,她心情早就由阴转晴,一边吃羊肉包子,一边用饱含幸福感的语气说,她长这么大,是第一次吃羊肉包子,以前在娘家都是吃馍,就连素菜包子都很少吃。还与五叔比起了谁嘴大,说她顶多四口,就能吃完一个羊肉包子。
五婶的话和吃相,带着穷酸和不体面,五叔却很受用,趁机冲五婶表决心,他以后会经常带五婶来这里下馆子。五婶好像不满足仅有这些,眼怀期待地说,她真想吃饭时坐在餐桌边,桌子上全是肉,有鱼、有鸡,还有红烧肉,而不是像现在的生活,端碗饭,里面放一筷子蔬菜或咸菜,随便找一个地方蹲着吃。
五叔听了,当即表示,他以后会努力挣钱,一定能让五婶过上富裕的生活,顿顿有肉吃。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五叔那时竟然身无分文,为了这次下馆子,他偷走了奶奶藏在棉絮里的钞票。等我们回去后,奶奶就冲着五叔五婶指桑骂槐地骂上了。
五叔护妻心切,却又不好直接顶撞奶奶,将我推到奶奶面前,冲奶奶说:“是你孙女嘴馋,非让我俩带她去下馆子的。”奶奶将信将疑,但没有再继续骂了。
至此我才恍然明白,五叔五婶之所以带着我一起下馆子,是拿我做挡箭牌呢。后来,我妈将五叔偷奶奶的钱,如数补给了奶奶。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也并未因此记恨五叔和五婶,每每想起这事,反倒觉得挺有趣。
二
当初,五叔和五婶的恋情,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奶奶的强烈反对。奶奶嫌弃五婶长得难看,说“嘴巴连牙齿都包不住,颧骨高得像锥子”,还说“娶坏一门亲,损坏三代人”。意思是五婶的长相,不仅克夫,还会拉低后代颜值。不过,因为五叔的坚持,依旧将五婶娶进了家门。
五叔和五婶结婚那天,虽然没有大摆宴席,来的都是亲戚,只有三桌客人。奶奶家的院子里临时垒了个土灶,上面摆着口大锅,在凉拌菜上桌的同时,掌厨的师傅抡着一把大铲,一锅锅热菜新鲜出炉,分装进盘中,接二连三地端上餐桌。我是过足了嘴瘾。
五婶因为是新娘子,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很少动筷子,就算是伸手去夹菜,也是夹一星半点,生怕给人留下贪吃和粗鲁的形象。不过,等到后来,五婶似乎又饿又馋,再也不愿意为了顾及新娘子的形象而矜持下去了,专挑荤菜,可劲往嘴巴里塞。
五婶大快朵颐的一幕被奶奶尽收眼底,奶奶走出院子,撇着嘴冲邻居老太太说:“宁要大家奴,不娶小家女,这话说得真是一点没错!”奶奶的话,我当时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后来特意让奶奶给我解释过。意思是说,娶妻子宁愿娶大户人家的丫鬟,也不要娶小户人家的闺女。因为大户人家的丫鬟跟着主人见过世面,从而显得大方和有教养,而小户人家的闺女,因为没见识,处处显得粗鲁,并且吃没吃相站没站相。很显然,奶奶是在讽刺五婶不顾自己当天是新娘的身份而大吃特吃。
其实奶奶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妇,但大约是因为爷爷在世时曾在县税务局上过班,还曾当过小学校长,而姑奶奶又是师范学院的老师,从而奶奶骨子里是有一份骄傲和高高在上之感的。
下馆子事情过去不久,奶奶就跟五叔五婶分了家,不在一个锅里吃饭了。五叔和五婶虽然文化水平都不高,却都是思想上有点文艺情调的人。五叔迪斯科跳得极好,还曾写过小说,在小说投稿全都泥牛入海之后,不再做文学梦,可是五婶却一直很爱看书。她似乎是故意想将自己与农村人区别开来,专门坐在临近马路的树林里看书,旁边还放着一杯茶。奶奶非常看不惯五婶装文化人的样子,背地里总说,她连书上的字都认不全,捧着书纯粹是偷懒,不想去地里干农活。
五叔有一把自制的猎枪,总是去山里打野兔。有一次打到野兔,五婶喊我去她家里吃。她厨艺不行,并将原因归咎于从小到大娘家太穷,没吃过什么好菜,自然也烧不出味道好的菜肴。所以,总是五叔下厨。五叔依旧爱吹牛,他总是说,等有一天他混得好了,当了董事长,就让我做总经理,五婶当他秘书。
五叔结婚前曾在湖南打过工,染上了吃辣的习惯,他做出的兔肉是麻辣味的,放了许多干辣椒。我以为有那么多干辣椒打底,会很麻辣,但是,并没有,那种辣度会使人有微微冒汗的感觉,但舌头却不会因为辣椒的侵袭而失去感知。野兔肉很有嚼劲,越嚼越香,吃多了也不腻。
五叔因为奶奶一直对五婶不满,所以对奶奶产生了怨言。有一次,他故意大声地说:“出去是挣大钱的,挣了钱,顿顿吃饭下馆子大口吃肉,谁还啃掉渣的馍。”这句话似乎是故意惹奶奶伤心。
后来,五叔和五婶离开了故乡,出去打工。临走时,奶奶给他们蒸了一锅白面馍,说那些馍敬过神,吃了可以保平安。可是没想到,五叔五婶的饭店一直门可罗雀,没过多久就关掉了。原来,他们借的钱全是用来开饭店的,而且连平日里为了维持生活也借了不少钱。那些债主以为五叔五婶躲起来了,生怕欠他们的钱成为空账,几乎每天都来讨债。我家也总是坐满了讨债的人。
我的父母不堪其扰,也心疼奶奶每天被讨债的人滋扰,就拿出积蓄替五叔五婶补上了窟窿。四年后,五叔五婶再度回到村子里。那天,我和奶奶早早在路口等他们。在我和奶奶的身旁还有几个闲来无事的邻居。
远远地,五叔五婶就冲我们招手,可脚步并未加快。他俩似乎是有意“轻装上阵”,随身挎包只有一个。待走到我们跟前,有人开玩笑道:“这包里装的都是钱吧?”五叔明知是玩笑话,却并不否认,笑着说:“大城市里的钱真好挣啊,你们瞅瞅我脚上的皮鞋,还有她身上这毛呢大衣,价格你们想都想不到......”
邻居们冲五叔五婶恭维几句便各自散去。五叔伪装得也很累,像是将要窒息的人,等邻居们走远后不由得长舒一口气。或许是不小心发现了五叔强颜的笑和假装的阔气,我心中难受,动动嘴唇想送他一抹笑,临了却又偏偏别过脸去生气地不去理他。
三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艾滋病三个字会与五叔联系起来。
镇上有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传言是艾滋病。而且人们还传言,我五叔也患上了艾滋病。事实证明,传言非虚。
后来我得知,五叔和五婶在外打工的那几年,因为吃不了工厂和工地的苦,打工总是时断时续,又遇到过不结工钱的事情,在走投无路时,五叔曾去地下非法血站卖过血,一个针头常常抽好几个人的血都不换。
镇上有一个人,就是传言因艾滋病而去世的那个人,也曾与五叔一起在那家地下非法采血点卖过血,他去世前曾与五叔见过一面,告诉五叔说,他十有八九是卖血时感染的艾滋病,并让五叔也去检测一下。五叔闻言,很震惊,提心吊胆地去做了检测,希望是漏网之鱼,可惜结果没有给他惊喜,也确诊感染了艾滋病。
那时人们背地里议论纷纷,说五婶肯定也感染上了艾滋病。
有一次我去看五叔,谈笑之间,午饭时间到了。五叔那时已经很瘦了,力气不足,免疫力低下,总是感冒,但还是起身步入厨房,烧了两个菜,一个是大葱炒鸡蛋,另一盘是油炸花生米。
鸡蛋很嫩,有酱香味。五叔似是有些抱歉,笑着说:“五叔家里穷,没有肉,加几滴酱油就算是闻着肉腥了。”
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却故意笑得很灿烂,跟五叔开玩笑,说等着他当董事长的那一天,我给他当总经理。他笑了,是真心的笑,就好像那样的日子并不遥远,伸手就可触及。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发现,五叔是一个热衷幻想的人,能够在被死神步步紧逼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时还心怀期待,尽管有好高骛远和盲目乐观之嫌,我依旧觉得他这点很可贵。
吃饭间,五婶说,看见我,就想起那年冬天,她和五叔以及我,去镇上下馆子的情形了。又说,那天的羊肉包子味道真不赖,她后来在别处又吃过几次,但总觉得那天的最好吃。
五叔接着五婶的话说道,当年在镇上卖扯面和羊肉包子的那个老板兼厨师早就去了市里,开了家更大的饭馆,想吃那天一模一样的羊肉包子,得去市里。
接下去,五叔五婶共同回忆着那天的羊肉包子,馅子里面都有什么。五叔说,里面除了有羊肉,还掺了胡萝卜、木耳和大葱。五婶则说,不对,没有大葱,有洋葱。五叔又笑着说,那羊肉包子里面不会加的有大烟壳吧?要不然为啥过去几年了,那味道咱俩还念念不忘?
五婶笑了笑,忽然用一种央求的语气说:“等你病好了,再带我去吃一次吧?”
五叔笑得很勉强,但还是郑重其事地答应五婶,一定带她再去吃一次。
趁着五叔去厕所的间隙,五婶冲我说:“我今天特意提一下羊肉包子,也不是非要吃那羊肉包子,当年穷,见个荤腥就觉得香。加上当时是你五叔第一次带我下馆子,心里甜蜜吃啥都觉得香。现在就算真吃到与当年一模一样的羊肉包子,可能也觉得就那样、很一般。我之所以非让你五叔带我再去吃一次,是让他觉得他还有未了之事。”
听着五婶的话,我心里微微震荡着,立即明白,五婶并非真的馋羊肉包子,而是想利用一个承诺,紧紧抓住五叔,让他留恋人间,与死神博弈。
“你五叔对我很好,当初我也想去卖血,他不让,说挣钱的事,还是得靠男人。”五婶说这话时,眼睛里带着泪意。
然而,五叔最终没能兑现他对五婶的承诺。而那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吃五叔做的饭菜。几个月之后,五叔身体每况愈下,浑身无力,躺在床上,无力下床,进食也越来越少,瘦得触目惊心。
五叔去世那年是1999年,那时一旦患上艾滋病,就意味着死亡。因为当年大家对此病了解不多,都十分忌讳这个病,生怕离得近了,就会被感染,几乎无人来吊唁,没有任何葬礼仪式,就匆匆下葬了。
五叔去世两年后,五婶去了外地,随后听说,她和一个男的结婚了。不过几年之后,五婶又回到了村子里,听说遇人不淑,那男的只是拿她当免费的保姆,没有领结婚证,也不给她钱。
可是,村子里五婶是不能住了,当年她和五叔住的房子,已经倒掉了。听说五婶站在一地废墟前,静静看了许久,谁也不知道她当时心里刮着怎样的风暴。
五婶回了娘家,住在她弟弟提供的一间房子里,租金每月五百,听说日子一直过得拮据。我一直想去看看她,但听说她作风一直不够好,明里暗里,与好几个男人有染。虽然我尽力说服自己,她和五叔已是过去式,如今怎么生活,是她自己的选择,内心里却隐隐有一种不舒服,觉得她这明摆着是堕落了。
四
再度见到五婶,是2016年,在我奶奶的葬礼上。她脸上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站在人群中,不停地抖着腿,我的叔叔和姑姑们,给她好几个白眼,可她依旧故我,仿佛是有意想气气大家。
本来按照当地风俗,老人去世后一个月,要办丧宴,宴请宾客。因为亲戚以及家人们几乎全在外地工作,不方便总是请假,所以丧宴提前了,就在奶奶下葬后的第三天举行。
人来得很多,但只准备了十桌,因此许多客人都被劝回。原本席位就不够坐,可五婶却独自占了一个位置,吃得很尽兴。下午四点多时,客人陆续离去,我坐在屋里听到外面的争吵声,出门一看,见五婶和姑姑怒目而视,正在争吵着什么。后来从她们的争执中得知事情经过——五婶全程都在吃,吃完了还将剩下的菜打包带走,令姑姑很不满。
“又吃又拿的,成什么样子!你心里恨老太太是吧?你知不知道老太太临死前还在念叨你,担心你命苦遭罪!”姑姑说道。随后,四叔和四婶也加入到谴责五婶的队伍中来。五婶哑口无言,倔强地站了一会,依旧拎着几兜剩菜离去了。
那天晚上十点钟的火车,我想去奶奶的墓地跟她告别一声。人至中年,习惯了奶奶的存在,突然间失去了奶奶,心里空落落的,挺难分难舍的,并且开始不再惧怕黑夜,甚至期待着世上真的有鬼。已经接近傍晚了,正月的天气还挺冷的。将几个奶奶生前爱吃的橘子放在她的坟前后,我默默站了一会,再一次悲伤地意识到,从此后喊奶奶再也听不到应答声了。
五叔的坟与奶奶的坟相距不远,中间仅隔着一道低矮的山岭。我隐约听到几声倾诉,带着哭腔,似乎是五婶在冲五叔诉说着什么。穿过稠密的胡叶林走过去,果然是五婶,她正坐在五叔的坟前,面前打开着几个袋子,袋子里是她从丧宴上兜走的菜:凉拌木耳、蒸鸡、蒸鱼、肘子肉......我的脚步声惊扰了她,她抬起泪痕狼藉的脸,很漠然地看我一眼。我知道她将我归到整个大家庭的一面了,认为我是不尊重和看不起她的。我想跟她寒暄几句,随便聊聊天,大约是因为她漠然的表情,我试了几次,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在那个瞬间,我又重新读懂了她一些。显而易见,她依旧将五叔放在心间,凡是有好吃的都不忘给五叔带去一些尝尝。而她肉体上的沉沦和肮脏也许是为了抵消寂寞或者获得一点金钱上的回报。2019年的时候我还是联系上五婶并去探望了她一次。我主动问起我那堂弟也即五叔五婶的儿子,五婶闷闷不乐地说:“一年到头难得打个电话给我跟我一直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点钱花可就是连个妈都不喊”
五叔和五婶的儿子,从蹒跚学步起就寄养在姑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