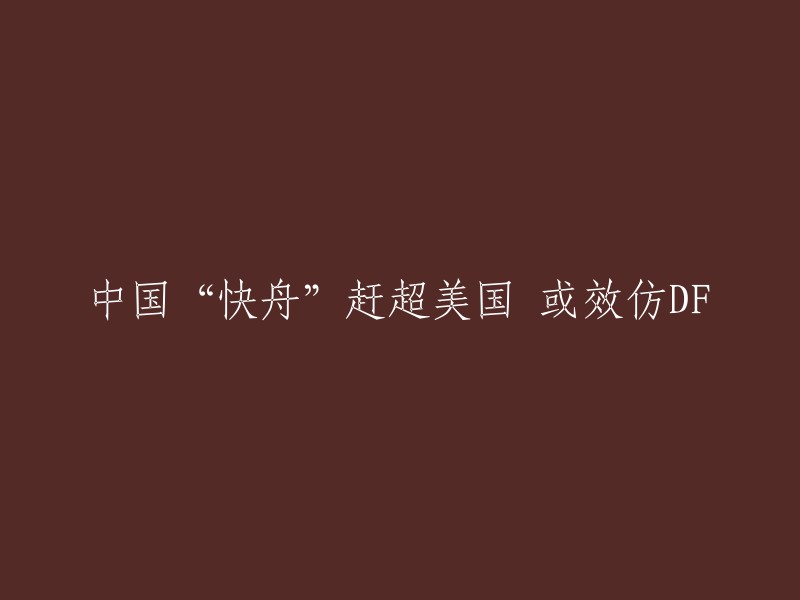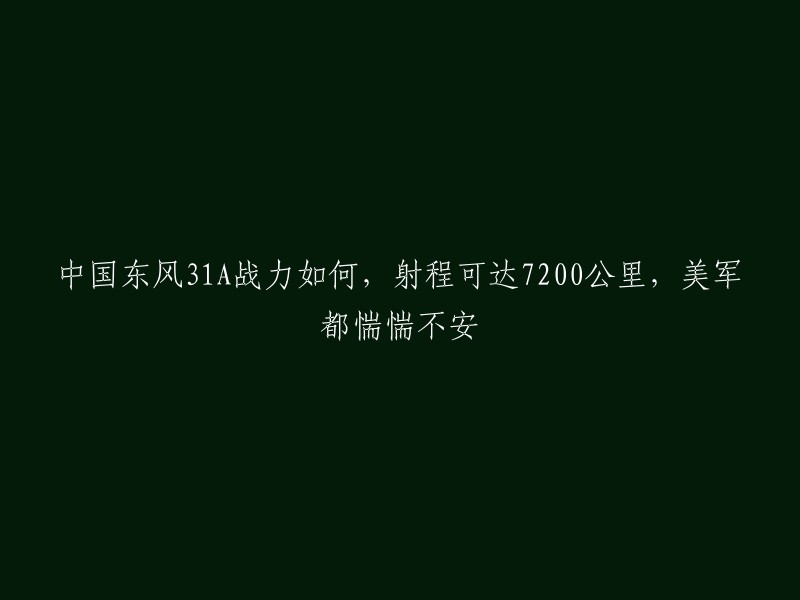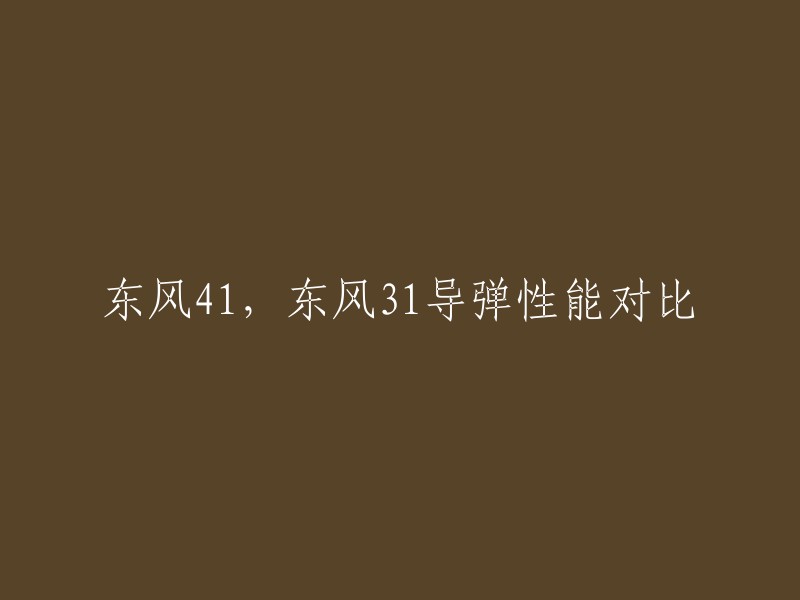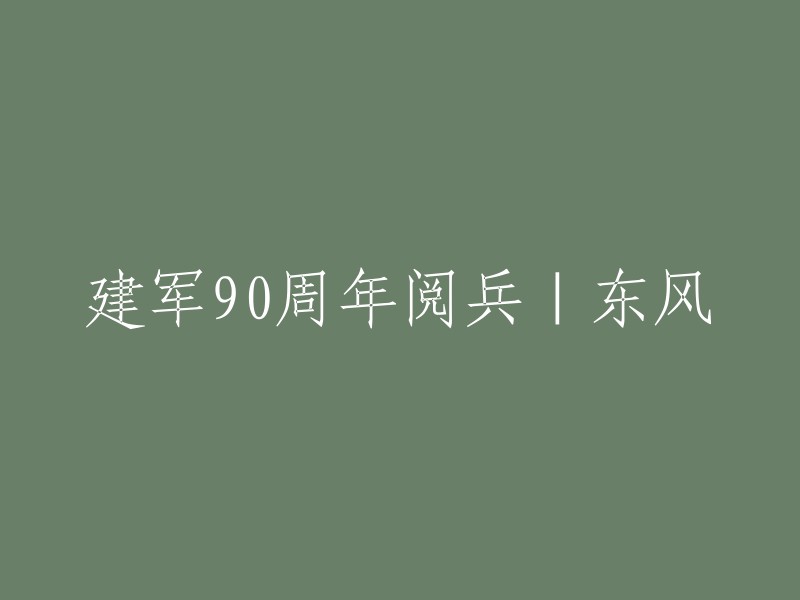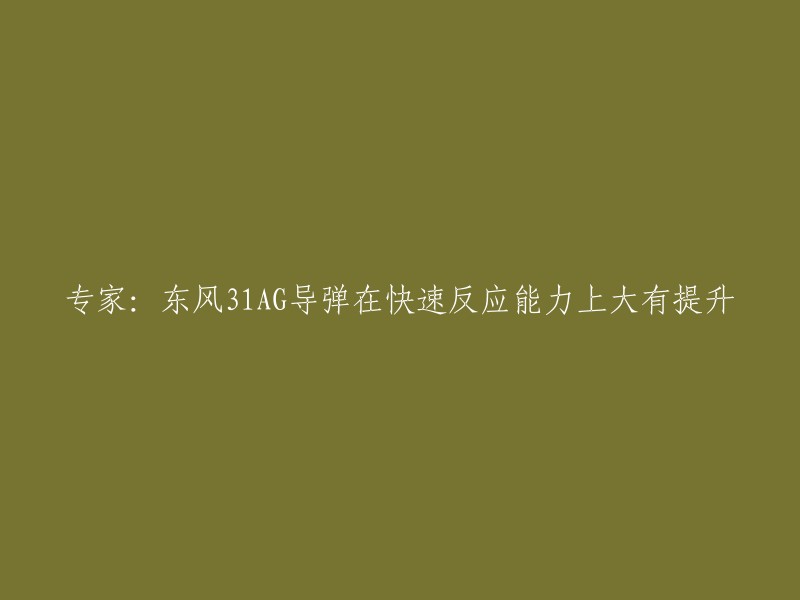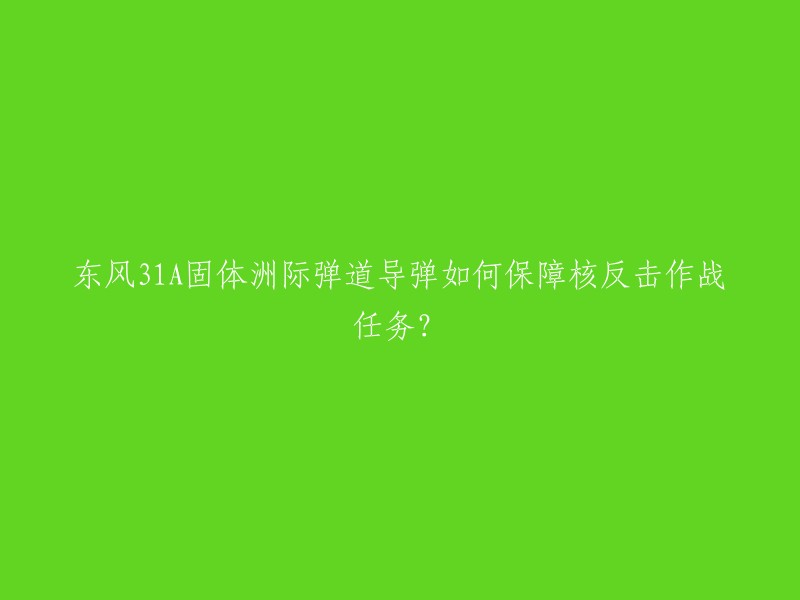今天,当我们在谈论文学日渐衰微时,大多在文学的外部寻找原因,例如现在真正读书的读者愈来愈少。这些问题都是人们的物质消费倾向愈来愈严重的结果。其次,写作者及文学受众、文化和意识的多元化、阅读模式的碎片化等等,也使得整个社会不再为文学提供专注的表达视角。
这里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学内部找找原因——例如,是否可以考虑从恢复文学的娱乐精神方面入手,扩大受众面,使文学走出日渐小众化的怪圈。娱乐精神在传统小说中其实是很发达的。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对文学的娱乐性从来就没有低看过。娱乐是文学、文化的一部分,是双胞胎或多胞胎中的一个,文学与娱乐从本质上一直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我们现在一谈小说,不少人就显出一脸“正经”,以文学的文学性、崇高性、严肃性来否定文学的娱乐性。更有甚者只偏执地看到文学的教化功能、“为人生”的目的,以为只有这些才是存在的必要。我们似乎忘记了,其实从源头开始,中国小说就是为了娱乐。娱乐恰恰是小说最为重要的品质。
那么什么是中国小说的娱乐精神呢?我认为小说的娱乐精神是指创作者在创作小说时完全是在自由、愉悦中进行的,秉持非功利的文学审美。在这个非功利精神的观照下作者始能自由地编织奇幻、诡异、美丽而动人的故事。这样才可以让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放松身心进入到浪漫甚至于玄妙的精神世界中去陶冶性情提高精神和审美境界。它包括浅层次的感官满足心理愉悦两个层面也就是说较广义的文学娱乐功能包括生理上的快适和精神上的愉悦满足(即审美性)两个层面。总之小说的娱乐精神指作者在创作小说时为了自娱或娱人读者阅读小说第一寻找也是快乐
学者吴洪森在一次网络讲座中,将《圣经》《论语》和佛教的开头做了对比。他指出,《圣经》开头讲的是上帝创世造人,人偷吃禁果被罚到地上。从此人生而有罪,戴罪之身所生活的地方,是赎罪的暂留之地。佛教开头讲创始人释迦牟尼出家前是个王子,父母百般宠爱,无意中看见了人的衰老、病残和死亡,由此悟到了现实生活,再荣华富贵也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最终都逃脱不了生老病死——人生的根本是悲苦。而《论语》开头却讲的是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与君子乎?”开宗明义地探讨了做人的快乐。李泽厚先生也认为,《论语》首章突出了“悦”“乐”二字。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日本的“耻感文化”不同,以儒家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
孔子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思想就是快乐地做人,如何在现世快乐地活着。孔子问弟子子路、冉有、公孙赤和曾点各自的理想,子路想治军、冉有想治国、公孙赤想做司仪,而曾点却说,“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表示“吾与点也”——表明了孔子对曾点的认同。正是这样的“乐感文化”,成为中国传统小说娱乐精神的文化土壤。古人一直重视好玩,富有游戏精神。无论是高堂教化里,还是儒家经典里,讲的都是快乐。一直到后来的明清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很好玩的书。
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初的小说主要是为了娱乐。在当时,受众看重小说的娱乐性,满足的是人们的好奇心。讲大道理的文章自有诸子百家、儒家经典、史学文献等,但这些并不是作家写作小说的出发点。正是小说家对小说娱乐精神的追求,使得小说逐渐疏离主流文化对小说的束缚,从而使小说具有了独立而自觉的审美意识。
从字源上来看,《说文解字》对“说”的解释是“说释也”,段玉裁注曰:“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清末胡怀琛也从字源和文体上对小说做过阐释,他认为“‘小’就是不重要的意思。‘说’字,在那时候和’悦’字是不分的,所以有时候‘说’字就等于‘悦’字。用在此处,‘说’字至少涵有‘悦’字的意思。‘小说’就是要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是讲些笑话,供给听者的娱乐,给听者消遣无聊的光阴,或者讨听者的欢喜。这就叫做小说。”“凡是一切不重要,不庄重,供人娱乐,给人消遣的话称为小说。这虽以故事为多,但不一定限于故事,非故事也可叫小说。”胡怀琛对小说传统中所蕴含的娱乐精神的分析,尤其他指出供人娱乐的小说的娱乐性“以故事为多”这点,可以说是道出了小说的娱乐精神这一事实。即在传统小说中,其娱乐性主要是由“讲故事”来承载和完成的。
杨义则继承了前人的这一说法,他认为,“小”字有双重意义:一种属于文化的品位,它所蕴涵的是“小道”;一种属于文体形式,它的表现形态是“丛残小语”。杨义还从三个层面上来阐释“说”字的语义:“首先是文体形态层面,有说故事或叙事之义。其次的语义属于表现形态,‘说’有解说而趋于浅白通俗之义。其三的语义属于功能形态,‘说’与‘悦’相通,有喜悦或娱乐之义。”他以此认为,小说的基本特征就是“故事性、通俗性和娱乐性。”
因此,无论从小说的起源,还是从字源、艺术发展史看,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天生地带有娱乐或游戏的精神品质。《说文解字》对娱乐的解释是“娱,娱乐也。娱乐者,顾名思义,为游戏、嘻乐的意思。”而小说所构建的,正是一个让人可以暂时忘却俗世苦恼的虚幻的精神空间,使创作者、阅读者均能享受到乐趣。
宋以前的文言小说,如《琐语》和《山海经》,娱乐精神或趣味叙述已隐约可见。例如,《琐语》中的《师旷御晋平公》,师旷从鼓瑟声中,预测并证实千里之外的齐侯因游戏伤臂。虽然诡异,但叙述却充满乐趣。对于怪异的《山海经》,司马迁说,“至《禹王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也说明了经史和小说之别。包括后来模仿《山海经》的一些地理传说,都是凭借丰沛的想象力,对远国异民、神奇怪异的动物的描写,把读者带入到一个神奇、荒渺的幻想空间,“以取得惊心诧骨的愉悦效果。”
到了东汉的《神异经》《十洲记》,便可更清楚地看到小说中的娱乐游戏精神。例如《神异经》中的《东荒经》中,东王公与仙女的投壶比赛,不仅是小说中最早写到游戏的,整则小说读下来也让人忍俊不禁。
《列异传》是魏晋时期第一部志怪小说集,由东晋干宝辑录、编纂而成。其中不少故事也充满着笑点。典型的如读者熟知的《宗定伯》。鬼本是狡黠刁滑的,但自作聪明,嫌步行慢,提出与定伯“共迭相担”,定伯以自己是新鬼不懂为由,诓骗鬼说出“鬼唯独不喜欢被人吐口水”的秘密,最后到了集市,定伯将背在背上的鬼紧紧夹住,不让它逃遁,鬼害怕被人看见原形,只能变成了一只羊,定伯马上朝鬼吐了几口口水,让鬼不能再变化,然后将羊卖掉,得钱一千五百文。这个故事让人过目难忘 。
《搜神记》、《世说新语》和《幽冥录》都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些小说都充满了娱乐精神,其中《搜神记》中的很多小说都是充满娱乐精神性的。例如,《倪彦家狸怪》说的是倪彦家来了一个鬼魅。鬼魅和人说话,像人一样吃喝,就是看不到形。搞笑的是鬼魅不仅告密婢女私下骂倪彦,还去追求倪彦的小老婆,倪彦请道士来收拾鬼魅,鬼魅却戏弄道士。在摆好的酒席上撒上从厕所取来的粪草,道士猛烈击鼓请求各路神仙来帮忙,鬼魅就拿了个便壶,在神座上吹出号角声。还恶作剧地把夜壶藏在了道士背上,把道士搞得狼狈不堪。倪彦晚上和老婆躺在床上说鬼魅,鬼魅就在房梁上要挟说,你们还敢说我,我把你家房梁锯了,立刻房梁就发生隆隆声,吓得全家跑到外面,点灯进去一看,房子还好好的。
地方官典农听说了这件事,认为鬼魅是狐狸。鬼魅就跑去吓唬典农说,你贪污了官府的几百斛稻谷,藏在什么地方,你再敢议论我,我就去官府告发你,吓得典农再也不敢吱声。整个小说充满了鬼魅戏弄人的滑稽感。应该说,《搜神记》里有很多这样令人捧腹的小说 。
魏晋时期的小说作者主体是方士和文人。当时的人认为“人鬼乃实有”,将“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当作一回事,但从阅读的角度看,“叙述异事”本身含有娱乐的成分。“搜奇猎异,是文人作家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志怪小说娱人色彩的表现。”这一时期还有几部被忽视的志人小说集,也充满笑点。如《妒记》,它专记上层妇女的言行,特别好玩。颇有代表性的如《士人妇》,士人妇对自己的丈夫动则打骂,并用“长绳系夫脚”。巫妪献计,在士人妇睡觉时,士人“缘墙走壁”,等士人妇醒来,手中牵的却是一只羊,士人妇受骗,以为丈夫真的变成了羊,抱羊恸哭。丈夫骗夫人说自己变成羊后每日吃草腹痛,夫人更加悲伤,可见士人妇对丈夫还是爱恋的。这个故事情节特别幽默,让人爆笑。
到了唐代,小说的娱乐性更强。如果说唐前小说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那么,到了唐传奇,虽然它也受到了道教、佛教的影响,但宗教味明显弱化,而娱乐味更加充足了。唐传奇主要是进士阶层为显示自己的才华和遣兴娱乐而为的。现在研究者常说的“行卷”或“温卷”,本质也是娱乐,只是它是娱乐比自己位置更高的人罢了。甚而可以说,唐传奇就是“文人的沙龙”,艳遇自然是文人沙龙最吸引眼球的事了。
《游仙窟》是唐代文学家张鷟早期创作的传奇作品,描写的是一出假想的恋爱故事。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手法,用一万余字的骈文详细铺陈了一场华丽的艳遇。自叙奉使河源,途经神女山,夜宿大宅,与五嫂、十娘调笑戏谑,诗赋赠达、宴饮歌舞,后来与十娘共效云雨之欢,夜宿而去 。
这部小说以轻松的笔调,无拘无束、没有任何负累的情感世界,正是张鷟此时心态的反映。小说中充满了性暗示的诗句,把唐初文人放荡、轻佻的狎妓生活,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其他写艳丽、婚恋的传奇虽然没有《游仙窟》香艳,但也颇为有趣。比如《霍小玉传》中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文中描写霍小玉的美以及宴饮酬答,让人赏心悦目 。
宋以后,白话小说的娱乐性更加明显。宋代说话中有“说诨话”一类,专讲幽默诙谐故事。嘉靖间洪楩《六十家小说》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卷,也突显了小说的娱乐消闲功能。
现存的宋代小说35部中,大致可以追溯到文言小说的有13部;在宋代历史剧中,《五朝平话》是《资治通鉴》所载的五朝历史剧,《大宋宣和遗风》是一部早期的历史剧。
宋元话本小说是宋元时代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包括小说、讲史、说经等说话艺人的底本。它的主要特点是注重趣味性和虚构,以娱乐为首要目的。从程毅中先生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收录的小说看,几乎每篇小说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充满了娱乐味。同时,话本小说中,还大量使用“彻话”,插科打诨,目的就是为了娱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文人尚趣。“晚明文人追求的趣境人生既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逍遥自适,更是一种洞穿人生的审美本然,这种审美态度表现于文学上就是视文学创作为自足自乐的个性化行为,于轻松诙谐中追求趣味,展现才情”。甚至有有人提出了“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
明代以“三言”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不少即由宋元话本发展而来,本身具有娱乐特征,加之晚明文人重趣,以及“以文为戏”的推波助澜。冯梦龙对宋元话本小说进行改写后更加丰富细致,语言更加贴合人物个性等。来自民间说话文学的娱乐性和自由勃发的生命力进一步得到张扬。
“三言”中许多故事都运用了诸如“调包”“冒名顶替”等桥段,这些显然来自民间口头文学的元素,为小说增色不少,提高了其娱乐性,使其更具吸引力。而冯梦龙在改写创作过程中,不仅让这些情节更具真实感和自然流畅的肌理,还使得情节熟悉却又令人百看不厌。这些故事甚至可以与莎士比亚的喜剧相媲美,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文。
故事讲述了新郎生病,年轻貌美的弟弟代替姐姐出门,他们精明的母亲打算在三朝后视情况而定,到底要不要让女儿真正出嫁。然而,新郎家却让姑伴嫂眠,新婚之夜意外成就了另一对姻缘。在这篇杰出的小说中,“调包顶替”“男扮女装”的情节架构可能来自民间口头文学,就像人们总是津津乐道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木兰从军的故事一样。这种出人意料的情节能够引起读者/听众强烈的新奇、愉悦的感觉,是这篇小说娱乐性最重要的来源。
冯梦龙在改写过程中,一方面使这略显夸张的情节显得合情合理,弥合了生活的真实与戏剧性之间的缝隙;另一方面,他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刘妈妈之自私自利、孙寡妇之精明、刘公之厚道软弱等,都跃然纸上。此外,这篇小说的娱乐性还体现在生动活泼的语言上。例如,代姊而嫁的孙润和小姑慧娘洞房内的一段对话,委婉、节制、语义双关、充满张力。这段对话既是文人创作的典范,也是俚俗的口语、民间生动活泼的方言土语在文学作品中的伟大记录和表达。
当刘家父女母女三人打成一团、搅成一处时,小说的娱乐精神达到了高潮。结尾是喜剧性的,皆大欢喜,刘妈妈这个不顾她人利害的自私者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受到应有惩罚,但她的女儿慧娘却是无辜的,最后得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同时证明了自己的坚贞。无论戏剧性的情节结构,还是人物的对话语言,都体现出小说的娱乐性。
而这篇充满娱乐性和喜剧色彩的小说之所以十分动人,其审美价值固然由于上文中提到的两个要素,还因为它在思想方面充分肯定了人情(相悦为婚)和人性(“无怪其燃”),肯定了“情在理中”——永恒的天理之下还有复杂的人情。这在理学家们纷纷主张理欲二分、“存天理、灭人欲”,社会风气干枯残酷的明代,尤为难能可贵。
“三言”是明代冯梦龙纂辑的三个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是明代通俗小说的代表作。其中大量的小说运用了“调包”“冒名顶替”“女扮男装”等故事模式,使其充满了戏剧性,情节曲折好看;故意制造和设置了许多有趣的对立;生动形象、诙谐俚俗的方言口语的运用。这些故事足以媲美莎士比亚具有类似故事模式的喜剧。
“三言”中小说的娱乐性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其中大量的小说运用了“调包”“冒名顶替”“女扮男装”等故事模式,使其充满了戏剧性,情节曲折好看;二是故意制造和设置了许多有趣的对立;三是生动形象、诙谐俚俗的方言口语的运用。
而哪怕在“劝善”痕迹最重的《陈多寿生死夫妻》这样的篇目中,仍有很强的娱乐精神。
总之,“三言”作为宋元话本的集大成者,中国白话短篇小说最重要、最杰出的代表,不管是其志异传奇的色彩,还是夸张离奇的情节,不管是“调包”“男扮女装”等桥段的反复运用,还是人物语言的俚俗生动,都体现出强烈的娱乐精神。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杰作,它的娱乐精神体现在对立的人物形象设置、精彩的人物对白等方面。小说中的娱乐性没有那么直接表现,而是隐藏在喜剧化场景的描写和人物的设置与对白等元素之中 。
晚清民初时期,白话小说的娱乐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白话小说的娱乐精神表现为作者在创作小说时,为了自娱或娱人,读者阅读小说,第一寻找的也是快乐。
在源头上,白话小说就带有极强的民间娱乐性。从程毅中先生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收录的小说看,几乎每篇小说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充满了娱乐味。同时,话本小说中,还大量使用“彻话”,插科打诨,目的就是为了娱乐。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以在报纸上连载的方式面世。它们在两个方面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一个是结构,一个是讽刺、暴露黑暗。它们也往往和《儒林外史》一样,于讽刺中显示出小说的娱乐特点。
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诗歌散文,但真正具备了小说要素的是唐代。在这一时期,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宗教故事等都孕育着小说的艺术因素,为小说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露出小说童年时期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的端倪。
到了宋代,随着文化娱乐活动的丰富,宋元话本因是“说话”的底本,娱乐性和通俗性自是题中应有之意。而明代以“三言”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不少即由宋元话本发展而来,继承了宋元话本对娱乐精神的追求。
明清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总的来说,娱乐性仍贯穿始终。从其源头的街谈巷议、稗官野史,娱乐性即成为这一文体的美学特征;在中国小说的演进过程中,小说这一本源意义上的美学特征,与两种力量构成张力:一种是“载道”教化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小说的功用在于教化劝惩;另一种是“为人生”的文学观念,这一观念下的写作要求真实地描写人生。
近百年来,中国小说给人的整体感受是太沉重。作家背负的精神压力太大,完全忘记了小说的娱乐精神。他们在急于批判现实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或者被世俗利益牵制,被低俗趣味蒙蔽。近些年,又呈现出小资化的写作倾向,缺乏对来自土地、来自于生活一线的、来自底层的鲜活、生辣的生命状态的书写,而这恰恰是娱乐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现象导致了很多小说在理论家如何去阐释它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的同时,却无法赢得普通老百姓的认可。即使是在著名作家中,也不乏如此的例子。譬如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本应该成为一时洛阳纸贵的作品,但市场销售并不理想。我想,或许文学娱乐精神的缺失,没有真正唤起底层阅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吧。
娱乐精神的衰微和故事性的淡化,使得小说越来越失去了读者。在当下时代,要想重新吸引读者的关注,是不是应该恢复小说的娱乐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