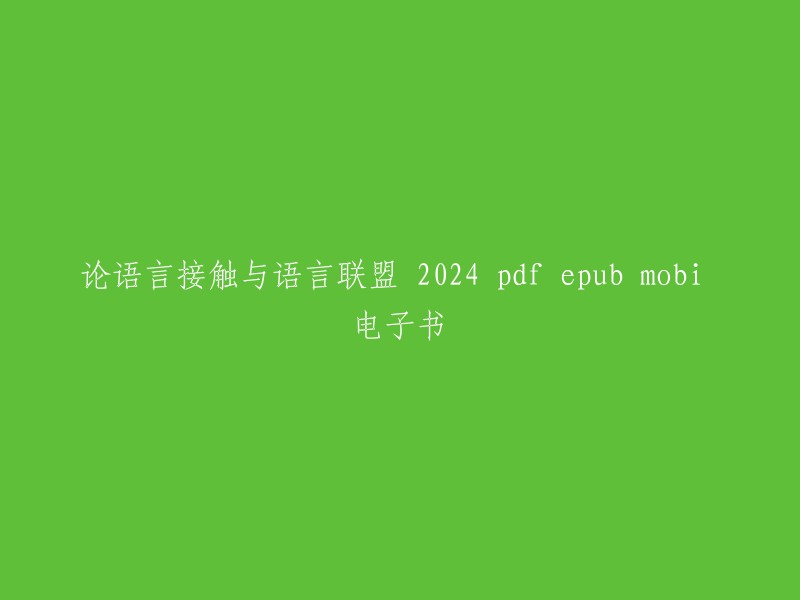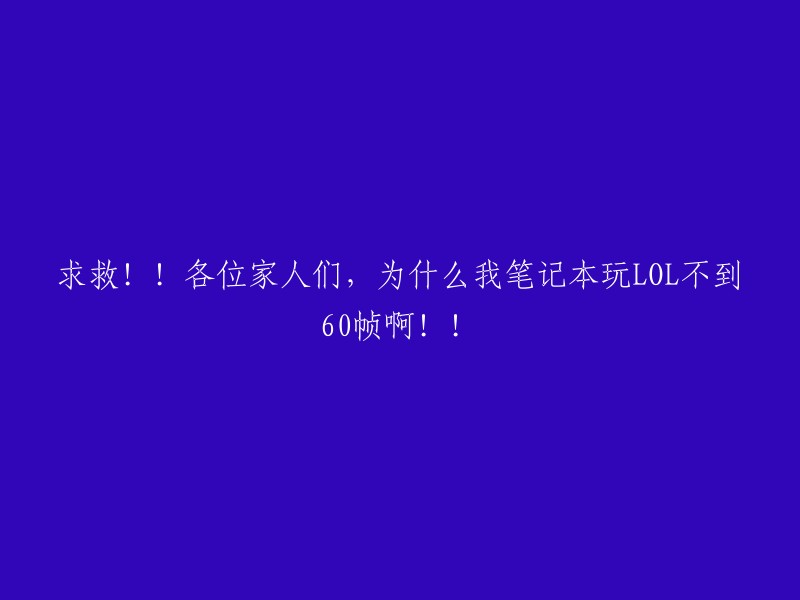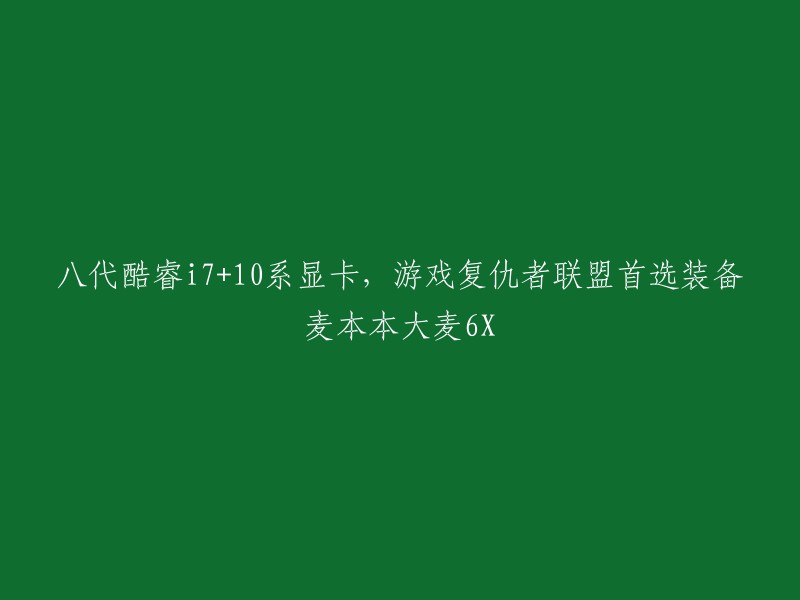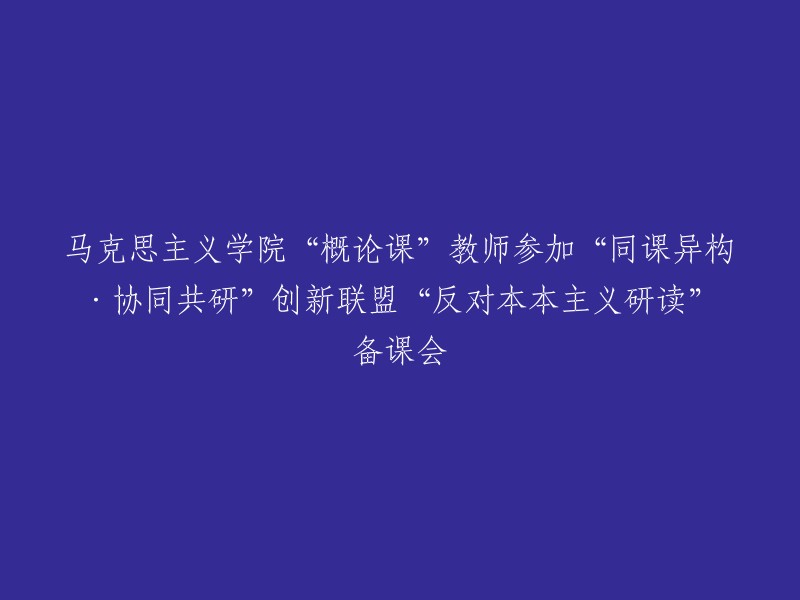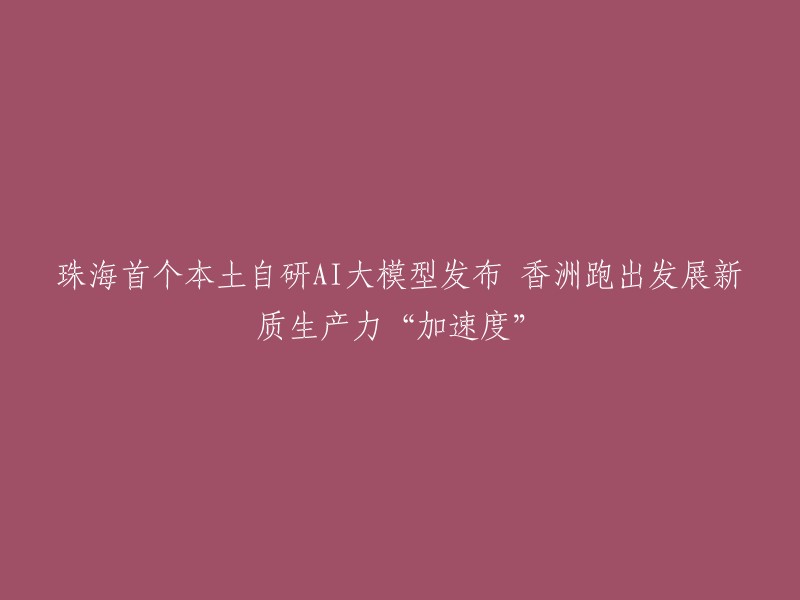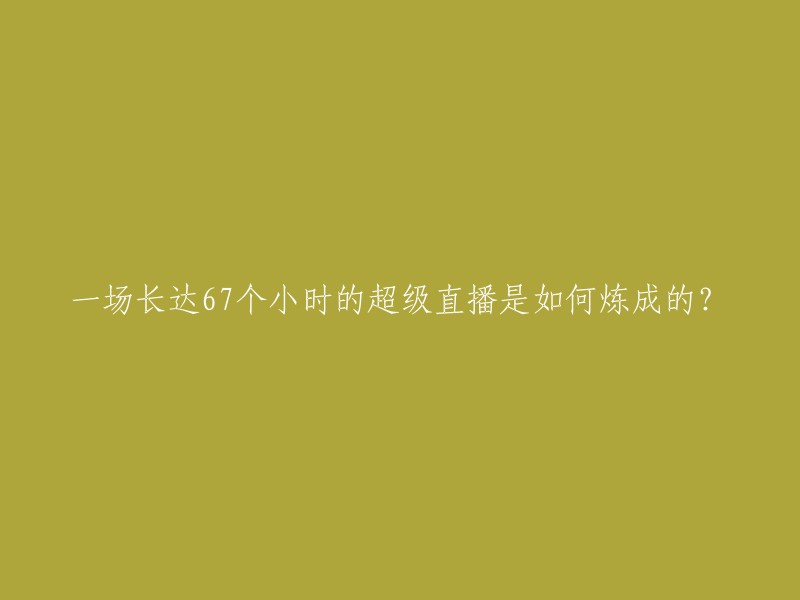昨晚,我和爷爷奶奶通电话,询问他们晚饭吃了什么。电话那头,他们语气轻快地告诉我,吃了笋,焯水后和炸泥鳅一起炒的,大火收过汁,再放点剁辣椒和青蒜翻炒几下。一筷子嫩嫩滑滑,入口生津。听得我口水涟涟,不禁生出疑惑:往年不是过了清明,山上就没得笋拔了吗?怎么今年谷雨将过,竟还有?他们解释说今年是闰年,闰二月,这时候三月未至。过了惊蛰,天气还是一直偏凉,近些日子才转暖,山上新笋正盛。听完,我禁不住叹了口气:想念家乡了。
我的家乡在湘南郴州,湘南多山,且山势大都平缓,又有舂陵水顺流而下,四季草木深秀蔚然。世间百味,各有所爱,唯独一“鲜”,能集万千宠爱——春水繁盛时,山野林间生长诸多鲜美之味:茶耳茶苞、三月萢、刺苔、菌菇、蕨菜、野山笋等等。其中,数蕨菜最易得,漫山遍野都是,山脚下随心晃一圈,就能摘上满满一筐。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提到,相对而言,野山笋便得来不易了。尽管,无论是山沟沟里,陡坡上,还是山顶,都生有一茬茬儿的小竹林,而有竹的地方就有笋。但是,采拔野山笋却既是眼力活儿,又是体力活儿;而且看似散漫分布的小竹林,也几乎全在荆棘丛生之处。拔个野山笋,眼要尖、手要快,还得有翻山越岭的决心和披荆斩棘的勇气。
不过,对于天真无畏、胆大心细的孩童来说,这都不是事儿。我孩童时最爱上山拔笋。约上小伙伴们一起,在山坳丛林间弯着腰弓着背,睁大双眼,如猫一般,跑东跑西,寻寻觅觅,顾盼流连。一顿操作下来,手臂上、腿上,都是被刮的道道,还有被蚊虫叮咬的小包,又痛又痒——可说不上来为什么,每个人都特别快乐,且乐此不疲。
拔笋之后,便是剥笋。剥笋有技巧,拇指和食指在笋尖处一搓,再用食指缠住笋衣一搅,由上而下指尖旋转,野山笋便褪去麻色外衣,露出鲜绿嫩生的笋肉。单是看一眼,都能感受到笋衣剥除后的清脆。
食笋方知春味。此番鲜味得来不易。难得的食材须善加利用。明末清初文学家、美学家李渔所著的《闲情偶寄》中提到,笋的做法:“笋之为物,不止孤行并用各见其美,凡食物中无论荤素,皆当用作调和。”但不比冬笋、春笋那般质地厚实且清甜,食笋如食肉,可以素用白水,荤用肥猪,两两相宜;对于野山笋,我们那边极少素菜的做法——若是尽量保留它的原味,反而涩口。
单独的做法,我们一般会选择凉拌,以最大限度发挥野山笋的爽脆。
凉拌野山笋是一道简单的菜肴,但是制作调味汁却需要一些技巧。首先,将野山笋煮15分钟左右,加两勺食盐去除涩味,煮熟后沥出来,放冷水中浸透;然后,将小米辣、蒜蓉、姜末、芹菜末、白糖、陈醋、香油、熟芝麻各一勺,生抽、红油辣椒、葱花、香菜各两勺,淋入适量热油拌匀;最后将野山笋撕成细条状,置大碗中,加调味汁翻搅充分,码味3分钟即可。一道凉拌野山笋,味道香辣浓烈,口感细嫩脆爽。
新鲜的野山笋和咸猪肉是天作之合。只需简单小炒,即成鲜香佐饭佳肴。此外,我还在网上学到衢州人做的一道传统菜:饭粿。饭粿是主角,野山笋是作为配菜出现的,除此还有新鲜的肥瘦肉、豌豆、木耳、香菇、葱花。按着教程尝试过几回,真真鲜到掉眉毛。
国人吃腌笋已有悠久历史。《周礼》里讲:“凡祭祀......以五齐七醢七菹三臡实之。” 郑玄注:“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笋。”凡祭祀需用七菹,末为菹笋;菹即腌菜,菹笋即腌竹笋。
我老家那边腌笋的流程则十分简洁。笋煮熟沥干放冷,煮笋的水留下备用。大蒜切片,小米椒切圈备用。将笋置入无油无水的陶罐或玻璃罐中,倒入煮笋的水淹没即止。放入切好的大蒜和小米椒、食盐、白糖、白醋和高度白酒少许。最后放入干紫苏叶盖好盖子一周后即可食用。这样做出来的腌笋香辣鲜酸薄甜开胃爽口。除了作前菜早餐佐面茶水点心外还可以用来煮鱼。
笋干,这道古老的美味,至今依然令人难以抗拒。南宋《吴氏中馈录》中就有关于晒淡笋干的制作方法:“鲜笋猫耳头,不拘多少,去皮,切片条,沸汤灼过,晒干收贮。用时,米泔水浸软,色白如银,盐汤焯。”虽然步骤相似,但在老家,通常的做法是将其整块晒干。
煮过的野山笋,竹纤维变得柔软,颜色由绿变黄,最后被晒成干瘪的笋干。与过去脆生生的模样相比,面目已经改变,质地也有所不同:褪去了脆嫩的笋干,口感变得柔韧。煮前泡一泡,可猛火爆炒,做一道最为经典的笋干炒腊肉;或是搭配老鸭炖汤,浸润了油脂,笋干的口感柔中带脆、脆中带韧,回味无穷。
春去春又来,岁月不回头。提到笋,不仅在那一口鲜美的味道,还有珍贵难忘的童年回忆。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多年后,越来越觉得那时的生活真是很简单:有什么就吃什么,种了白菜吃白菜,收了玉米吃玉米,刨花生煮花生,摘茶叶炒茶叶——“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所言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