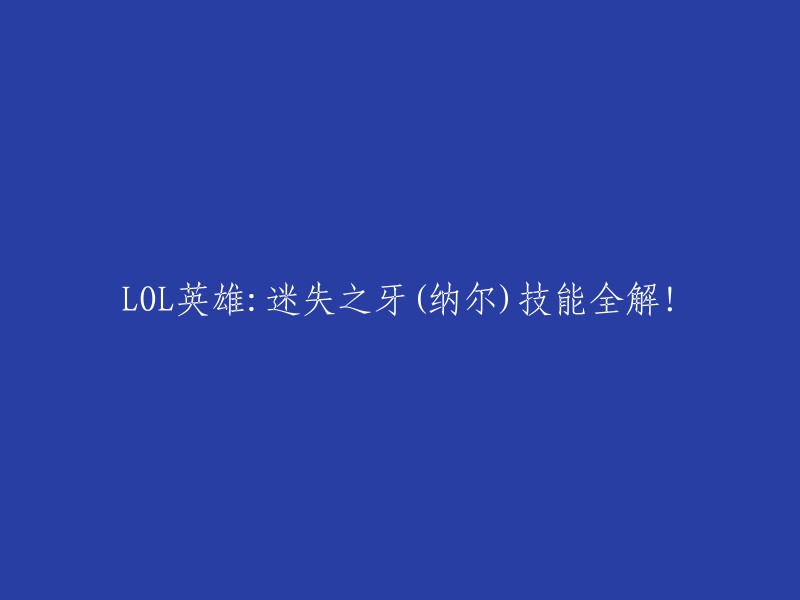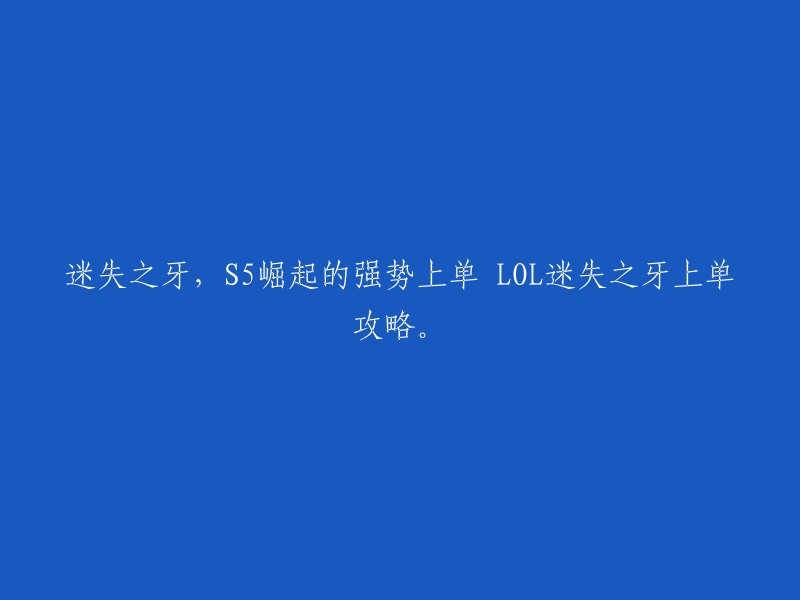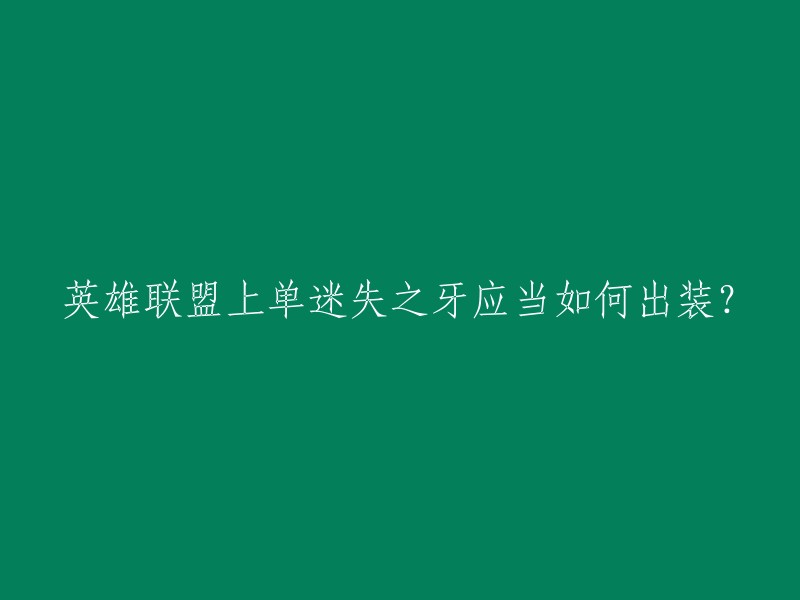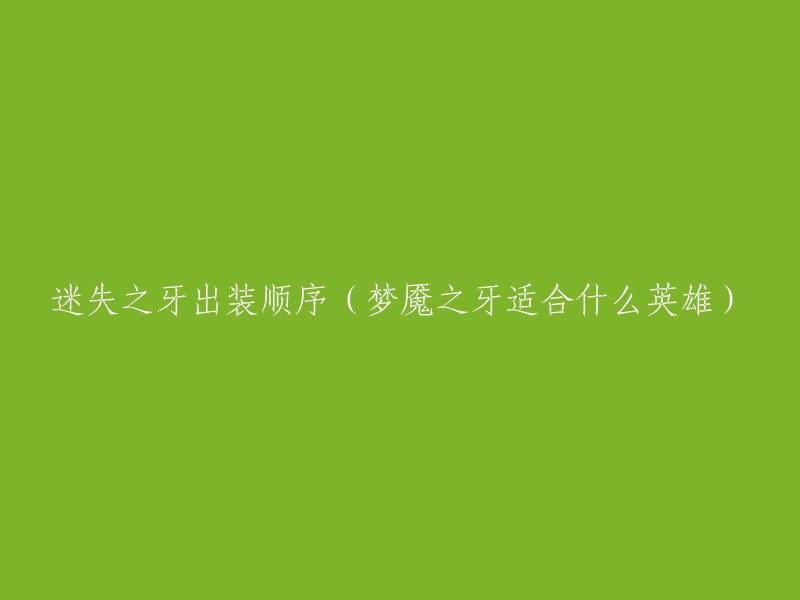塔诺德知道这出戏要砸了,因为他所有的剧作技巧都已用尽。他手下的演员全都开始怯场。可能要怪剧本的行文,或者是迷信的心里在作祟,毕竟他们要表演的是一个已故作家的未竟手稿,所以无论是什么原因,每个演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有失专业水准。
亚特洛扮演的角色只有一个“哲人”的代称,他的问题是死得太拖沓。每当那对名为“羊”和“狼”的双生鬼魂来到他身边,陪他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总是要苟延残喘好一段时间,显得莫名其妙。而这一次,南妮笑得太厉害,把脸上的羊面具甩掉了,落到地上发出响亮的碎裂声。
埃米尔摘下狼面具,锋利的毛边几乎要把他的下巴磨开花。他疼得龇牙咧嘴——塔诺德知道他肯定又要叫人拿药膏来了。
“停!”塔诺德说。他不需要大声喊。伶圜剧场出名的拢音结构可以保证,即使是票价半个铜板的蹲在边沿上的位置,也能清楚地听到最轻柔的叹息。
这座老剧院坐落在山顶城堡的附近,在这里能和郡王城主一样瞥见远处的黑暗森林。每每迎来今晚这样的夜宴场合,贵族们都会从郡王的宅子里出来,醉醺醺地走下山坡,借着酒意欣赏戏剧。一群贵族要是感到不悦耍起酒疯来,后果可比演出失败本身的羞辱更严重。
演员们中断了刚才的造型和站位,纷纷转过身面向他们的首席剧作家。
塔诺德捏了捏鼻梁,看向剧场侧面,一个胡须浓密、穿着精致的黑色套装的人,正靠在一块事记石上。
“杜瓦迪。”塔诺德对那个人说,“尽量帮我争取时间。”
杜瓦迪点点头,“我拖住观众,等你发信号。”
“一定不要来打扰我们,就算俄尔茵夫人的病情好转,突然要求亲自观看预演也不行。我们已经站到了悬崖边,杜瓦迪。我们必须同归于尽,才能齐飞升腾。”
“天赐生命之风,助我们一飞冲天。”杜瓦迪亲吻自己的手心,然后印到事记石上祈求好运。他离开舞台,走出剧场。大家在一片寂静中等待门闩闭合的声音。
他们被反锁在伶圜剧场中,斜阳已抵不过夜晚的到来,塔诺德的脾气爆发了。
“雄都的孩子主意多,你让他提桶水,他给你放把火。亚特洛,人只死一次,要死得干脆一点。”他转身面向南妮,“亚特洛犯傻,你也跟着傻笑吗?我知道你是斯卡郭恩出来的女娃子,老家带来的奇怪笑点你给我克制一下,要的是你冷峻的死亡气息。”最后,他指着埃米尔说,“你的血都顺着下巴淌了。擦一下。”
“拜托,让我往里塞个垫子吧,这个狼面具想咬死我。”
“你要让你的表演穿透疼痛!索阿蒂丝在临终的病榻上写出《千珏寓言集》的时候,她抱怨了么?没有。你得懂得敬畏!她的传世之宝正在刮擦你的脸。”塔诺德说着,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扔到南妮脚边。
这个剧团已经彩排了不知多少小时,但索阿蒂丝未完成的遗作让他们一筹莫展。要问责任,塔诺德承认自己有一部分过错。作为埃尔德堡最大、也是唯一的剧院里的首席剧作家,替她续写遗作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
“《果园里的羔羊》是索阿蒂丝的临终狂舞。她迸发出的最终火花,现在被我们拿在手里......而你们全都选择亵渎她的记忆,为了贪图虚荣和慵懒而对自己的戏挑肥拣瘦。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从迫近的湮灭中感悟真理。如果不是死亡让她持笔的手停在了这一句话上,可能我们将会对自己短暂而悲惨的存在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几位演员一言不发,垂头丧气,最后是亚特洛清了清嗓子开了口。
“请恕我直言。”这个瘦高的德玛西亚人稍作停顿。塔诺德知道亚特洛肯定要唱反调,毫不掩饰地翻了个白眼。“或许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注定就不该由别个人续写。”
塔诺德感觉自己的品行受到了攻击。他们曾就此问题反复争论过。“你是想说这场演出就是亵渎?”
“我们似乎无法再现出一位大师在大限将至时的情绪。”
“你疯了吗?我们现在的确是快没时间了!”塔诺德指了指剧场木墙缝之间洒进来的落日余晖。他突然觉得一阵寒意拂过全身。
“可能,我们就把我们知道的部分演出来,没完成的部分就不演。这难道不是纪念索阿蒂丝的正确方式吗?你得承认,塔诺德,这一套,”亚特洛指了指自己周围,“行不通!。”
亚特洛说的对。那位多产的吟游诗人写出过许多寓言故事,但他们始终都未能再现其中的灵感火花。他们的主顾是索阿蒂丝的狂热剧迷,虽然自己身体抱恙,但却期待这个剧团创造奇迹——给一部残篇续写结局。在不择手段的创作过程中,塔诺德全权委托了杜亚迪向西远行,到嘉文二世国王的雄都内寻找吟游诗人索阿蒂丝当初用过的面具。这两副面具都是古董,所以非常昂贵。
塔诺德垂下了头,然后肩膀也耷拉下来,然后他向后躺倒,感觉喘不上气。天色渐晚,他焦急的心在狂跳。
“我们必须取消演出。”他揉了揉额头,想挤出最后一点运气,但只揩下来一手汗。“更糟的还在后头,我们还必须得退款。”他深吸一口气,“可我们已经把金子都花出去了。”
这个时候,塔诺德犹豫着是否应该提及羊面具损坏的事情。他脸上的血色瞬间消失,南妮一只手紧紧握住面具碎片,其中一只木耳朵断了,她说:“我觉得可以缠起来。”
“简直是波澜壮阔。”塔诺德强笑着说,“我们的金子正是花在它上面了。这对面具是索阿蒂丝当初用过的。是租来的!”“她说了,是意外事故。”埃米尔说。
“让我想想。”塔诺德站起来端详这座剧场。阶梯状的环形观众席已经矗立了几百年。一块块事记石是伶圜剧场的根基。这些巨大的石板排成环形,它们立在这里的时间,甚至比任何人定居于诺克默奇的时间都更久远。经年累月,一层层木质观众席沿着石环外侧耸立而起,让人们可以从更高的视角观看舞台上的戏剧和其他仪式活动。演员和歌手会把自己的徽章刻在石柱上,在这片圣地留下自己的痕迹。
这座剧场一直都是塔诺德的家,在许多次艰难时期为他遮风挡雨。现在,在他的执掌下,这里却成为他悲伤的源头。
“一副损坏的面具讲述了两个故事,”中间看台传来一个声音,那里是最富有的贵族预留的位置。即使是四下无人的时候,塔诺德也不敢用那边那些精美的靠垫当枕头。“如果你算上面具工匠的话,其实是三个故事......可惜啊,没人愿意听那个故事。”
“我们都说好了彩排期间谢绝访客!”塔诺德对着演员们说。
“她一整晚都在这,”南妮说,“我们都以为她是你带来的人呢。”
一直都在吗?不可能。塔诺德这几周一直失眠。他立刻看向那个女人,她坐的黄金座位是给俄尔茵夫人单独预留的。两夏以前,嘉文二世国王的子嗣曾坐在那里的丝绒靠垫上欣赏过塔诺德编导的万鱼之王。最终落幕的时候,那个孩子鼓掌的声音最响亮。
“你是谁?”塔诺德说,“上前面来。”
那个女人往前走,但昏暗的光线并没照清楚她的面目。她的双眼就像迷雾笼罩下的遥远星辰。她戴着似有似无的半面具,面具顶端伸出一根奇异的枝杈,枝杈上单独挂着一片黑暗的树叶。她的步调节奏透出贵族的优雅,塔诺德最后终于认出了她罩袍上的家徽。
她正是他们的赞助人,看来是克服了顽疾。
“俄尔茵夫人,我有眼无珠!请见谅。”塔诺德恭敬地俯身鞠躬。“请问,是谁家的面具得来福分戴在您的面前?看着眼熟但又想不起来。”
“这是用艾尔德劳克树雕出来的。”她的嗓音平静,虽然轻声细语,但却听得字字清晰。“故事里说,从艾尔德劳克树上取下来的任何木料,都会和大树母亲在同样的季节开花萌芽。无论相距多远,只要大树母亲依然挺立,这份纽带就绝不会被扯断。”
“真是稀奇,夫人。”
“容我插一句嘴,”俄尔茵夫人对着演员们说,“我有个修改建议不知想不想听。”
塔诺德双手胡乱挥舞,示意大家安静下来。“我们最喜欢的赞助人要提建议,我们肯定欢迎。”
“索阿蒂丝在世的时候,所有演员都是戴面具的。那,或许大家必须带上面具,才能窥探她在死亡大门之前看到的那些神魔灵怪,体味她在被黑夜拥入怀抱之前的奋笔疾书。”
“这个主意我喜欢!”亚特洛说,“装面具的棺材呢?剩下的面具都在里边。”他一边说着,一边钻进后台消失了。
“别急,稍等,这得好好商量——”
塔诺德话说到一半停住了,因为他看到那个戴着艾尔德劳克木面具的憔悴妇人把双手扣在一起。他们这位赞助人似乎有点不同寻常。
但还不等塔诺德找到旁敲侧击的机会,亚特洛就已经回到了台前,拖着一个长度堪比他身高的大箱子。箱子侧面刻着Q•W•索阿蒂丝的名字。塔诺德突然意识到,这个古旧的木箱的确是很像一口棺材。
亚特洛搬开厚重的箱子盖,说道,“入土的诗人朽烂以后的味儿。”
这人真是没品味。塔诺德心想道。生锈的折叶发出厚重的吱嘎声,像饿犬的哀嚎一样回荡在剧场里。另外两个演员伸长了脖子往箱子里看。
“先别急着挑选,”戴艾尔德劳克木面具的妇人说,“务必听我下面一言。天色已晚,戏将开场,若要今晚为人铭记,各位需选择与自己相称的面具,因为我们所演绎的灵魂......”
“......常寄于我们内心。”埃米尔补全了后半句。
“演员的信条。”南妮说。
“无论这场疯狂闹剧最后的味道如何,”亚特洛撇嘴露出歪笑,“我都要参与其中。来吧,塔诺德。你就是再顽固也得承认,现如今这个情况,我们必须借着生命之风舞下去。”
“勇往直前。”那位妇人说。
塔诺德似乎从她口中听出一丝笑意。他记不太清楚......刚才杜瓦迪离开的时候,贵族的看台没清空吗?整座剧场都清空了......而这位俄尔茵夫人现在给他感觉也很不一样。她似乎体态憔悴,忧心忡忡。似乎俄尔茵夫人并没有从恶病中彻底康复。傍晚的凉气开始袭来。
“夫人,见您安康无恙我甚是高兴。要不我给您拿件斗篷来?”
亚特洛展示出一副骨白色的面具,前方突出又长又尖的弯钩鸟喙。他原本就瘦高的身材,宛如一只食腐的飞禽。俄尔茵夫人靠近舞台,看起来古老但矍铄优雅。她皮肤像石膏般凝固,头发如同黑夜向外发散着拥抱。塔诺德居然把俄尔茵夫人认错。南妮对埃米尔说:“跟我换面具,你的皮肤比不过我的。”二人交换面具,戴到面前。风吹过伶圜剧场,塔诺德听到说话声。“小羊,这里,有心跳。”塔诺德看到南妮和埃米尔牵手戴对方面具,两名演员唱起诡异台词。塔诺德穿过舞台,盯着憔悴的妇人。妇人说不是他的雇主。塔诺德让戴面具的演员下台,喊道:“杜瓦迪!”
塔诺德停下脚步,他看着那个并非俄尔茵夫人的妇人转过身看着他,闪烁的眼睛深邃而广袤。在艾尔德劳克木面具下,那双眼睛散发出诞于黑暗的光芒。诡异的光泽让塔诺德神游出窍。无论这个人是谁,他感到相识而又陌生;恐惧而又向往。要逃离她似乎很傻,但又合情合理。
“面具都给我摘掉,”他说,“这,简直疯了......这出戏中邪了!你们还没看出来吗?假如,我们大胆猜测一下,索阿蒂丝并不是意外死在写这出戏的半途中,而是写出果园里的羔羊这个行为本身害死了她......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诅咒!”
回答他的不是那个憔悴妇人,不是南妮的狼,也不是埃米尔的羊。亚特洛,或者说透过亚特洛发声的东西,用刺耳的声音回答了他。他高高展开双臂,单腿站立,宛如一只食腐的飞禽。
“作者等着我啄食。”他的嘴角裂开了口子,“索阿蒂丝已经真正死亡了......如今已经没有人记得当时的她。”亚特洛被拉长的脸颊上流下泪水。那个声音让塔诺德的心脏僵滞,脚步也停下了。“索阿蒂丝跟在我身后飞,很快就迷失遗落。纸张上的文字。风中的名字。只不过是......残片。”
“索阿蒂丝的残片依然是索阿蒂丝。”憔悴妇人说。
“他停止了表演......”占据了亚特洛的东西丝毫不在意自己对他的身体造成多大痛苦。那个演员的胳膊猛烈向前扭摆伸展,皮包骨头的手对着塔诺德伸出一根凌厉的指头,“而且他不戴面具......”
“你距离索阿蒂丝是如此接近,”那个妇人对剧作家说,“选一副面具,见证她最后一场戏最真实的演绎。”
他想逃离伶圜剧场。他想象自己跑上山坡来到郡王城主的山顶城堡,或者跑到镇上。他进入俄尔茵夫人的宅子以后会怎样?他望向那个憔悴的妇人。太阳几乎已经落山。虫鸣和鸟啼声渐起,迎接即将到来的黑夜。他曾在多少个夜晚梦见过索阿蒂丝的临终时刻,最后一场戏......
“必须所有人都戴好面具。”那个妇人说。
塔诺德哑然地点了点头,捉摸不透艾尔德劳克木面具后面的表情如何,但那片黑暗的树叶在一阵觉察不到的风中轻轻飘舞。
“如果必须要我选面具,那我承认,我知道我要选的那一副并不在这个箱子里,也不在这个舞台上。”他觉得自己的四肢重新注入了生命力。他浑身骨骼僵硬,动弹不得,但那种情况只是暂时的。
那个憔悴的妇人笑着说,“你想戴我的面具?这是极好的决定,亲爱的塔诺德,一个充满创造力与好奇心的人。来从我面前摘下它吧。”
“我要摘下你的面具,然后变成你。愿我们所演绎的灵魂......”
她终于说出了那句:“......常寄于我们内心,根深叶茂。”
随后,塔诺德摘下了那副艾尔德劳克活木面具,戴到自己脸上。这一刻,他终于看到了索阿蒂丝戏剧的真实结局。这个结局既完美又糟糕,既充满活力又令人窒息。
“朋友们,同伴们,请就位。”他说,“我们的故事可不等人。让我们同归于尽,齐飞升腾,共唱和声,礼赞生命之风。”
“最后的呼啸。”羊、狼和秃鹫齐声应答。
于是,他们开始了表演。
***
杜瓦迪一整天都在瞒着塔诺德,不敢告诉他关于俄尔茵夫人的消息。但有好几次他差点就忍不住透露出她的死讯。今早还没破晓的时候,她就伴着恶病离世了,至少新任俄尔茵家族夫人是这么说的。这个噩耗足以摧毁整个剧团的士气。他知道,塔诺德是最无法承受的。
虽然杜瓦迪心情沉重,但在这场悲剧的尽头,也有一丝光明,一件激动人心的好事。俄尔茵夫人在临终的病榻上嘱托,要将她的财产全部用于资助伶圜剧场,点名由塔诺德管理,不设期限。
然而,随着时间越拖越久,那帮醉醺醺的贵族老爷们开始等得不耐烦了。脾气大的贵族要是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往往会出言不逊,冷嘲热讽,而最糟糕的情况则是,抵制未来的剧团创作。
前来的观众们开始在门口聚集,他们脸上都涂了烟灰,以此向俄尔茵夫人致哀。就在杜瓦迪打算说点什么压一压场面的时候,他听到了塔诺德的开门信号。
他连忙跑到大门口,搬开了沉重的门闩。观众们冲进剧场,他们看到演员们已在铺满了黑柄玫瑰残花的舞台上摆好造型,纷纷驻足。这幅骇人的景象把乱哄哄的人群镇住了。他们迅速而安静地找好自己的座位。俄尔茵夫人的专座是整个剧场里唯一的空地。
演员们保持着充满张力的静止,而台下的贵族们则等待着索阿蒂丝失传已久而且没有写完的绝笔,隆重开场。
杜瓦迪没有看到塔诺德。很少看到这位剧作家在首演之夜丢下演员们不管。正常情况下,他会向观众们致欢迎词,然后带上一瓶酒站在侧面观看。
他转身查看开场的造型。南妮和埃米尔锁定在至死方休的拥抱中...
观众们安静地坐在台下,急切地等待演出的开始。然而,杜瓦迪意识到似乎少了点什么。他来到后台,查看剧作家最喜欢的位置,却发现没有酒,也没有塔诺德的身影。
这时,他意外地发现了世上仅存的那一本果园里的羔羊。翻开最后一页,他看到故事依然没有写完。在塔诺德稳健的笔迹下,竟然写下了新的一行:结局不给那些不戴面具的人看。她给我看了,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