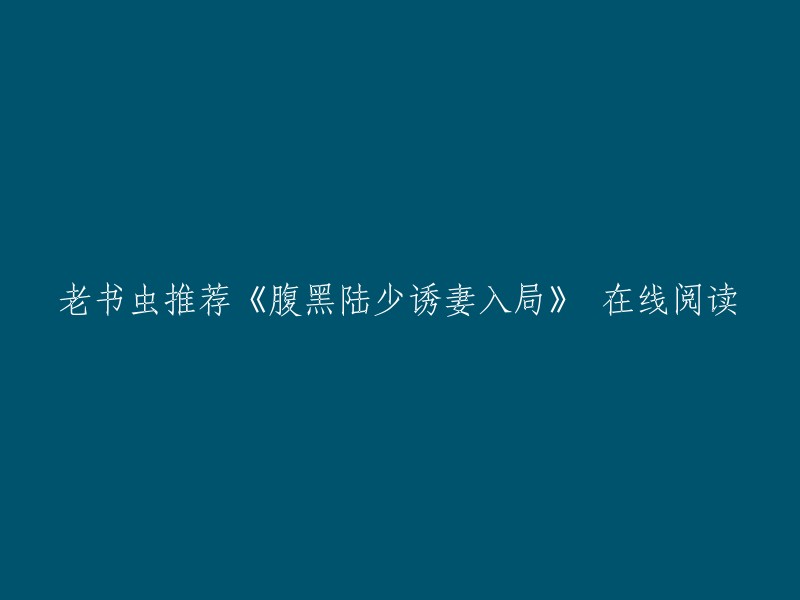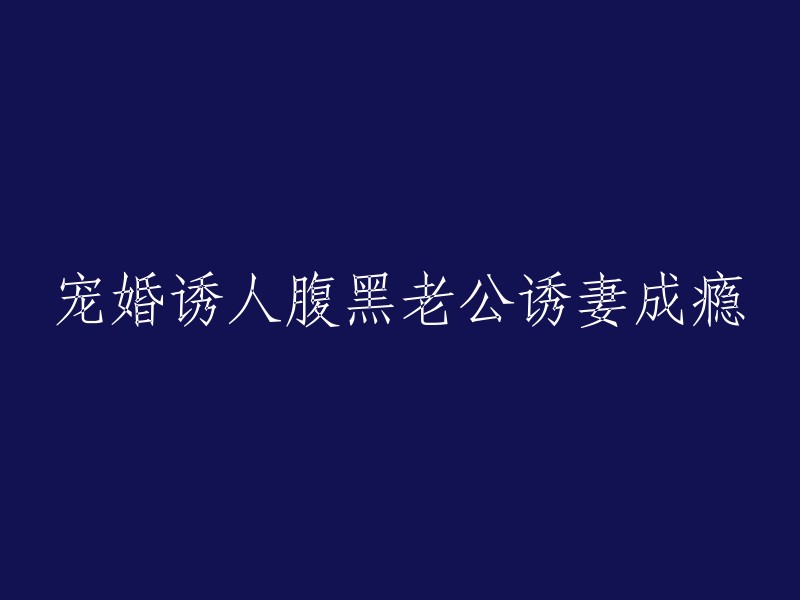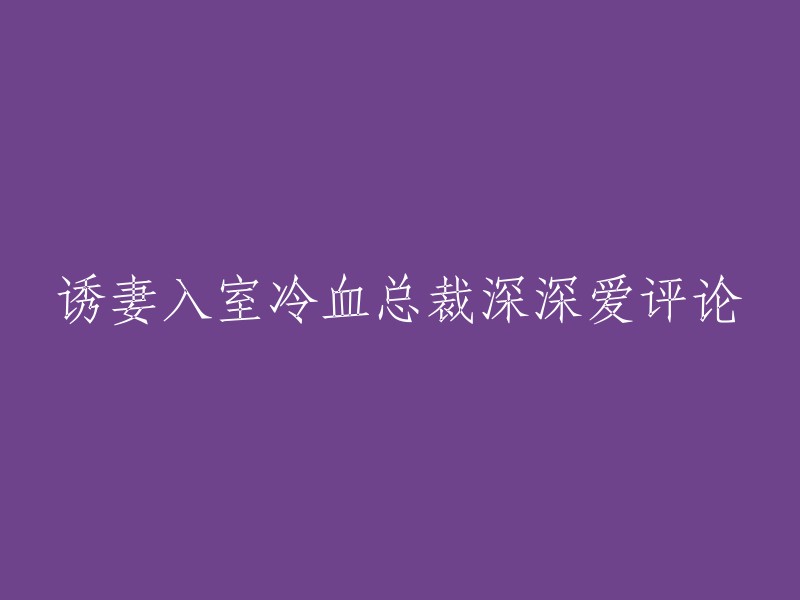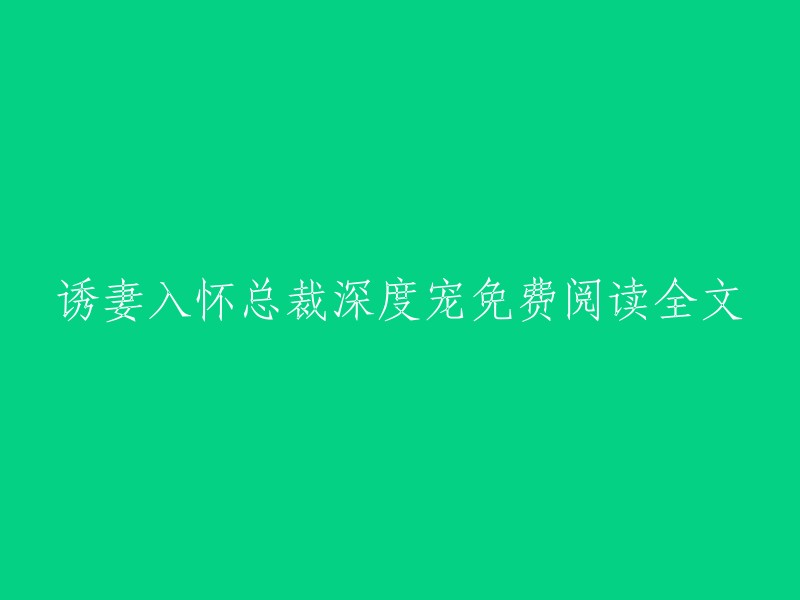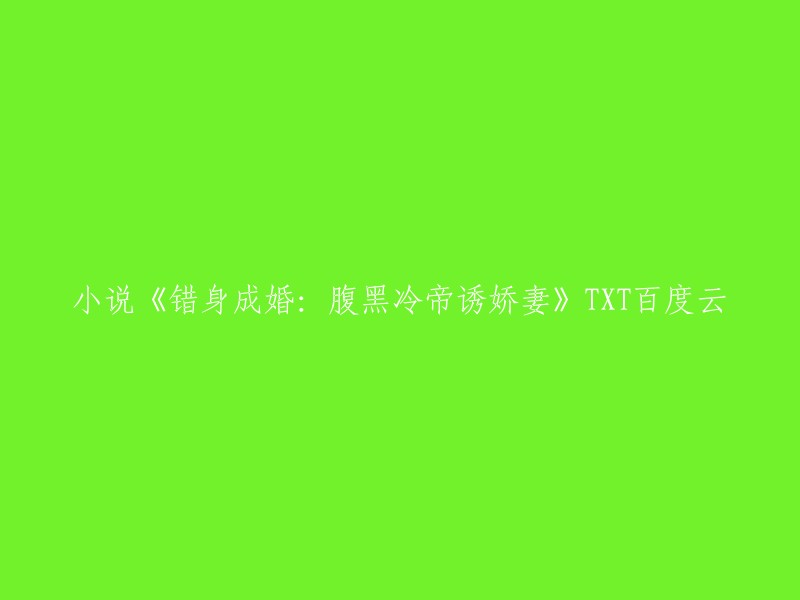“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出自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典型的战争诗《国风·邶风·击鼓》。这是一首厌战情绪贯穿始终的诗,士兵唱的一首思乡之歌。
这句话一般用在对婚姻的承诺,表示希望与对方相知相守一辈子。
《击鼓》共有五个诗章,分别为:
第一诗章“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在这一诗章中,“独”字明显表达了愤愤不平的情绪,奠定了整首诗的基调。这位士兵在众多“土国城漕”者的相比较中,产生了强烈的怨郁情绪和思归意愿。这种情绪可能源于他对战争的不满和对家庭的思念。
第二诗章“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在这一诗章中,士兵的抱怨情绪更加明显,与战争发动者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这可能意味着他在战场上难以发挥出色表现。
第三诗章描绘了他居处无宁、丢失坐骑的反常表现,进一步强化了他因思归而导致的失魂落魄、漏洞百出、左右失据的行为体验,为整首诗情感高潮的到来作了铺垫。
第四、五诗章是《击鼓》诗的情感高潮。在这里,士兵揭示了自己对妻子的强烈思念和想要信守承诺而恐不能的深深隐忧。这两个层次的情感关联紧密,共同构成了整首诗的内在逻辑。
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对此有一处眉批:“在此一章追叙前盟,文笔始曲,与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机局相似。”方先生准确地揭示了战争叙述和情感抒发的脉络,展现了他独特的眼光。
综上所述,《击鼓》通过五个诗章展现了战士在战争中的种种情感和心路历程,使读者深刻体会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无奈。同时,诗人通过对战士内心世界的描绘,也传达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家庭亲情的珍视。
综上所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诗表达了出征丈夫对新婚妻子的深厚情谊和浓郁思念,真挚而深沉。也就是说,“执子之手”要执的正是“妻子的手”。因此,之后把它拿来作为爱情或婚姻的誓言也就顺理成章,哪里会有误用的滞碍呢?
然而,我们又能不能反过来说,讲“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表现战友情的人是误读了《击鼓》呢?我以为没有必要如此草率。阅读应该提倡仁智共见。一方面,可能是认为《击鼓》是战争题材的诗,而战友情是战争众多情感中最深厚而动人的情感,所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应该是战友的手相执,才对得起战争二字。固然,战友“执手”也很正常,不过在激烈的战斗场景中因想到“与子偕老”而相“执手”的战友似乎让人无法信服。战友情还是应该多些阳刚气,“执手”的举动多少阴柔些了吧?宋代词人柳永用“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寒蝉凄切》)表现男女情愫,就更加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何况,无可否认,《击鼓》是一首厌战诗,一边厌战,一边发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更有点不可思议了。战友情不更应该体现在“誓扫匈奴不顾身”(唐陈陶《陇西行四首·其二》)“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唐卢纶《塞下曲》)的壮烈行动里吗?
另一方面,可能认为战争中战士没有时间去思念自己的妻子。的确,尤其古代战争几乎是男人的事,女性唯恐避之不及。但这并不代表战争与女性就完全无关。相反,女性在战争题材的诗歌中,往往充当着特殊的角色。有的女性为丈夫能成为勇士而自豪,像《诗经·卫风·伯兮》中,“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就是在夸耀作为勇士的丈夫高大威猛,出类拔萃。有的女性甚至鼓动丈夫随王征战,封侯拜相。而更多的女性是作为牵挂男性或被男性牵挂的对象出现于诗词中的。甚至像《伯兮》和《闺怨》里的女性,虽然她们俩各自有复杂的内心,但是她们渴望与丈夫团聚的需求却并无二致。特别在反对战争或厌恶战争的诗歌中,女性更是反对或厌恶战争思想情感的重要生成元素。《击鼓》诗里的女性就是作为战士丈夫牵挂的对象,是丈夫厌战的根源和符号。因此,对战争题材诗中女性形象和作用,也要来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臆断有无。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击鼓》中战友情的存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误解其中的夫妻情。此外,援引古诗词脱离原有语境和意境的情况非常普遍。例如,在《论语·宪问篇》中引用《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中的“深则厉,浅则揭”这句话来揭示审时度势、随波逐流的道理,但实际上这句诗是写爱情的;又如引用李商隐《无题》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焟炬成灰泪始干”来赞美教师的奉献精神,与原诗的爱情本意相去甚远。因此,这种“有句无篇”的征引法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创作血液。事实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已经被广泛用作爱情誓言和对婚姻的祝福语,成为民族接受心理学的一部分,并非简单的误用就能推翻。因此,我们应该继续保持“夫妻执手”,白头偕老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