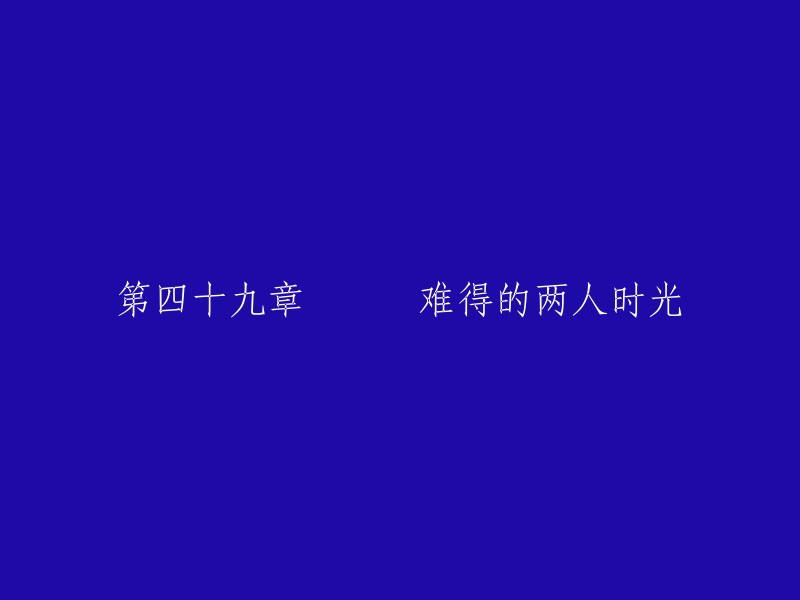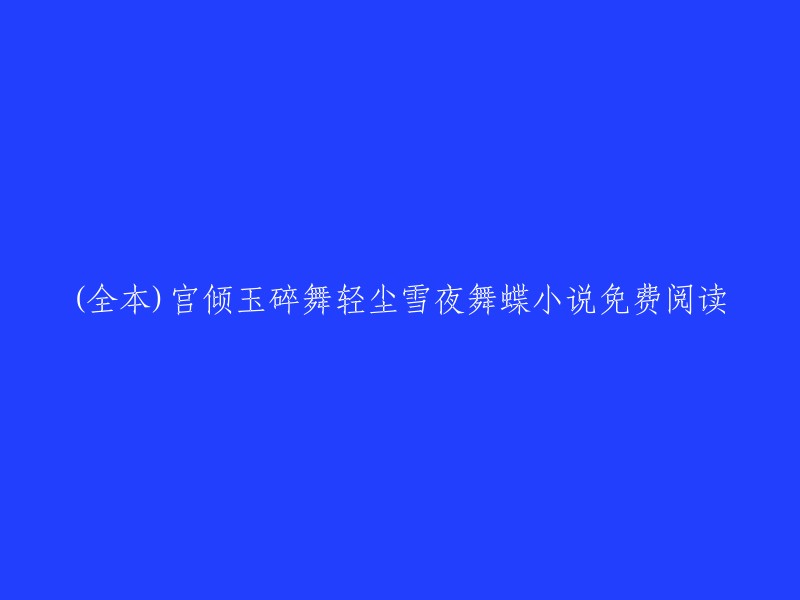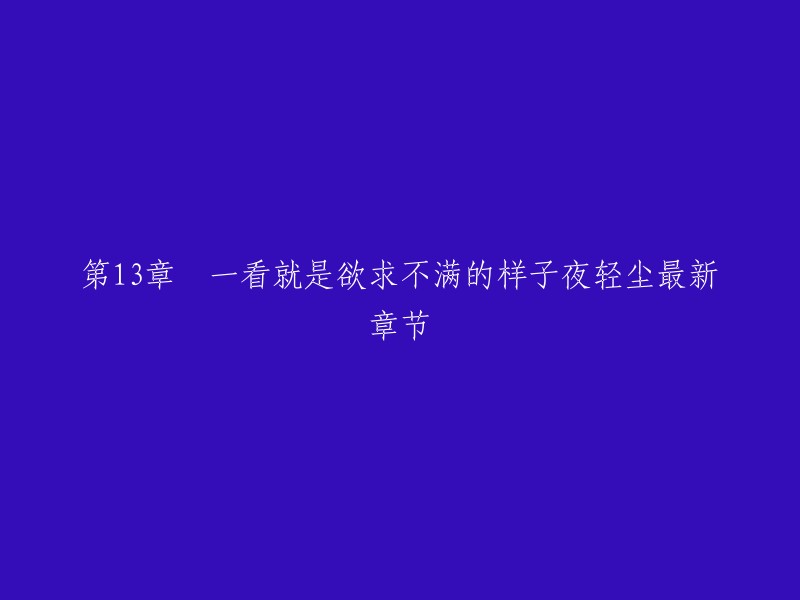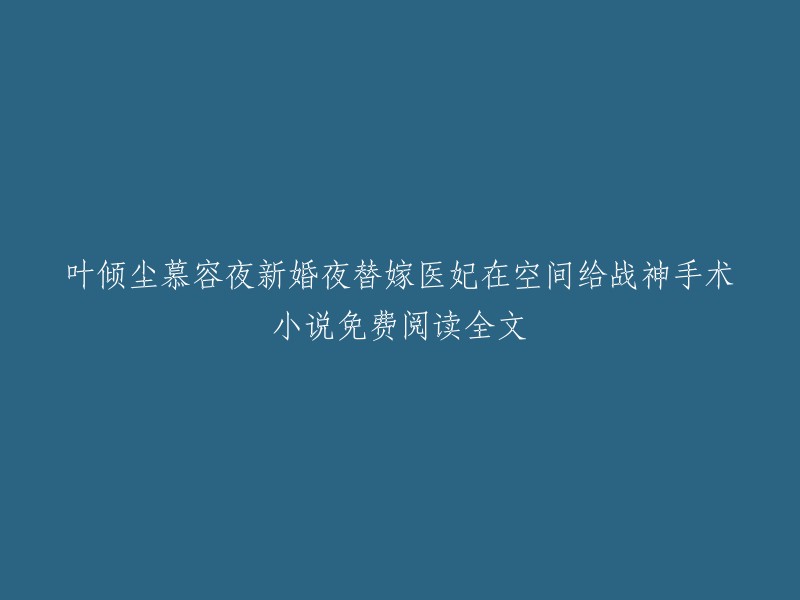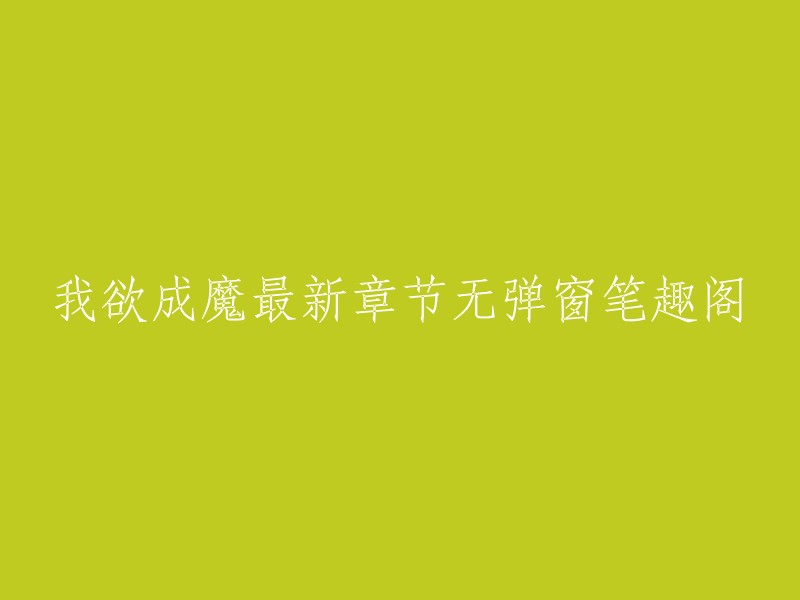正如翻译家林少华在得知莫言获得诺奖时所言,“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始审美就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对超越现实、灵魂层面的追求和探讨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贯倾向。”往往是追求超越民族、国家,探讨普遍的人性和普世价值的比较多,这也是村上春树等世界一流作家作品的共同之处。而中国人讲究入世,文学大多贴近现实、关注社会而莫言则迈出了这一步。
正如诺奖颁奖词所评价的: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从他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可知,莫言的狂欢性想象力与时空辽阔、体量巨大的怪诞历史叙事暗相匹配。此处“历史”绝非事实性和公共性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赋予怪诞的过去时想象以合理性和赦免权的空间。
而在其新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蛙》中,更具这种代表性。台湾版《蛙》的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在《蛙》的写作过程中,莫言的心态也与以往不同。因为在他看来,《蛙》是一部冷静的小说,是一部关于灵魂的小说。我们过去都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拿放大镜寻找别人的罪过,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人只要认识到灵魂深处的阴暗面,才能达到对别人的宽容。作为作家,应该对他人抱有同情。哪怕他是十恶不赦的恶棍,那怕他无中生有地造我的谣言,那怕他将唾沫啐到我的脸上。因为他本来可以成为好人的,成为恶棍,是他的最大不幸。如果能达到这一高度,才是真正的宽容,才能达到真正的悲悯。”
陈晓明在评价莫言时这样说,莫言的小说可以找到当代国际学界最热门的所有的主题,既是现代性的表达,又充满后现代的蛊惑人心的意味。20年过去了,莫言的写作依然旺盛,笔力狂放,就说是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也不为过。那些语词、情感、戏谑、快乐,就象他家乡的红高粱一样,始终那么茂盛!多年来,我们一直困扰于中国本土的汉语写作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是与世界一流大师的作品比肩,中间横亘着一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门槛,就把本土写作挡在现实主义的藩篱之内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