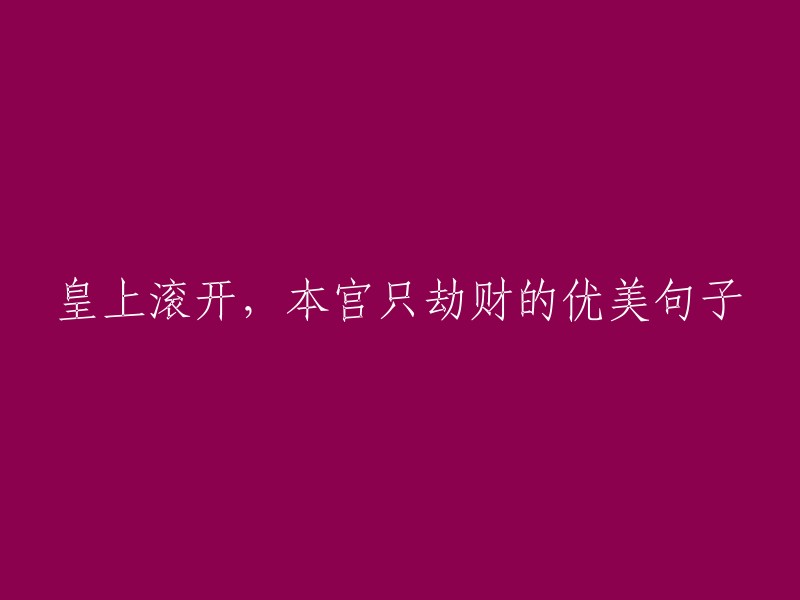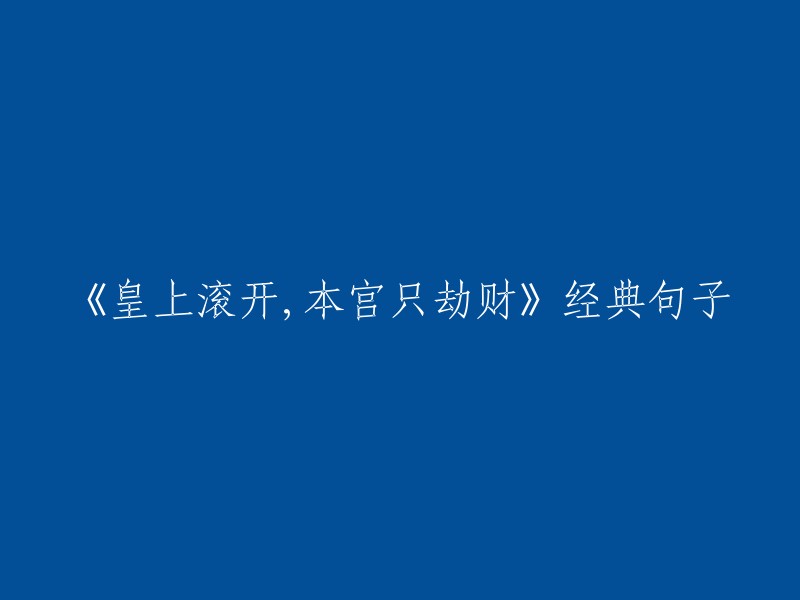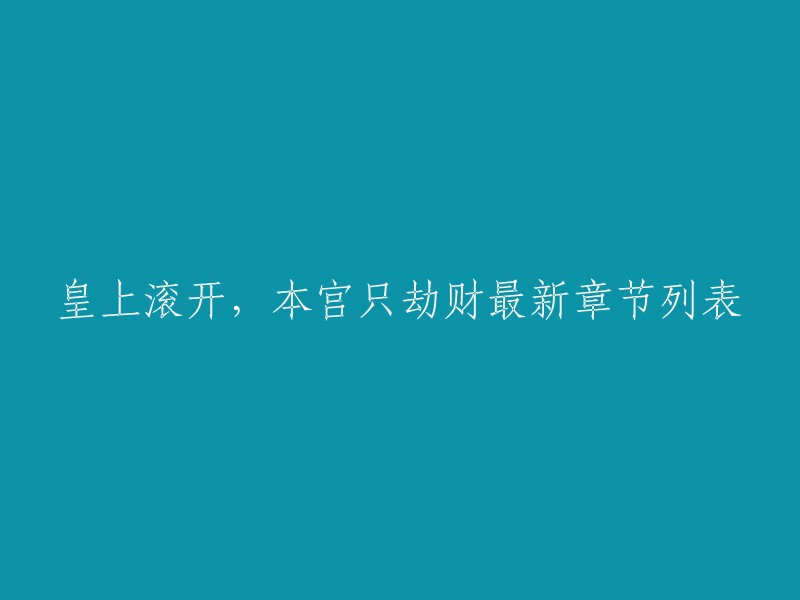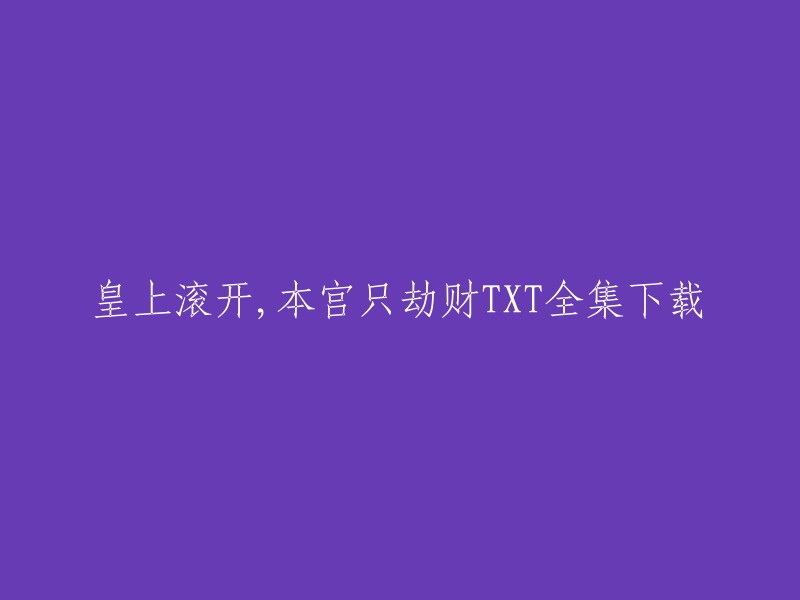心怡将厚重的研究书籍摆放在课桌上,然后偷偷躲到桌下吃零食。老教授不时地向她投去目光,但她似乎并没有察觉。
同桌的晖晖轻推了她一下:“小怡,别吃了,教授在看你呢。”
心怡满不在乎地往嘴里塞了一片薯片:“怕什么!让他看着!晚上我还偷他的讲义呢,让他抓瞎。”她觉得老教授的课讲得太烂了,却还自以为是,真是受不了!
心怡一边认真地吃着零食,一边听着老教授讲课。突然,前台传来一声雷鸣般的喊叫:“心怡同志!”
心怡猛地站起来,身姿笔直、严肃受教,堪称好同志表率:“到!”回答得响亮干脆,就像是一个乖学生。
“你在做什么!”老教授几近光秃的头发又掉了一根。
“报告教授,我正在思考您提出的问题!”她的用词都这么讲究,简直就是尊敬师长的典范。
同桌的李晖汗颜地低下头,他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认识了这个女孩。
老教授推了推鼻梁上的花镜,不相信心怡的回答:“我刚刚讲了什么?”
“古代女子在束缚下的反抗。”心怡回答道。
“你有什么看法!”老教授问。
心怡行了个标准的军礼,面无表情地说:“对不起,我没有看法。”
老教授本就凋零的头发更是稀疏了许多,他把讲桌敲得咚咚作响,可怜了前几排听课的同学:“怎么没有看法!我们已经研究这个课题三个月了,你竟然没有看法!”
晖晖无奈地站起来,温和地对教授微笑,迷倒了一片花痴小女子。教授也被帅哥的影响所感染,稳住了自己越来越狰狞的面部表情。
心怡站着不动。
晖晖开口说:“教授,心怡的意思是,您的看法就是她的榜样,您的......”
心怡不等李晖说完,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我的意思是,从本质上我就瞧不起你的课题。”晖晖无语地看着天花板,坐回原位收拾东西,准备下课。凭他这么多年对心怡的了解,她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那个打扰她进食的教授。
“你敢说瞧不起我的课题!”老教授几近发狂,他在史学界混了这么久从没人敢看不起他的课题。老教授备受打击的头发飘飘落地。
晖晖收拾好东西,那个老家伙也没消火,吃了十几年的亏,还不知悔改,难道那所剩无几的头发也要献给这个不可理喻的女子。
心怡尊敬地对教授行了一礼,口吐气死教授不偿命的话:“那个课题没有成立的必要!”
晖晖悄悄地拉拉她的衣袖,小声问:“午餐想吃什么?”
心怡站姿不变,更小声地说:“回锅肉。”
晖晖点点头,拿起东西奔向菜市场。整个授课厅一半的女士都回头目送他们离去。
我不认同,您说她们受礼教束缚,试问我们现在就不受礼教束缚吗!况且被束缚有什么不好,人活的是本质,不是本性,就应该在道德的束缚下完善自我,往高等生物、变异人种迈进。”
“荒谬!难道三妻四妾也是该忍受的?”
心怡平静地点点头:“教授您用错词了,是接受不是忍受。一个女人从小接受三从四德的熏陶,你认为她能接受一夫一妻吗。你和她讲一夫一妻,我相信她会骂你神经病。”这就好比姜昆的相生中的描述的片段:你说现在的女子性感是褒扬,以前说女子性感是侮辱。如此而已。
老教授气得压根痒:“让你老公娶七八个女人你能接受吗!”
心怡挑挑眉:“教授,我说的是在一种大环境下,现在的理念是一夫一妻,为什么别人老公一个老婆,我的老公七八个!我是个大众化的人,不喜欢玩特殊。”
“让你们裹小脚不残忍吗!”这个同学就喜欢唱反调,偏偏唱的一本正经。
“古时以小脚为美,女人为美丽付出代价是痛苦的快乐。现在人整容比裹脚痛苦多了,你怎么不说他们惨无人道。况且并不是所有女人都承受痛苦,那些广大贫苦群众,还是要下地劳作,抛头露面的,谁有闲工夫爱美,谁有闲工夫裹脚。”
“强词夺理!如果每个人都愿意,怎么会有祝英台女扮男装,怎么会出现花木兰不顺从礼教,怎么会有河东吼狮!”
心怡放倒面前的课本,不在意众女子期盼的眼光,不在意众男子嘲笑的表情,义正严词道:“首先,我要说,祝英台是杜撰出来的,她只是鬼嫁的一例,是作者感性的创作,就算从主旨出发,说的也不是女子行为;花木兰从军嘛,只能怪你们男人种下了祸根,逼得她不得不从军,不是她乐意去的,她是没办法才去的。
没发现她是女子,证明当时女子从军很普遍,如此大规模的女子参军,你们男人不该检讨吗,不该反思当年的行径吗,不该向那个时代为你们扛起一片的女子致敬吗,那是男人的悲哀,应该检讨的悲哀,劝你下次别拿出来自贬。
至于河东吼狮,那是某些人见不得人家幸福,古往今来,多少名人志士奉老婆为上帝,多少名客哄老婆当小孩子,上至昏君,下至黎民,把凶娘子哄成猫的数不尽。
怎么就出了个制不住老婆的白痴,竟然还闹的人人皆知,丢人丢到他姥姥家了,沾沾自喜什么,她不是在反抗她老公,更不是挑战礼教,女子没那么大报复,她只是嫌他老公太傻,脑子不开窍,不会疼人。谁知吼两嗓子他就受不住了,无奈之下她只好出出名看能不能换个壮点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