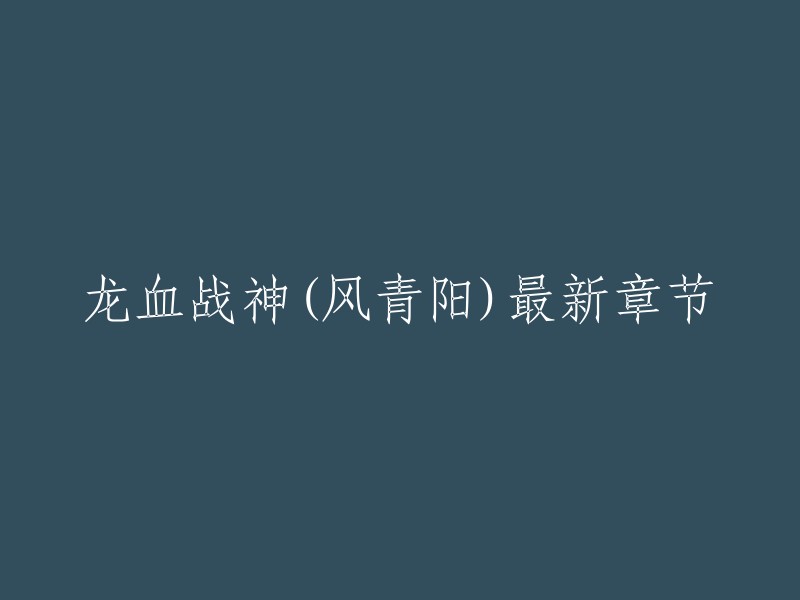《投辖录》和《玉照新志》都是南宋学者王明清治史之余写的志怪笔记。其中,《玉照新志》主要记史事,但由于闲笔多、八卦怪谈风格浓,所以不如《投辖录》严谨方正。唐末到两宋算是中国第三个大变革期,文化普及程度比前代大为提高,生产、商业的发展和人身禁锢的松弛又促成市民社会发达、社会流动性大,所以神怪之说市井琐谈本来就比前代兴盛。南北宋之交,天下板荡兼以局势变化吊诡,状况之极端空前也几乎绝后,于是各种神道段子越发呈爆炸式增长。即使达官贵人方正君子的笔记里,也不免要写上几段。而其中集大成者,大约还要数洪迈的《夷坚志》,王明清的这两本相比之下原不算特出。
总之这其中有非理性的因素在,原理大概和看人差不多,所谓“眼缘”,所谓“惊鸿一瞥”“一见钟情”,人和文字也来得的~ 而王明清平生第一本著述投辖录虽篇幅简短,不过记得几十则逸闻,却偏偏就有两个达到这种“惊鸿过眼”级别的段子。
宣和七年元日,有太学生数人,共登丰乐楼聚会饮酒。都城楼上的酒客坐处,各有小室,称为酒阁子。旁边的阁子里有一位客人,独自倒酒喝到数斗,高歌豪饮,旁若无人,衣冠甚伟。学生们感到很奇怪,于是相继与他揖拜,并邀请他共坐。客人也不推辞,过来前又喝了几斗,谈论锋芒毕露,凡所提问尽出人意料。学生们向他询问姓名。他回答说:“我的姓龙,离家访道,随所寓而安之,也有年头了。”学生们于是称呼他为先生。问他说:“先生的休息之处可听闻吗?”客人说:“在景龙门门外某人家的小府中居住。诸位明早幸能早到那里,恐怕晚了的话我也出去了。”学生们中有如期去拜访他的人,客人果然在那儿。一间房里萧然空寂,一张床榻,一名老仆人,别的什么也没有。他对学生们说:“我也想与各位小酌一番,但旅店不是适宜的地方,我有一天有空,希望与前天同桌的一些公子们同行出郊,为他们设宴送行,是我的心愿。”学生们应诺后就告诉了其他几位同学。到了那天早晨,一起前往叩告老师,客人果然在那儿。让老仆人带着几千文钱出了城门到外面买酒买果品。他们在一二个小花园间畅饮终日,间或用经史没通透的地方问客人,都能迎刃而解。学生们中有自带弓箭自随者,恰逢空中有群雁穿云而过,客人取弓调矢,一支箭射下双雁坠地,学生们又惊奇佩服起来。从此以后,每当有空闲时间便去拜访他,客人总是在那儿。一天,他们一同经过新城县下时,当时土木工程刚刚结束,连绵的楼阁矗立着,客人忽然指示学生们说:“不过一年的时间,这座城将被摧毁。即使是外城也是如此,地面都将变成碎石瓦砾的场地。”说完后叹气不已。这时告密的人已经分布在各条街巷之中,学生们非常惊慌害怕,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却不敢作答。再次领同学们到近郊人比较稀疏的地方去,说:“幸亏各位游历已久,也许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了别人,希望不要忘记。”学生们请求告诉他原因。客人说:“胡骑将要进犯皇宫,天子将要北逃,城破之时大雪纷飞,天下从此就乱了。请诸位不要顾虑升斗之间的计算而舍不得回去,应该各自怀着亲人思念家乡的心情赶快离开京城就可以了。否则的话不是我所知道的那样,我也会从这里离开了。”说完后散去。第二天早晨,学生们再去访问他的居处想探得详情时,那家店主说:“昨天晚上他已经告诉离去了。”学生们认为此事很奇怪,便请求告诉他原因,每人给了长假回到家乡中之后,后来事实全都像他说的那样。我的叔祖父曾任台州公永这样说过他家的仆人这样一句话:后面观察到《华严经》中有龙主鸳盘荼王的故事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个人就是他本人啊!
故事本身其实并不算很新鲜。所谓事后诸葛亮,南宋时人回顾靖康之变也不能免俗。反映到奇谈怪闻上,有诗谶、字谶、能预知未来的异人(有趣的是,异人的营生大多不怎么高端,比如卖鱼的都能来预知一下)、预兆不祥的美艳妖妇、怪异天象等等。看多了会觉得这天机也未免太廉价,简直什么渠道都能露几分。其实多半是后人附会编排罢了。王明清此处记的这个本也属此类,但胜在文字更潇洒有致,人物形象和整体上那种盛景将终、大乱将临的氛围都渲染得更生动。特别是“怪客”将太学生们引到荒郊僻静处时说的那几句话:“胡骑将犯阙,天子当北狩,城破日大雪,天下自此遂乱。”
破空而来的几个短句,一句一个画面感极强的场景,连缀在一起就打开了一幅乱世板荡图卷;而以近于排比的方式一气道出,更使语言如所叙的事情本身一样,痛切而急促;同时又勾连出比东京城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指示着其中更大的灾难:“天下自此遂乱”。确实挺像神示、谶言。但更像事后反顾当初的慨叹。事实上它也就应该是劫后之人追思往事的慨叹。如果说“胡骑将犯阙”还在徽宗朝宣和年间有识之士预见之内的话,那么“天子将北狩”则无疑是再怎么慧眼如炬的战略家也难以预判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在理性之外的、偶然性极大的事件;更遑论“城破日大雪”这种非亲历者不能道的细节了。
引人遐想之处在于,这个段子的原创者——按照王明清所示的信息源和行文语气,这人应该就是宣和末年游学于东京的太学生一枚——为什么会想出这样一个故事来呢?也许他和他的几个同学真的曾经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元日的东京丰乐楼之上、酒酣耳热之际,遇到过痛饮浩歌、心忧国事的逸士高人并与之交游,听他对时局作过某些悲观然而事后证明相当清醒的预测,只是没有段子里写的那么精确罢了——这样的人在南北宋之交还是有不少的,只是未必都能风云际会扬名青史(当然若附会到某个名人身上好像也不错);也许就是他们自己在当时已经对国事失望透顶又投效无门,只好转觅退避之途,结果没想到真的半蒙半算的避开了战祸,于是干脆演绎出一个世外狂客的形象寄情伤时;也许他们只是纯粹巧合的撞了大运,但是事后有劫后余生的同辈感叹之余追问何以远见如此,遂只好伪托鬼神来自抬身份兼以自解;也许前述这些猜测都在实际中发生过,然后在编故事的人嘴里被烩在了一块儿......
张中孚和张中彦兄弟是南宋初降金将领,他们投降金朝,充当金军先锋,相继攻占熙(今临洮)、河(今临潭)、阶(今武都)、成(今成县)等地。张中彦字才甫,张中孚的弟弟。年轻的时候,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宋朝为官。担任泾原副将,掌管德顺的军事。金睿宗进军陕西的时候,张中彦投降,被金任命为招抚使 。
至于你提到的故事中的“城破日大雪”,我无法确定它是否与张氏兄弟有关。但是,这个故事最初的作者可能会想起发生在雪中的这种种酷虐、荒唐、凄惨、绝望和悲壮吧?
己未岁,虏人入侵河南故地,大将张中孚、张彦兄弟自陕右来朝行在所。道出洛阳建昌宫故基之侧,与二三将士张灯夜饮于邮亭。忽有妇人衣着奇特,姿色绝美,执役来歌舞于尊前,曰:“晓星明灭,白露点,秋风落叶。故址颓垣,荒烟衰草,溪前宫阙。长安道上行客,念依依旧,名深利切。改变容颜,消磨古今,陇头残月。”中孚兄弟大惊异,诘其所从来,不应而去。(张仲益所云)
这一则怪谈虽短,但简直是我目前看过的聊斋风记事里最美的一篇,苍凉艳异之致,对文字稍有感觉者即可凭想象体会,原本不需再加铺陈。只是还是忍不住要铺陈一下:洛阳自是汉魏以来的千古名城,在北宋时期地位极显赫。既是四京之一,又毗邻宋帝陵寝。同时还是当时大儒名士乐于结庐闲养的所在。因此本就兼山水之美的古都,又添甲天下的园林之胜和荟萃人文。就连衣冠礼俗也异于他郡而有唐时遗韵,比之汴梁别是一种风致。神宗朝时更因朝堂政争在此聚集了多位反对新法的名臣。于是政治地位与人文气质之特出更为显著。文采风流冠绝于承平岁月。直到南渡后著名诗人陈与义、朱敦儒等人的诗作里还隐隐有遗韵与回响。
但这都是靖康之变之前的事了。靖康之变北宋覆亡后金人屡次南侵。洛阳所在的京西北路和毗邻的京西南路因为地处中原腹地战略位置重要成了战乱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不仅洛阳的宫阙园林尽毁于兵火宋帝诸陵被损毁盗掘甚至周遭的虢洛至襄阳一带也是“长涂莽莽杳无居民”“墟落尤萧条虎狼肆暴”。
张中孚和张中彦兄弟是南宋时期的将领,他们曾经在金朝担任重要职务。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约和后,河南、陕西归还南宋,两人降于金及伪齐。后来,伪齐覆亡宋金议和后又重归于宋。在他们降于金及伪齐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在临安朝见途中邂逅了一位不知何所从来何所归的佳人 。
天会八年,即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宋金在陕西进行了著名的富平(今陕西省铜川市富平县)大会战。当时宋军兵力占优,但因当时川陕督抚大臣张浚的荒唐指挥而惨败,一溃千里。金军乘胜进兵,围困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而时任渭州守将的宋西军泾原军统制张中孚,刚刚在富平大战之前川陕督抚大臣张浚的人事整肃中挨了处分。孰料曲端的判断转眼就应验成现实,身陷重围的张中孚思前想后,怨恨不平之气难免加倍;同时张浚空降的泾原军新统帅刘錡,张中孚又“素轻”之;而稍早些时候,张浚心腹幕僚刘子羽假手孙恂整肃富平之战中率先溃阵的西军环庆军时,又因措置过于峻急,导致环庆军统制慕容洧率军叛入西夏,张浚命刘錡领兵弹压,却迟迟不能下;当然最糟心的,大概还是张中孚深恶的张浚,在富平大败后居然还好好的待在川陕督抚的位置上。
局势糜烂如此,人心离散如此,富平之战前就已经“颇不悦”的张中孚哪还能有坚守孤城血战到底的心志?遂献城降金。而张中彦是张中孚兄弟又素来相友善,见兄长已经降金,也很快有样学样。所以这两人其实是因私怨和畏敌才投降金国的。只是说起来二张也算簪缨之家出身的宿将,降金前也曾屡与金军血战;而且两人的父亲张逵就战死在靖康初年的太原保卫战中。
张中孚、张中彦兄弟入觐天子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张中孚、张中彦兄弟在金国时期就已经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而且他们的父亲也是一位有名的将领。但是,当他们投降南宋后,却被南宋政府贬到了一些偏远地区。因此,他们想通过这次入觐天子的机会,向南宋政府表达自己的忠诚和期望。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张中孚、张中彦兄弟想要通过这次入觐天子的机会,向南宋政府表达自己对金国的不满和愤怒。
个人怀疑,张中孚和张中彦兄弟虽然因私怨而叛国降敌,但他们仍是降将中较有才干和见识的。在绍兴九年,这样的人应该能看出宋金之间的和议并不稳固,新掌实权的四太子完颜宗弼随时会毁约南下;同时也一定能看出金国国力已衰,宋金之间的强弱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当时的金国不但依旧不能消化宋金开战初期吞并的关陕、两河和中原地区,不管是张氏兄弟这样的一方军头,还是河东韦铨那样依山结寨、“虽力屈就金人招,而据险自保如旧”的民间抗金义军,都只能是“无如之何,覊縻而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7),而且开国宿将凋零、军队士气低落,统治集团上层的倾轧内斗一次比一次血腥,经济上一系列旨在推行奴隶制、聚敛财富的政策也乖张失措,逼得本就人心思宋的两河百姓更加怨望深重,纷纷投入反抗者的行列。
然而,踏着亲族鲜血新掌大权的完颜宗弼却对此浑若不觉,完全不认为完颜昌促成的宋金和议是给金国捡了大便宜,反而依旧做着吞并南宋一统天下的迷梦。在这样的局势下,宋金之间若重新开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张中孚张中彦心里恐怕难免会有些盘算。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绍兴九年宋廷答复张中孚入觐请求的诏书说“伺春暖起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张氏兄弟却直到当年深秋才动身。
实际上,绍兴九年正是完颜宗弼发动政变诛杀主张对宋约和的完颜昌一党的时候。这大概就是《投辖录》中记的这则张中孚兄弟洛阳道中逸事的全部背景。
因此,在推想这则故事的编织过程时,我十分怀疑那位古妆美人所唱的小词,其实是张中孚的自作。这个原本出身良家子、文武双全又颇有威望,最终却屈膝而事杀父仇虏的乱世武人,在绍兴九年的深秋,怀着不可与外人道的心事千里间关赴故国行在朝见。当他行过当年的大宋西京府时,看到昔日名城被兵火摧残的惨状还历历如昨,而烧起这战火的元凶——女真人及他们所建的金国,却已经乱象纷纷,暮气沉沉了。不到十年,时势之易竟迅忽如此。然而金人固然已经衰落,故国今日气象到底如何,他虽然做出了初步的判断,甚至还进行了相应的行动,却也还不能完全确定;同时宋金之间的战火看似已停歇,但稍微明白点儿的人,都知道战争的乌云并未远去,相反正在不远处酝酿着更为酷烈的风暴。
张中孚和张中彦是北宋时期的将领,他们曾经叛国降金,后来又重新归顺南宋。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记载,张中孚、张中彦兄弟于绍兴九年深秋动身赴阙,到次年正月才到达临安正式朝觐天子。而宋高宗似乎很欣赏张中孚,完全不以其屈节事敌反复无常为意,“命坐甚渥”,封赏亦优。张中孚还为自己的父亲、当年战死太原的张逵请封,宋廷也允其所请,到绍兴十年秋还特地“加赠开府仪同三司”。
但这是后人翻着史书八卦的态度,在时人看来,就简直不可理喻了。张氏兄弟再怎么知书达理恭谨能干也终是叛国降将,如今只因金国归还故地才复为宋臣,却厚待如此,这让当年宋室垂亡之际辛苦撑持、百战余生的将士怎么想?别说军人,就是普通百姓士人也难免不平,所以很快有人为这两兄弟作了打油诗:“张中孚、张中彦,江南塞北都行遍,教我如何做列传?”“市人行坐皆道之”。
根据我找到的资料,张中孚、张中彦兄弟归宿如下:
1. 张中孚任行台兵部尚兵、行台参知政事、尚书左丞等职,封南阳郡王。
2. 张中彦任靖难军节度使、凤翔尹、庆阳尹、彰德军节度使等。
事实证明两人的判断是对的。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兀术果然来信索取张中孚张中彦兄弟北归,南宋朝廷也果然不敢挽留,在当年十一月给张中孚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张中彦靖海军节度使后,礼送二人北返。张氏兄弟还归金朝后,继续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其中张中孚入金后没有回关陇,而是行至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就被兀术命为兵部尚书进入中枢,后来做到参知政事,完颜亮登基后始告老归乡,犹被屡屡加封王爵,未几病逝,享年五十九岁。张中彦则仍回渭州老家任职,历仕熙宗、完颜亮、世宗三朝,在世宗朝还一度出关中任南京留守、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等职,后致仕西还关中,以七十五岁的高龄荣宠而终。兄弟两人由塞北而江南而又塞北,居然一路风光,风评官声也不算差。修金史的元代史官(实际很可能是金国遗民)都忍不住感慨两人“金以地与齐则甘心臣齐,以地归宋则忍耻臣宋,金取其地则又比肩臣金,若趋市然”(金史卷79卷末)。虽是贬笔嘲讽,却分明也有惊叹之意在其中。
然而这样的“风光”人生,就是张中孚兄弟当日所愿的全部么?金末诗人元好问所编的《中州乐府》中收录了张中孚一首【蓦山溪】词。这首词似乎是张中孚晚年告老还乡时作于途中的。清丽中富沧桑之意,风格与《投辖录》所录的那句“晓星明灭”极为相似。其中“萍梗落江湖”“往事知多少”几句似乎带过了词人当年远赴临安羁留故国的三载光阴。只是语中情绪似厌倦不耐但又不全是。依旧是欲说还休晦暗不明。一如那个洛阳道中遇佳人的逸闻背后若隐若现的纠结心绪。
张中孚在落笔写下这首词时,多半真的会再次想起数年前洛阳城里的那个秋夜,想起之后自己在临安度过的三年吧。毕竟他与其弟闲居临安的那三年,正是南北形势变幻最惊心动魄之时。然而怒潮惊雷之后苍黄颠倒,到绍兴十二年,他很可能一度暗自判定运数将终的金国,居然在大败之后还能利用当年安插在对方的间谍,逼着对手签订己方占尽便宜的和议,绝境回生;他当年深恨的重臣张浚,此时已经被一贬再贬,而且在秦桧的严密监控之下随时有倒更大霉的可能,但倒霉的原因却不是张中孚所憎恶的无能、刚愎、屡坏大计,而是反对与金议和;他一直瞧不起的公子哥刘錡,此时已经被天子宠臣和顺昌大捷的光环笼罩,但却仍然不免被剥夺兵权远贬江湖的霉运;他昔日在泾原军的同袍和后辈,一直被称为“吴家小帅”、似乎总处于兄长光芒遮蔽下的吴璘,如今已经是能独当一面的名将,并且也在这一年春天自关陕远赴临安朝见,却不得不一面打起精神小心应对刚刚大开杀戒的天子,一面忍受自己曾浴血守卫的大散关和兄长吴玠的葬地被划归金国的痛楚;当然最令他心惊的,大概还是他在这几年间屡屡听闻其声威、甚至可能曾在绍兴十年、十一年的临安某地与之碰过面的、那个年纪比吴璘还要小的岳飞,最后的结局,居然是被自家朝廷定为逆臣明示典刑。——同为乱世武人,同样经历了国破家亡积年血战之后,一直扶保炎宋旗号的,或死于非命或投闲散置或精神上饱受打击,没几个过的舒心;反而是他和自己的弟弟,两个背负投敌之耻、并且马上又要北归敌国的降将,正被宋廷再次加官进爵恩赐荣衔,以示优待礼敬,以及对大金的臣节之诚。
如此得意与失意的对比,会不会连张中孚张中彦自己都觉得荒唐?而比眼前这一切都更荒唐可笑的,难道不是三年前那个主动要求间关千里赴故国行在朝见、“念依旧”、“名深利切”的“长安道上行客”吗?不过不管是金史还是宋史,都不会有什么兴趣去探究和记载张中孚兄弟彼时的内心感受了。这两兄弟确实有才干,人品亦有可称道处;但显然眼光胸怀都极有限,真正在意的其实只有一己一身之得失。所行恩惠也好业绩也罢,不过是在不至威胁自身荣华的前提下顺势而为罢了。所以张中孚说自己是“萍梗落江湖”,倒也准确。但既是浮萍逐浪、不能力挽狂澜亦不能砥柱中流、甚至连洁身自好都做不到、那么心里有过什么样的挣扎、犹疑和感触、也都不重要了。历代历朝青史斑斑、最看重的永远是大是大非大局大节、一生行止、而不是文章言辞或者一时所思。
这一点,也算是半个读书人的张中孚自己心里多少有些数。所以当他在临安与旁人谈起朝见之事,或者忍不住唱出八成是他自己所作的那首小词时,他干脆隐匿了一切有可能指向自身的、现实的细节。最终,只留下一个神怪异闻一般奇诡幽艳的故事,以致在自己和弟弟北归金国后,依旧流传于南朝士人之口,最终又被热心搜罗南宋初史事的王明清记载在《投辖录》里。
然而,再荒诞不经的创作,也终难洗去所有现实的烙印与投影。所以千载之下,当略知这两人生平和这段历史大概的人翻开《投辖录》里的这则怪谈时,仍然会觉得故事里那衰颓的城池、飘摇的烛光,迷蒙的夜色、幽梦一般来去匆匆的美人歌舞背后,分明是张中孚兄弟自己飞蓬浮萍一样的人生与明晦不定的心迹。而绮丽容颜、婉转歌喉和荒寒之所、凄冷之词所成的反差,也恰如那个时代中诸般人生轨迹的对比一样,鲜明的令人感慨,也令人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