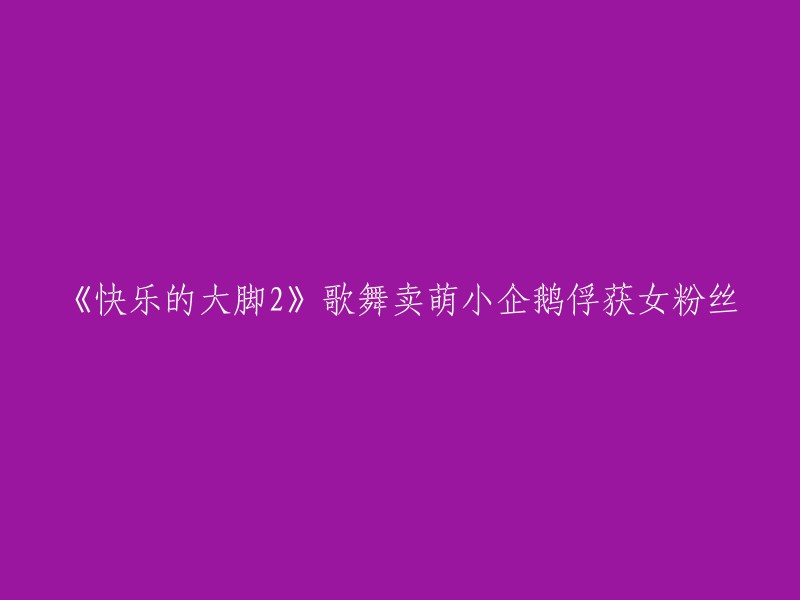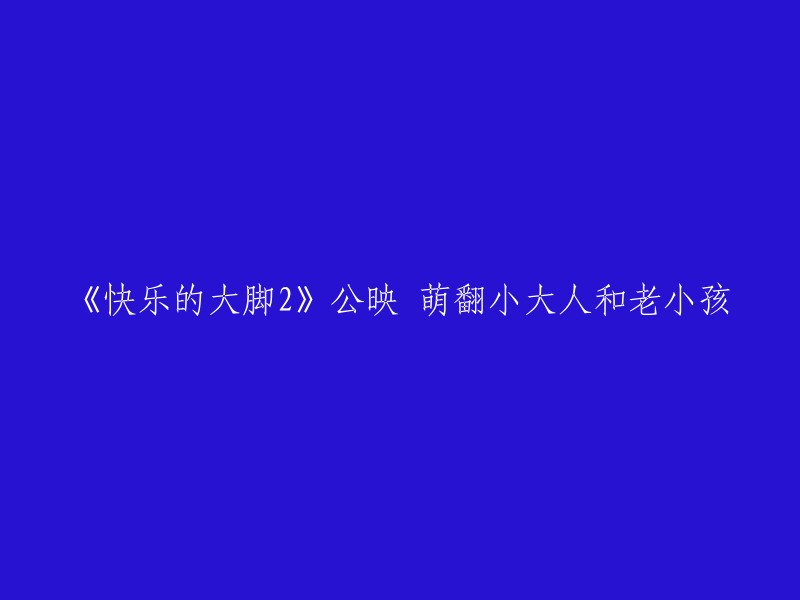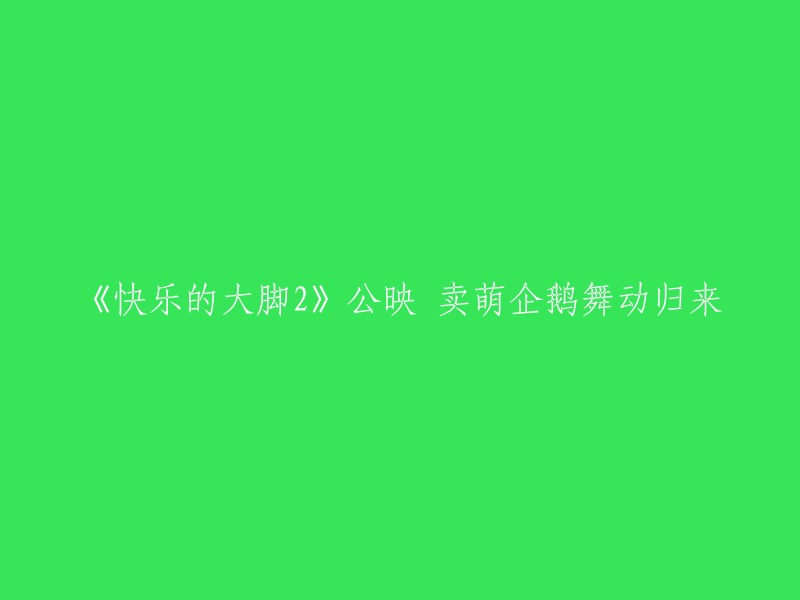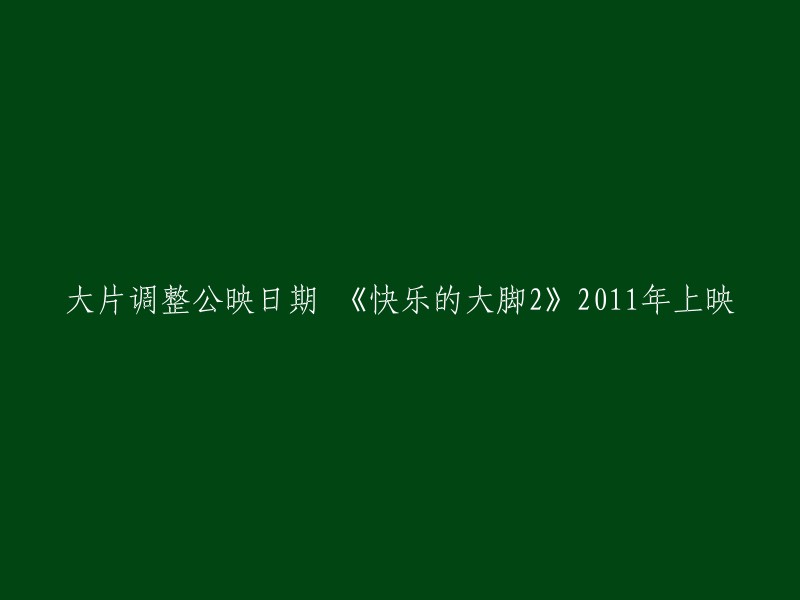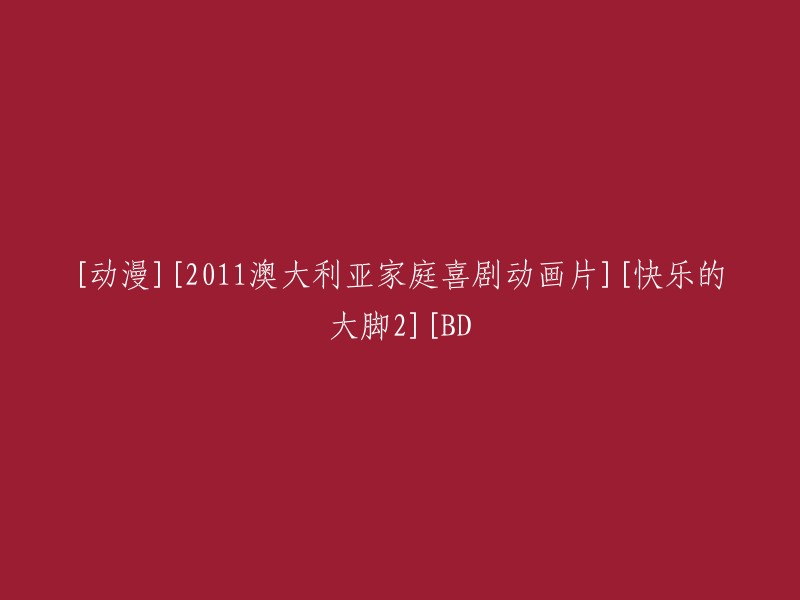放羊的星星
作者:马睿
有一天,爸爸对女儿说:“狗娃,你再不操心念书,写字拖拖拉拉,我就在乡下咱们的哪旧庄里给你收几只羊,你就一个人去乡下放羊去。”女儿担心地问:“爸爸,那我去乡下放羊的话谁给我做饭呢?那晚上我怕是一个人不敢睡啊!”爸爸回答:“就你一个人自己做饭,你一个人睡么,都要到乡下当羊倌了还想让爸爸妈妈陪着你?”女儿想了想,又提出一个要求:“噢,那爸爸,你把咱家那房子改造一下可以不,就给房顶安块玻璃。”爸爸疑惑地问:“安块玻璃?为啥呀?”女儿天真地说:“爸爸,那样的话我一个人睡就不害怕了,我可以透过玻璃看天上的星星。白天放羊,有羊可以和我说话。晚上睡觉,有星星陪着我......”
父女间这段以教育为话题的谈话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很明显,父亲的威胁没有起到作用,稚嫩的女儿根本没有理解父亲语言中的威胁成分。可一段关于放羊、星星的情绪却如雨后的野草一般在父亲的心中疯长了起来。
放羊
生长于农村的孩子大都有放羊的经历,当然我也不例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虽说已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了包干到户(俗话说的单干,即从农业合作社分离了出来,劳动积极性大幅度提升),可饥饿、贫穷仍然是禁锢在农民头上毫不松懈的钢圈。穷则思变,养羊几乎成了每个农户改变面貌的好出路,因为羊毛羊绒可以换钱,羊粪可以煨炕,更主要是要是遇个啥事儿,羊买掉可是会有大用处的。
一九八八年,我八岁,家里养了几只羊,宝贝的不得了。那时我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放羊成了我上学之外的主课,下午放学、周六、周日、寒暑假。约三五伙伴,将各家的羊伙在一起,上山下河,跋山涉水,羊儿悠悠,我亦悠悠。
春风拂面,赶羊上山,我拧几管柳笛横在嘴边,变出几种音调。羊儿撒欢,飞扬跋扈,啃几口刚探头的嫩芽。夏雨潇潇,领羊下河,河滩宽敞且多草,羊儿吃得忙,我等玩得也忙。找一处浅水,憋气、下水,其实水只能没到肚脐眼,戏水就不能谈了,只能说是和泥水了,狗刨是最标准的动作。遇到有大人经过,还要藏在水里,憋气,不敢露头,不时会因呛水而咽下小蝌蚪。
秋风习习,暑气未消,家人收割粮食繁忙,月朦胧之时正是羊儿吃草的好时节。宽敞的田野里羊儿疯狂地饕餮着美食。三五伙伴,相互合作,于高处挖一深坑,捡些许柴火,偷一捧洋芋,点火、烧土、掩埋。不多时分,洋芋的香味透过泥土喷入鼻孔,抢、夺,当然有时也很文明,勿论生熟,也算是饕餮了。冬雪皑皑,一片洁白。找一晴朗的天气,赶羊出门。撒蹄跑,赶紧追,或于山坡,或于涧畔,喘着的热气似乎化开了脚下的积雪。悠悠然天地苍茫之感,当然那时只觉得好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也只是后来的感觉。
十二岁那年深秋,赶羊出门时浓霜已将田野变成了肃杀场,羊儿忘情地吞咽着被霜浸染的短短的苜蓿。我则忘情地看着手中的小说。突然传来八声响亮的敲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八只羊全部躺在地上,肚圆如鼓。庄里的羊把式全被我凄厉的叫声召唤了过来......无救。永远忘不了母亲那绝望的眼神以及那眼泛泪花仍安慰我的话:“闲着来,狗娃,别害怕,羊胀死了咱还能换钱......”。我断了全家的财路,十二岁的孩子好像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羊儿从此再未走进我家的门。
天上繁星点点,哪颗最亮呢?像妈妈眼睛的那颗最亮。农闲时分,夜空下乘凉于院子中指着天上的星星问个不停。牛郎、织女、北斗,故事、知识。迄今为止,我对天空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妈妈讲述的故事里。至今仍然很羡慕那个数星星的孩子。上学时家里穷困,妈妈每天早上都要做早饭。在没有钟表的岁月里,鸡鸣和星星成了最好的时光机。妈妈说如果一个人上学路上走要不时看看星星那是她让星星代她陪伴着我就不会怕。我知道妈妈没有骗我因为我真的找到了那颗星我们一起走她也跟着陪着我看着我我真的不怕真的我不怕!
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一定是你最思念的人的眼睛因为每个人升天后都会在天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我知道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因为我在天空中找到了那颗星它一直看着我放羊的星星爸爸问我:“狗娃你真去乡下放羊吗?”
女儿:“爸爸,虽然我不想去放羊,但如果你让我去,我就会去。不过,房顶一定要安装一块玻璃。”
父亲:“是啊,安装一块玻璃,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星星了。”
孩子:“爸爸,你可知道吗?我看到的星星也一定是那夜空中最亮的,因为那是爸爸妈妈的眼睛在看着我放羊。他们就像是放羊的星星一样。”
父亲:“孩子,你可知道吗?其实爸爸也很想去放羊,我也想看到星星,更想看到那放羊的星星。”
星星:“放羊的星星啊,星星。”
“星星。”
大家都在注视着这对父女,以及那闪烁在夜空中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