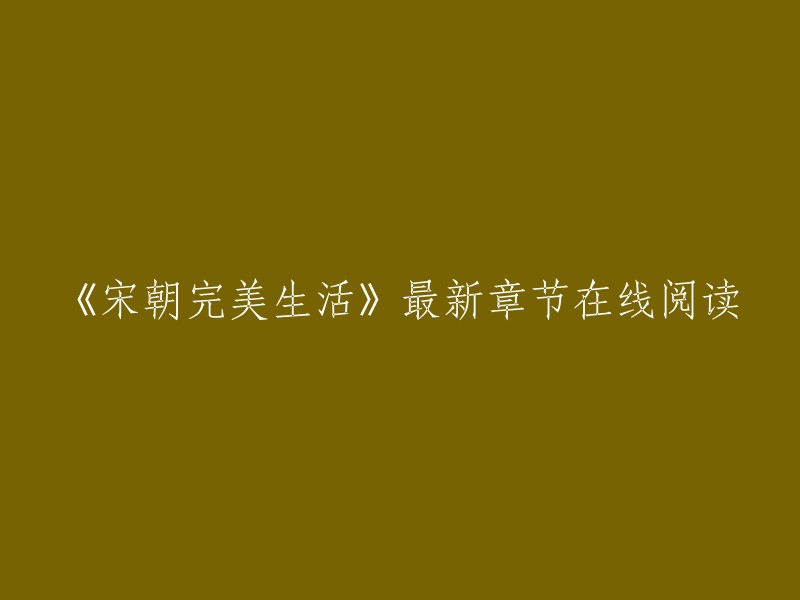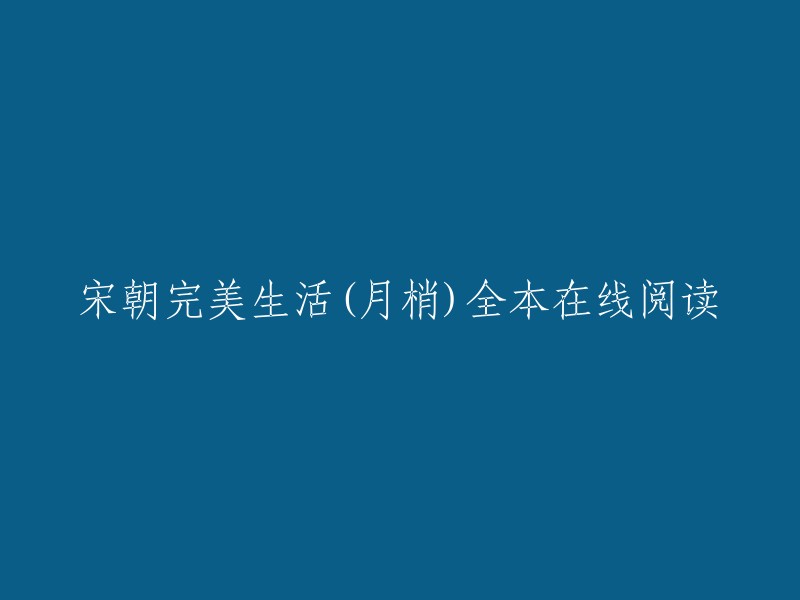骄阳当头,大地却如蒸笼一般,湿气甚重,万物好像蒙上了水汽织成的薄纱,连枝上蝉鸣也不似往日的欢快。沐清站在屋子门口,看着院子里蹲着的黄狗嘴巴大张不住地吐着舌头散热。她挑衅似的用力地挥动着手里的团扇猛扇,“呼哧呼哧”发出不雅的声响。再对上望过来可怜巴巴的狗儿,沐清不禁暗笑,幸好当初没投到畜生道,不然这鬼天气披着那身毛,还不得热死。
只站了一小会儿,沐清就觉得身上冒汗,赶紧摇着扇子进了屋,端起案几上的酸梅汤一口气喝了起来,一碗下肚,顿时畅快了许多,“用冰镇过的,喝着真痛快!”一低头,发现案几上还有个瓷盘盛着果子,是配酸梅汤用的,她不禁笑道:“还是碧烟贴心,怕我口酸。”说着,端起盘子端详,看看里面一粒粒乳白色沾着糖霜的莲子,沐清突然有些失神,低声呢喃着:“糖莲子......唐心......”
唐心!许久不说这名字了,沐清都觉得有些陌生。三个月前,她爬山时不慎跌了一跤,醒来时就发现躺在陈家东厢的床上,直到母亲钱月娘扑上来,哭天抢地喊“沐清”,唐心才意识到自己穿越了。记得当时,父亲陈愈见她像不识的人了,还备了厚礼专程请了丹棱的名医来给沐清看病,最后大夫说身体无恙,怕是高热烧坏了脑子,所以不记事了,得慢慢调养,旁人引导方可恢复。后来她才知晓这陈家六岁的独女沐清是因被人错绑,受了惊吓,回来后就高热不退昏迷不醒。等过了五日,退烧醒来的却是从二十一世纪穿越来此的唐心。
“天禧四年......”从钱氏口中知道这个年号时,唐心大窘,她不是文史通,连个年号都记得一清二楚,自然不知道自己穿到了哪里,幸好后来听京城里来的商人和父亲谈起过什么天祺节,纪念皇帝降天书,才反应过来自己到了造神皇帝宋真宗统治的年代。
陈家祖籍杭州,父亲接了族里的在蜀中茶叶生意,定居眉州丹棱五年有余。前世唐心本就是个孤儿,父母去世的早,从小寄养在舅舅家里,舅妈待她不好,舅舅又是个妻管严,不过念在死去的姐姐份上,还是偷偷攒了私房钱供她大了大学,后来,她就全凭写写画画的功底搞设计赚点外快交学费。毕业了,进来咨询公司做物流项目,好不容易混出点名堂,却出去玩时不小心丢了性命。
穿越来父母的疼爱让她体会到了久违的亲情温暖,那点初来时的彷徨无措、鸠占鹊巢的愧疚也随着陈愈和钱氏细心呵护慢慢消散。自此,她便以沐清的身份活了下来。
沐清收回了思绪,目光落在那盘糖莲子上,伸手捏了一颗放进嘴里,甜蜜可口。无论是唐心还是沐清,只要她能够活过来,就会珍惜这平静而甜蜜的日子。
正在这时,竹帘晃动了一下,一个穿着翠绿色衣裳的少女走了进来,大约十五六岁,梳着双丫髻,脸上洋溢着春风般的微笑。“小娘子,杭州来信了,四爷说过些时日就要启程回杭州。”
“碧烟,看你这么高兴,是想家了吧?爹可说了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回杭州?”
碧烟看着沐清额头上的细汗,连忙用帕子为她擦去,取过团扇为她扇风,“听说是因为老太君七十大寿,家里来信说要让四爷带着家人回杭州祝寿。”
“祝寿?”沐清将一颗糖莲子扔进嘴里,边嚼边说,“这段时间娘一定会很忙!也不知道现在的杭州是个什么样子?对了,碧烟,你有没有问过送信的人家里的情况?”
“哎呀,这次是大老爷家的恕二爷和何掌柜过来的,我哪敢多问啊?!”
“嗯?恕二爷,何掌柜?”沐清愣了愣,拍了拍手上的糖霜,低声呢喃道,“奇怪,这事有点不对劲......”
碧烟不解地问:“小娘子,你怎么了?”
“没事,走吧,去看看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小娘子,你才多大点人,能帮上什么忙?小娘子......唉!”碧烟还没回过神来,沐清已经出门去了。
沐清一路小跑到母亲房门前时,屋里陈愈和钱月娘夫妻两个正在说话。
沐清停下脚步,趴在窗边不再往前走,只听见陈愈气恼地说:“也不知道沐清被绑架的事情是怎么传到杭州的......他们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打着老太君的幌子。只怕这次回去,短期内不会回蜀地了。”
“这么多年都不让我们回去,这次突然来信说老太君想念曾孙女。那些人到底有什么心思?以为别人看不破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房眼红这两年生意有起色了,撺掇老太君让恕二来替你。当初我就劝你要留一手,你偏偏不听,非要做出个样儿给家里人看。可是爹他老人家怎么也没提前派人来知会一声,就这么看着大房明抢?”钱氏有些疑惑。
“爹?他什么时候关心过家里的吃穿用度?整日里沉迷于那些古董珍玩,兴致来了画上几笔。唉,谁知道大伯又给他许了什么好处。三哥在外做官,五弟还要进学,上下打点、日常花销都指望公中分下的例钱和那几处庄子、铺子上的进项哪里够?既然家里人都不说,我便放得干干净净,遂了众人的愿!谁愿意背井离乡?还不如守着几亩薄田、侍花修竹、逍遥快活!”陈愈的话里充满了无奈。
“算了,别生气了。自己身体要紧。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还是先准备寿礼、行装吧。等回到杭州再从长计议。”钱氏安慰道。
“哎!也只能如此了,老太君的寿礼就劳烦娘子费心了,再找个先生算下出发的日子。这几日我还得把铺子里的事情跟恕二交待清楚。沐清那边,你也得和她说说家里的规矩。”
听到这里,钱氏面色一黯,陷入沉默。
沐清见钱氏半晌不说话,神色有异,就知如她所料,陈愈夫妻在本家时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她扯了扯钱氏的衣袖,“娘有什么烦心事?”
“哪里有?娘没有烦心事!”钱氏抚了抚沐清有些凌乱的额发,“等回到杭州,沐清要见到祖父母,叔伯们,还有兄弟姊妹,平时娘教导的礼数要谨记,莫在人前失了礼数。省得吗?”
沐清点点头,“省得了!沐清刚出来跑得急了,现下渴了,跟娘讨碗莲子冰糖水喝!”沐清不适时宜地打断了钱氏的话,挥着小手扇风。她晓得若是让钱氏再说下去,指不定又要唠叨到几时。
钱氏从瓷盅里倒了碗糖水递给沐清,“给!今个午间许你多喝一碗。你身子底子薄,即便暑热难退,这冰镇过的糖水你多喝无益。”
沐清着实渴了,捧着碗,“咕嘟咕嘟”地大口喝起来,钱氏无奈地笑笑,“哪里像个女儿家?以前也未见这般跳脱。也怪我见你大病初愈,这几个月没拘着你好好学规矩,倘若回了杭州还这般,只怕有人又要嚼......”钱氏顿了顿,不知想到了什么,低声呢喃道:“你若是个男孩,也许......”
沐清喝完了碗中的糖水,笑着打断了钱氏的话:“多松快一日是一日,娘您不必担心!”她舔了舔碗边,然后砸吧了几下嘴唇,“沐清回了杭州自会守规矩,不让别人说三道四。”
钱氏微微一愣,自己的女儿真的长大了,心思也通透了。自从那场大病之后,女儿的变化就显而易见。原本有些迟钝的女儿病愈后像换了个人,口齿伶俐,也没了六岁孩子的胆小怯懦,还主动要求开蒙习字。即便平日里偶尔玩闹,却好像会看人眼色,决不再人前失礼。不是身材、长相、身上胎记样样对上,钱氏还真以为自己认了别人家的孩子回来。陈愈见她患得患失,笑着说她看孩子憨顽,担心,现在开窍了,她还担心,真真是杞人忧天。
钱氏后来想想也许是当初自己没有看护好女儿,害她无辜被绑,才让女儿受了刺激,一下子长大了。再每每见女儿善解人意,她就不免生出愧疚之心,心酸伤感之余,却也甚感欣慰。
钱氏现在想来,女儿也好,男儿也罢,如今都是自己的孩子!即便当年是个男孩,只怕在有些人眼里也没有多大分别。该面对的总要面对,自己又何必再胡思乱想,自寻烦恼?现在有个贴心的女儿比什么都好!
沐清不知钱氏心思转到了自己身上,夹了桌上的果子吃,还嘟囔着给钱氏讲闲下听来的趣事。钱氏心事暂时疏解,也与沐清一起说笑,母女俩个其乐融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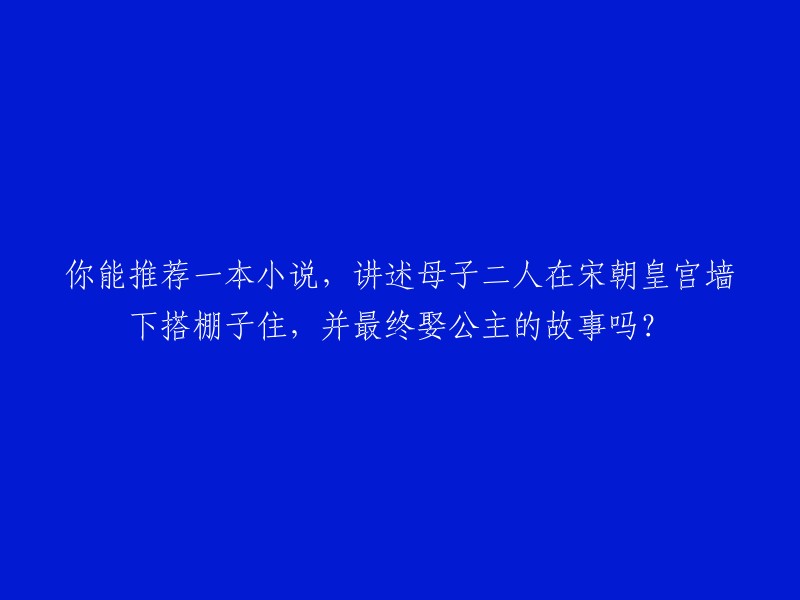
![宋代称谓与排行:完美生活的宋朝象征[转载]"](https://er5-1251572603.cos.ap-shanghai.myqcloud.com/uploads/202410/24/a13a320e77fbc38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