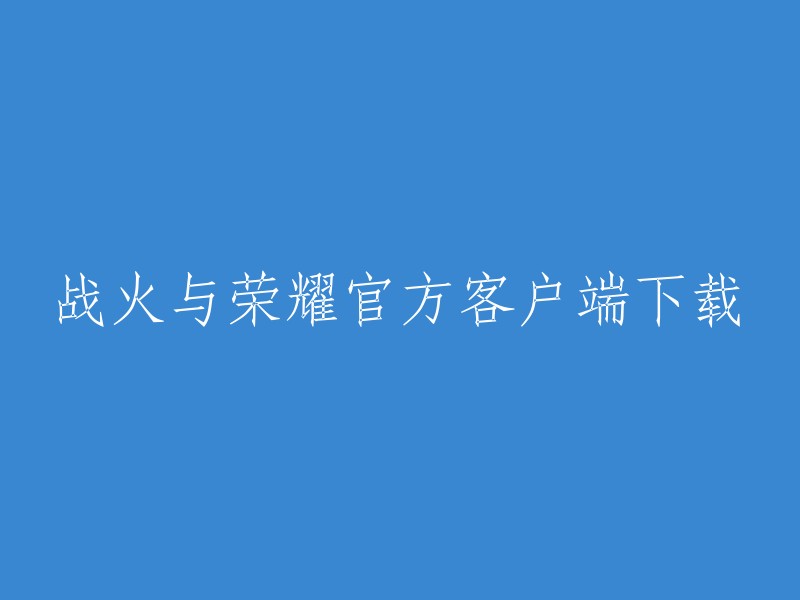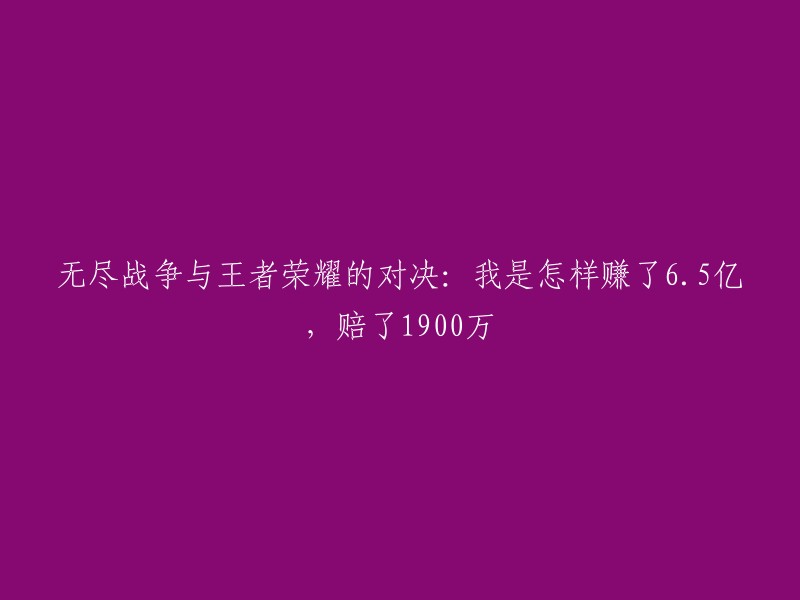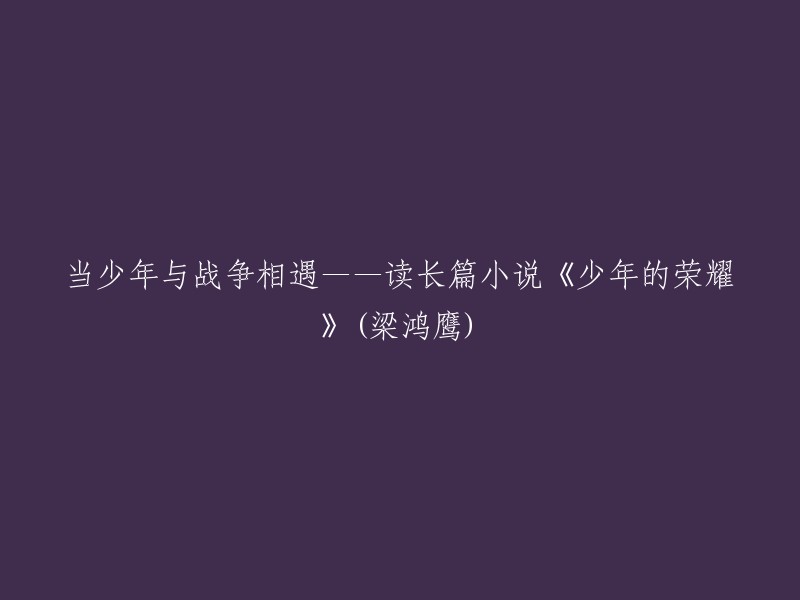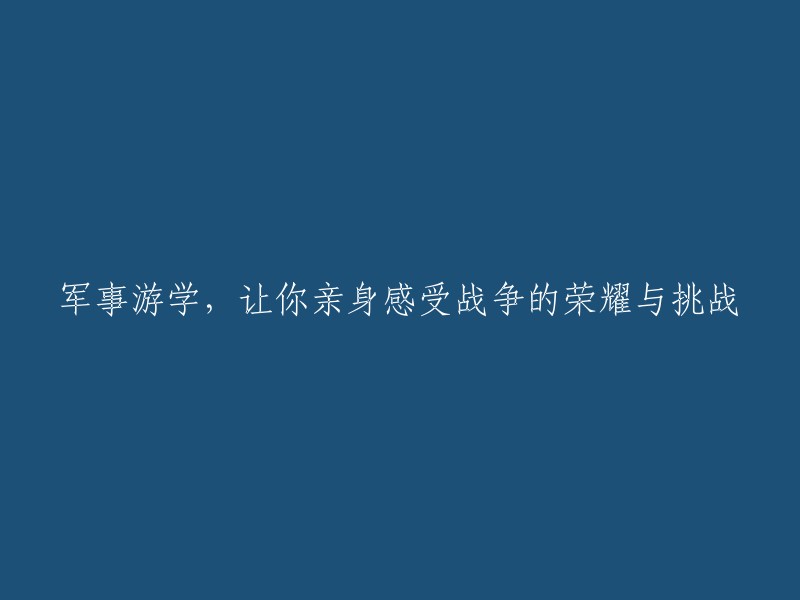悟空,一位叛逆的形象,在《西游记》中以皈依的方式隐遁。然而,通过电视剧集的肤浅描绘,他的形象被普遍认为是神通广大且嫉恶如仇。他对于任何妖魔邪祟都带有处女座式的精神洁癖和疯狂偏执,时刻挥舞着金箍棒,恫吓那些企图对他身边的白嫩僧人进行肉体占有的人。实际上,悟空作为直男,他的情欲被忽视,逐渐形成了一个呆板的形象。戴荃的《悟空》则实现了对悟空形象的重构与情欲再造,描绘了一个从精神流浪到情感皈依的过程。
另一方面,高瑀的《五百年的孤独》将悟空塑造成一个孤独的流亡者形象。这个灵魂正在义无反顾地向前疾驰,自我放逐源自深沉的情感迷思。悟空拥有通天彻地的绝世身手,但这也决定了他与世俗情欲的天然隔绝。他的身份焦虑与伦理危机通过对他降世的童话般的表述来消解。多年以后,站在小雷音寺的大雄宝殿前的悟空可能会想起积雷山上那个智慧无限、略微唠叨的人对牛鬼行刑队说的话:“人有人他妈,妖有妖他妈,请问你妈贵姓?”这句话揭示了悟空与三界生物的根本性差异,使他陷入身份悲情。
此外,悟空在宇宙时空中的永恒性与无限性让所有标榜永恒的情爱在他所经历的时间中变得可笑。经过千帆过尽,悟空对爱与欲的本质产生了朴素的疑问。他对所有关于永恒的承诺都感到质疑,因为他的寿与天齐让他们变成了虚假的爱情谎言。历经几世几劫的纠葛,悟空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情爱困境:那是由肉体的无限性与精神(灵与爱)的有限性构成的肉身有限性与精神无限性的一般哲学对偶性反题。
通过仔细阅读这段文本,我们可以稍微感知到这个与三界“学习暖男运动”格格不入的冷男所承受的巨大难以抑制的困惑、惊悸与恐惧。我们可以窥探到他时常像走投无路的阮籍一样,在花果山的深谷中狂躁与迷乱,悲喜无常地放逐与放空,发出“是人是鬼还是妖”的自我诘问。他期望有人或神能有效回应他关于身份与情感的终极关切,聆听到他关于铁棒和变化的抱怨。
这种自我厌弃式的宣泄是情欲与理智斗争的外在彰显,也是悟空的精神自觉趋于深刻的标志。他开始尝试斩断情丝的理性主义,吹响了除却六根的号角,但这样的救赎行动却遭到自身情欲的顽强抵抗。经常在倏然间,他会从一个安静的美猴王转而双目圆睁、眼角开裂、咬碎钢牙,变身超级赛亚人的小悟空毫无征兆地陷入福柯式的精神癫狂,挥舞手中铁棒以千钧之势横扫一切、砸烂旧世界。霎时间天地翻覆,六道逆转,三界迷乱,混沌不辩须弥。这是一场在疯癫之中感性、妖性和魔性对理性、人性和神性的报复。
戴荃的歌曲《悟空》是一首富含哲理思辨意义的好歌。在这首歌曲中,戴荃通过悟空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于生命与情欲的晦暗困境的理解和领悟。从“要这铁棒有何用,要这变化又如何?”的叩问到“要这铁棒醉舞魔,要这变化乱迷浊”的开释,从现实性到性实现,力比多获得了有效突破,天地开辟以来关于他伦理身世与情欲苦海的纠葛至此得到了暂时性解决。终于,我们看到了一个跋涉在西天路上的释门子弟孙行者,一个极力要踏碎凌霄、澄清玉宇,断却红尘之念,时刻要给予鬼魅妖魔当头一棒的直男癌患者形象,他的除妖狂热就来自其本身由情感冲动转化而来的生命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