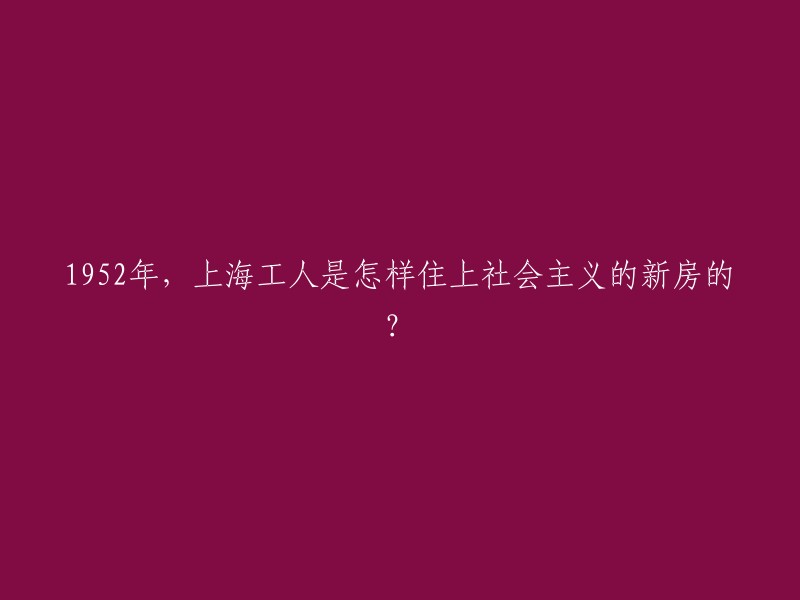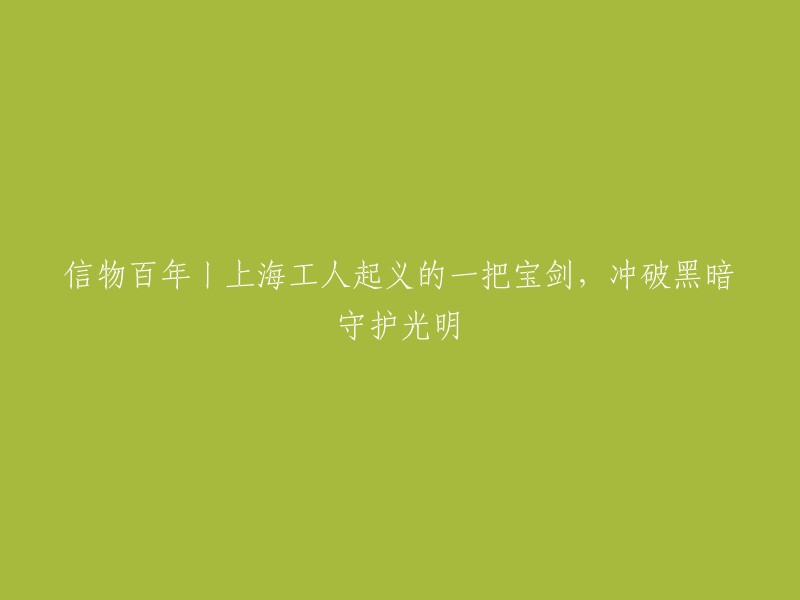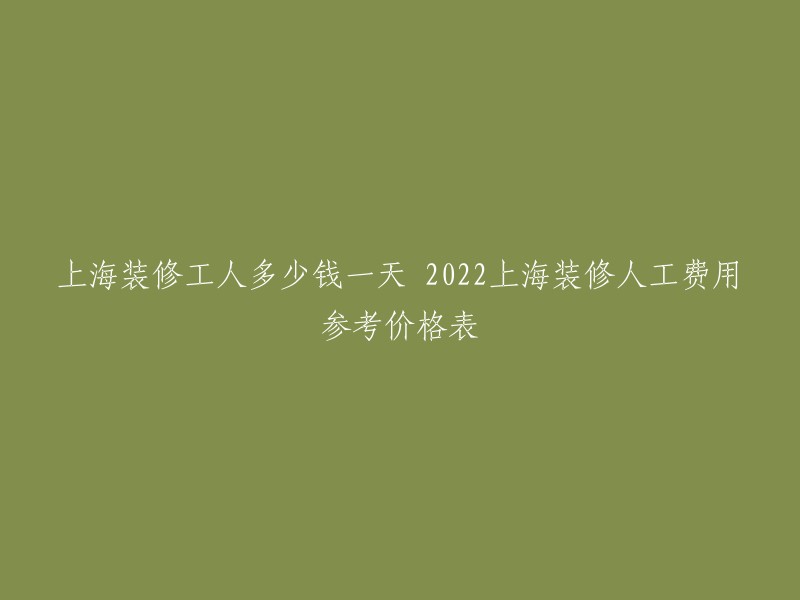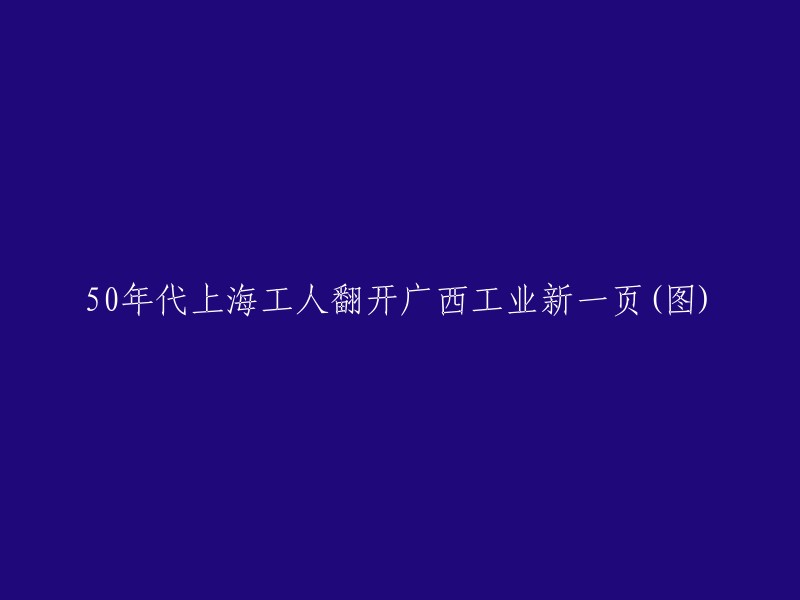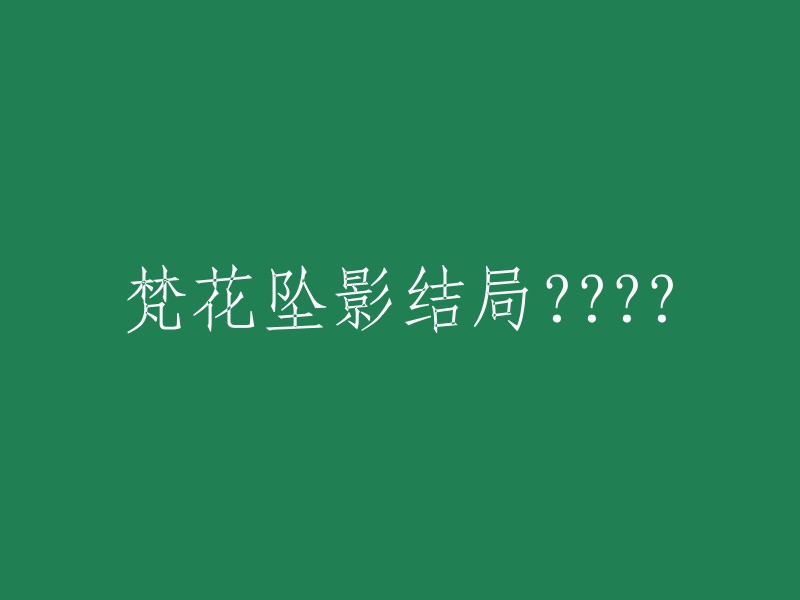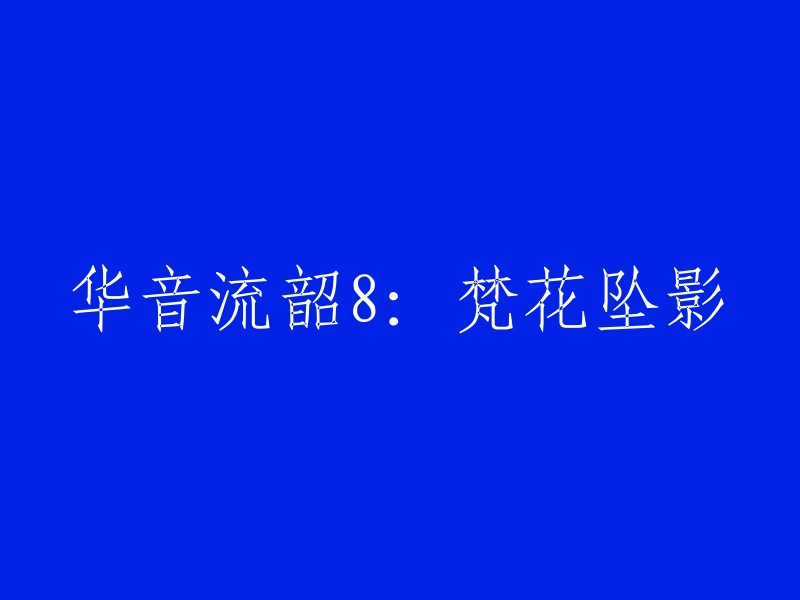您好,曹杨新村是上海工人新村的一个代表,它集中体现了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空间策略——“先生产后生活”、“社区管理的行政化”和“集体生活的培育”。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在联排的房子中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这种组织形式,既抵抗工业对人的异化,同时也试图探索一种健康的人类生活方式。
曹杨新村曾是上海的光辉象征,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它成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物质体现,并吸引了众多外宾。虽然后来被批评为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但它作为一种细胞形式的社区服务和治理,与中国设立的街道委员会和下属的居民委员会直接契合。参考了邻里单位设计的曹杨一村成为了上海的例外,因为之后的其他住房采用了苏式混凝土外墙公寓楼。
“第一批搬到曹阳新村的劳模和进步生产者被分配了住房单元,这样来自同一工厂的工人就可以住在同一栋楼。上海首个24小时公共汽车服务,在曹阳新村和工厂之间,运送上白班和夜班的工人。”根据这些回顾式的叙述,作者认为曹杨新村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共享物质和生活经验塑造了集体意识。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曹杨新村从48栋两层楼发展到718栋两到六层楼,社区从1952年的929户(4,247名居民)扩大到1958年的8,584户(47,563名居民),拥挤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58年上海市委的一份报告指出,该社区设计时的低密度原则现在已不复存在。虽然公共空间和设施很丰富,但在住房单元内,工人生活越来越拥挤。经常出现两个家庭共用一个房间的情况,拥挤导致了居民之间不可避免的争吵和纠纷。底层的共用厨房由五户人家使用,厕所由楼里的十户人家共用。1954年后,上海其他工人新村的建设采用了更好的建筑标准。但是,工人和家庭的住房等待名单长达八到十年。在市场改革产生新的私人或商品房存量之前,上海的住房仍将长期匮乏。但工人新村项目从未被设想为要解决上海的住房短缺问题。作者认为工人新村的力量是在象征性的领域,而不是实用性的领域。
2005年,上海市政府将曹杨新村定为优秀历史建筑,从而在法律上保护它不被拆除。如今,这些曾经被誉为解放空间的住宅,按照上海的标准,被认为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唯一能利用其位置和低租金的居民是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而他们的房东则是剩下的原始居民,即过去的劳模。21世纪上海的无产阶级住在曾经把工人奉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房子里。
改革开放后,“商品房”概念出现,新村中有经济能力的工人纷纷购置私密性更高的新型商品房,从而迁出了原先的住房。同时,由于外来务工人员财力有限,无法购置或租赁商品房,便住入了较为老旧的工人新村。于是,在工人新村中,主要居住人群为老年人、下岗工人和外来务工人员。
在90年代,由于工人新村内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许多人通过一种低成本的商业模式来增加收入。他们将原本用于居住功能的一层住房的外墙打通,面向街道经营起小生意,如开设小餐馆、理发店、水果店等。虽然这种将居住房屋改成非居住使用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但相关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行为,希望下岗工人们以这种方式自发创业以解决就业问题。因此,“破墙开店”现象在工人新村中大量出现,使下岗工人和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在城市中心区域就近生活。
然而,从2015年开始,政府基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打击“居改非”违法经营的双重考量,开始集中整治“破墙开店”现象。例如,徐汇区开始修缮花园洋房、还原小马路的风貌、乃至开放名人故居给游客。计划的第一步是处理违法用地,这份报告总结为“五违整治”。政府先是集中整治衡山路-复兴路的沿街店铺,随后范围扩展到全市。许多小店的店主实际是拥有营业执照的,但城管部门要求小店的原房东也要有营业执照。且大量街道由于“政府从未批准过居改非”,沿街店铺均被拆除。大多数店主无法继续营业,离开了这一片区,新店往往生意大不如前,还需要负担高额租金。(引自《“破墙开店”的前世今生》一文)
工人新村被列为优秀历史建筑后,不被允许进行大规模的改造。然而,工人新村本身存在厨卫共用、空间狭小、居住条件差等问题,被列为优秀历史建筑后对原本就已经陷于困难的本地居民而言是雪上加霜的。大部分普通居住者日常生活的经验被排挤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旅游性的视觉景观。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被转化成为商品之后,作为纯粹的审美消费物提供给游客一种怀旧的想象空间,它提供的是一个可供消费的建筑外轮廓,而不是一个活着的居民社区。更不用提无法被纳入怀旧城市文化模型的外来务工人员了,但恰恰是他们更有希望能够写出有活力的、庶民的上海城市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