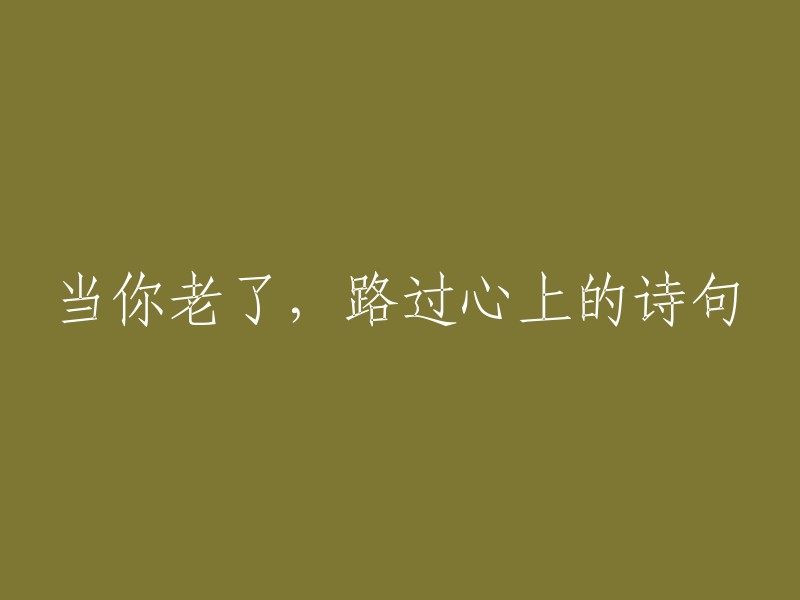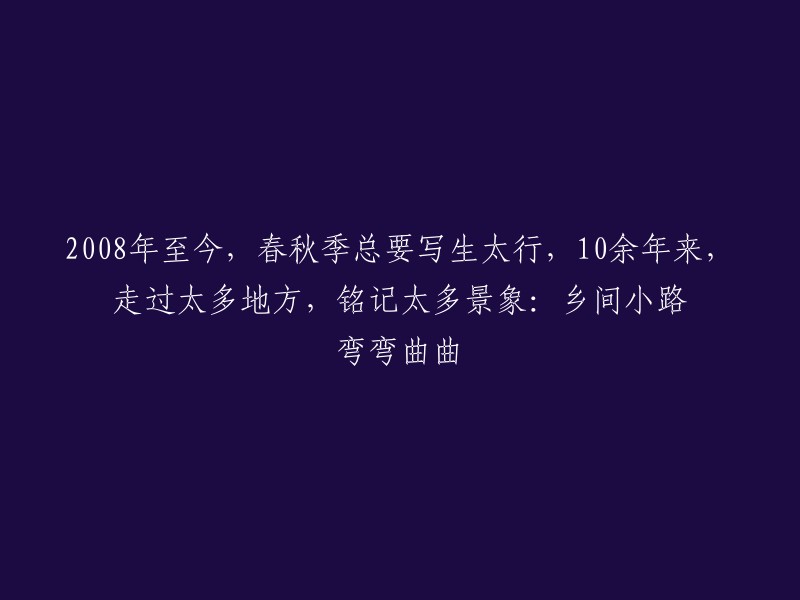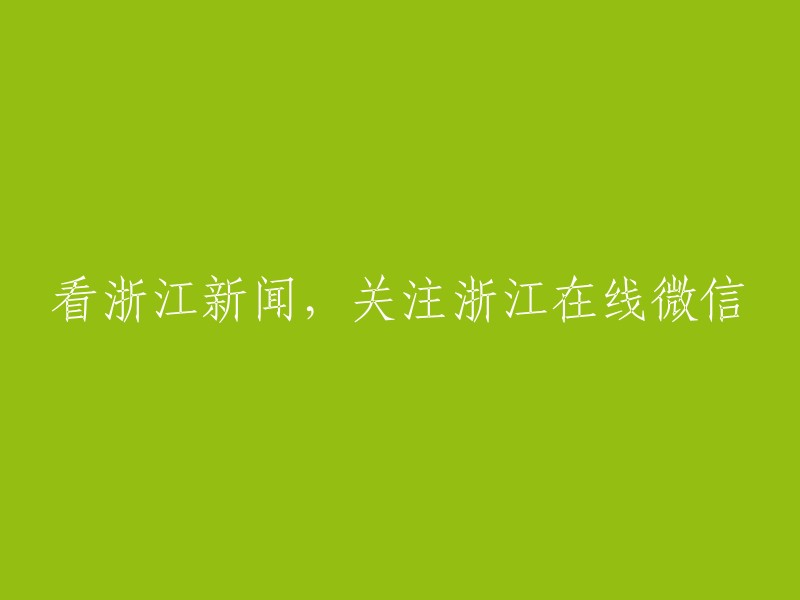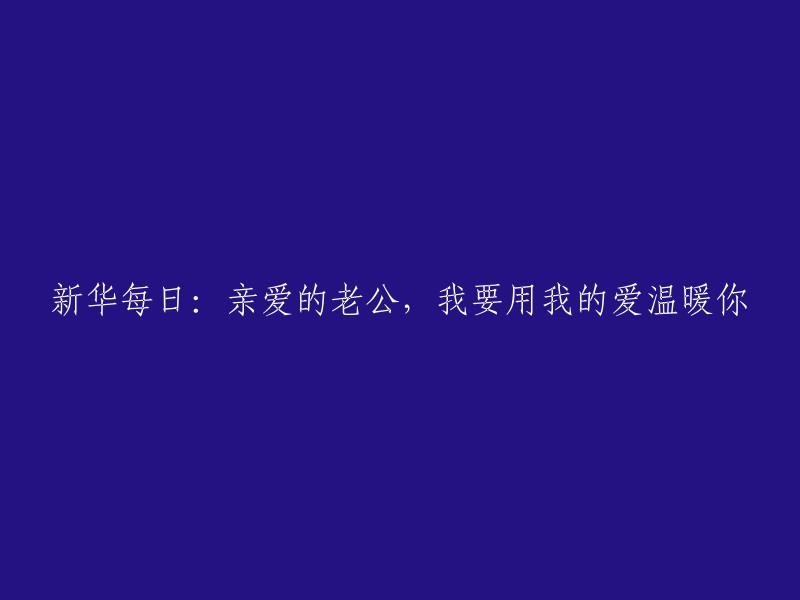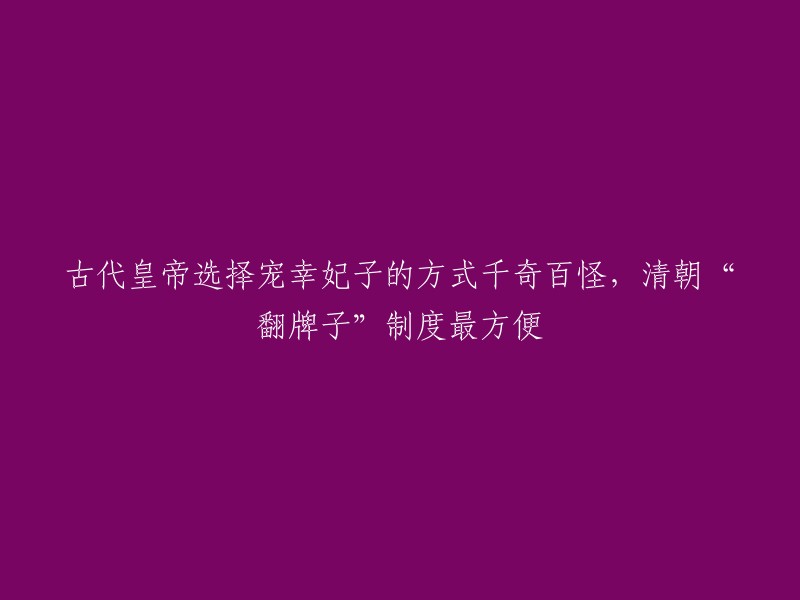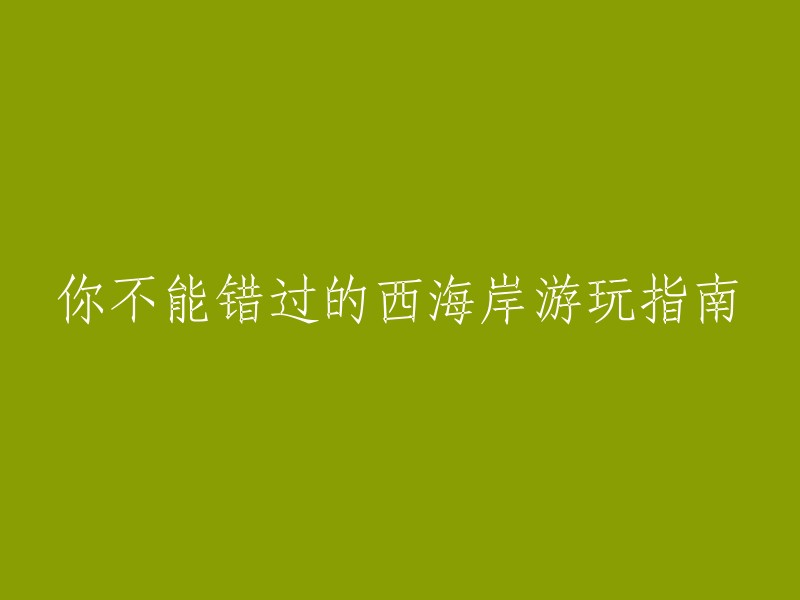你好,我找到了一些关于你提到的诗歌的信息。《夏夜登如方山》是苏野的作品,而《记忆·落日之歌》是黄金明的作品 。这两首诗都是现代新诗,其中《夏夜登如方山》表达了对自然、时间和人生的独特感悟,而《记忆·落日之歌》则通过对老之将至的人的赞美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 。
田野带着镣铐仍在工作,牲畜在吃草而没有不满。在这里,没有谁鞭鞑菊花。春天和秋天,田野像一块地毯被两度撕裂。这是多么神气的锋刃!它使经过的事物获得了两种对立的完整。到处有辉煌的落日,但无人可以阻止它的下沉。在它的瞳孔里有一个人在熄灯。到处有幽深的甜井,但无人懂得打开喉咙的阀门和身体的门闩。井水在变暗,它像一块眼镜片落在童年的课本中。多少年了,你们依然年轻,在落日拥抱,像清晨的露珠一样天真。
旅途
余西
我将驶向我所不在的城市。那里有我的书籍和床铺,有不是我的高架桥和人群。风景在蒙着水汽的玻璃上流逝:绿的杉树,白的河流,如同过往,在雨水中沉浸。在体内,幽暗的血脉里,有一种哀婉在静静流淌,但我请求,不要为我难过。透过蓝色椅背的间隙,沉睡中的女人,便足够给我安慰,她的双重下巴,她的尖嘴红唇。无人相识,却可以与自己交谈,没有人知道我的喋喋不休,只有震颤、轰鸣,在坐无虚席的车厢。我仍然没有准备好,和华丽的城市或者温柔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因为我贫穷、怯懦,我的生活没有意义。
网友荐诗
花瓶,月亮
欧阳江河
花瓶从手上拿掉时,并没有妨碍夏日。它以为能从我的缺少进入更多的身体,但是除了月亮,哪儿我也没去过。在月光下相爱就是不幸。我们曾有过如此相爱的昨天吗?月亮是对亡灵的优雅重获。它闪耀时,好像有许多花儿踮起了足尖。我看见了这些花朵,这些近乎亡灵的束腰者,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花瓶表达了对上帝的直觉,它让错视中的月亮开在水底。那儿,花朵像一场大火横扫过来。体内的花瓶倾倒,白骨化的音乐。一曲未终,黑夜已经来临。这只是许多个盈缺之夜的一夜,灵魂的不安在肩头飘动。当我老了,沉溺于对伤心咖啡馆的怀想,泪水和有玻璃的风景混在一起,在听不见的声音里碎了又碎。我们曾经居住的月亮无一幸存。我们双手触摸的花瓶全都掉落。告诉我,还有什么是完好如初的?
雨后
席慕蓉
生命其实也可以是一首诗如果你能让我慢慢前行静静盼望搜寻怀带着逐渐加深的暮色经过不可知的泥淖在暗黑的云层里终于流下了泪为所有错过或者并没有错过的相遇生命其实到最后总能成诗在滂沱的雨后我的心灵将更为洁净如果你肯等待所有飘浮不定的云彩到了最后终于都会汇成河流。
深山听夜
余光中
山深夜永万籁都浑然一梦有什么比澈底的静更加耐听呢?
再长,再忙的历史,也总有那么一刻是无须争辩的吧?可是那风呢?你说风吗?那是时间的过境引起的一点点,偶尔一点点回音。
这句话——叶志祥的《风和帆》,纠纠缠缠地描述了风与帆之间的关系,大约正是为了印证这句话在撕裂心肝。云和月遮遮掩掩,也许正为悄悄说过这句话而惶惶不安。浪和岩摔摔打打,是否正寻求一切机缘用这句话盟誓苍天。叶和花依依恋恋,这句话总被秋风吹散,各自寻梦相期来年。而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多么想把这句话重复倾吐一千遍,可是我一次也不敢,因为净土天堂路遥遥,天堂地狱一瞬间。我们去寻找一盏灯,这是顾城的诗句。
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在窗帘后面,被纯白的墙壁围绕。从黄昏迁来的野花将变成另一种颜色。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在一个小站上注视着周围的荒草,让列车静静驰过带走温和的记忆。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旁边像金桔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
在古代,翟永明的诗歌《在古代》中写道:“在古代我只能这样给你写信并不知道我们下一次会在哪里见面现在我往你的邮箱灌满了群星它们都是五笔字形它们站起来为你奔跑它们停泊在天上的某处我并不关心在古代青山严格地存在当绿水醉倒在他的脚下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彼此就知道后会有期现在你在天上飞来飞去群星满天跑碰到你就像碰到疼处它们象无数的补丁去堵截一个蓝色屏幕它们并不歇斯底里在古代人们要写多少首诗才能变成劳山道士穿过墙穿过空气再穿过一杯竹叶青抓住你更多的時候他们头破血流倒地不起现在你正拨一个手机号码它发送上万种味道它灌入了某个人的体香当某个部位颤抖全世界都颤抖在古代我们并不这样我们只是并肩策马走过十里地当耳环叮当作响你微微一笑低头间我们又走了几十里地。”
幸福一日,海子的诗《致秋天的花楸树》中写道:“我无限的热爱着新的一日今天的太阳今天的马今天的花楸树使我健康富足拥有一生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过去的诗幸福找到我幸福说瞧这个诗人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在劈开了我的秋天劈开了我的骨头的秋天我爱你花楸树岳阳楼方竟成七八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一层又一层风云登上此楼沉默的和不沉默的认输的和不认输的作为的和不作为的高调的和不高调的一步步踏上。
仿佛易碎的台阶,我登高而且望远。光线渐渐暗下去,洞庭却奔喊着,心无旁骛,浩浩荡荡。从此楼看到最多,也是最少——天地人生,洞庭沧桑。为官处事,岳阳岳州,范仲淹已不再是那个宋人名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读者来稿,告别警营(外一首)。俞弼文写道:“真不愿让熟悉的警营溶入记忆,也不愿脱去这身橄榄绿,让西装茄克衫的潇洒装扮人生。”不能忘记那一千多个用血、用火、用汗水串起的日日夜夜,回望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青春无悔。
不想告别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时间的手一挥,注定要面对酒店舞厅卡拉OK,挥洒人生。让我再一次再一次站一回岗,握一回水枪,走向沉默的战车,靠近长眠的英魂,庄严敬礼。什么都不想啊,却又在想,想来生唯一的愿望再干消防。
我喜欢为你写诗,我喜欢在夜里写一首长诗,然后在清凉的早晨逐行逐段地检视,慢慢删去每一个与你有着关联的字。我的梦被你和煦的微风染上了一缕金色的晚霞,明知道过程不一定就是结果。我想我还会以最初的心情等待你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