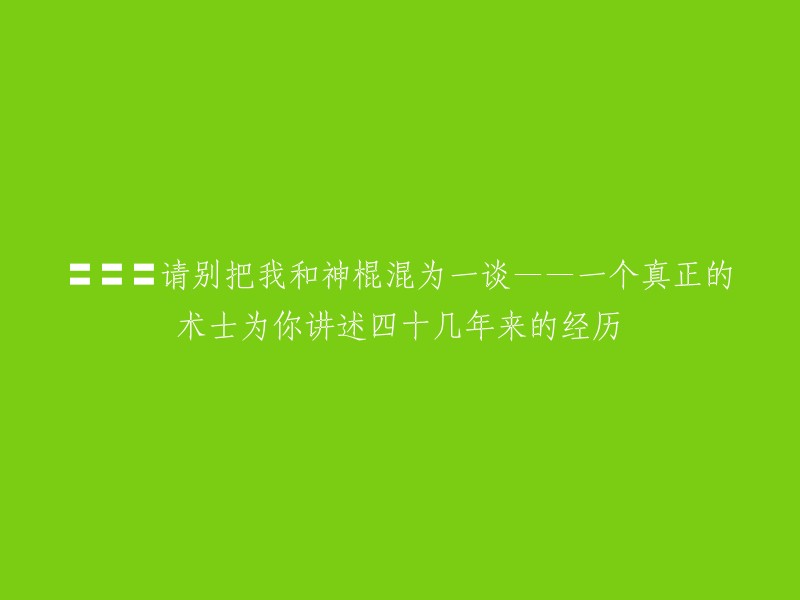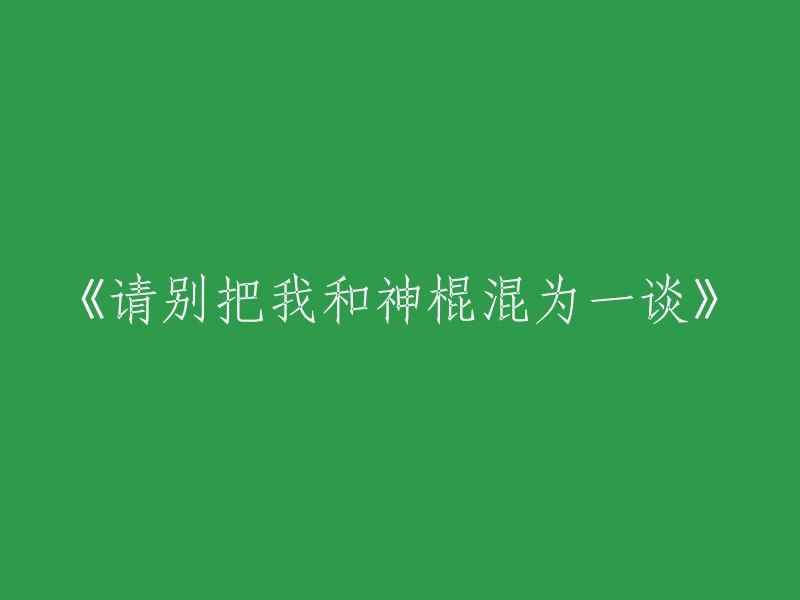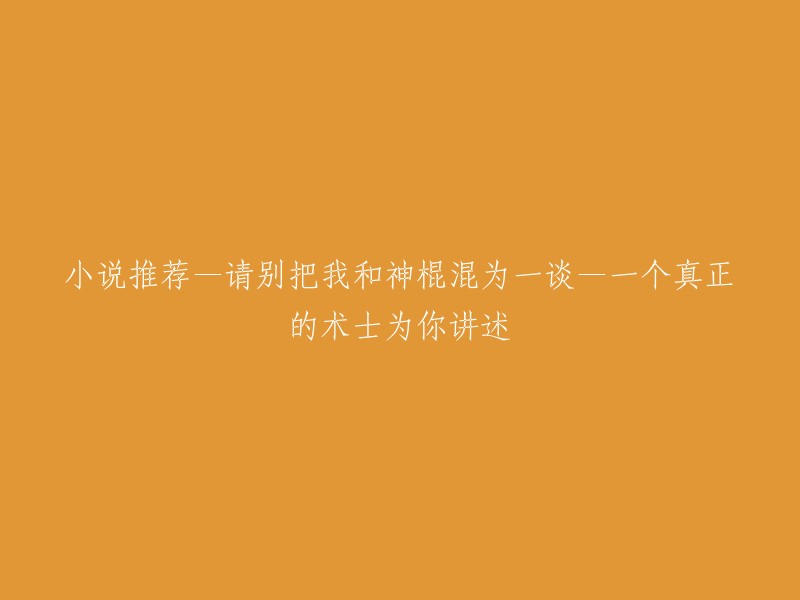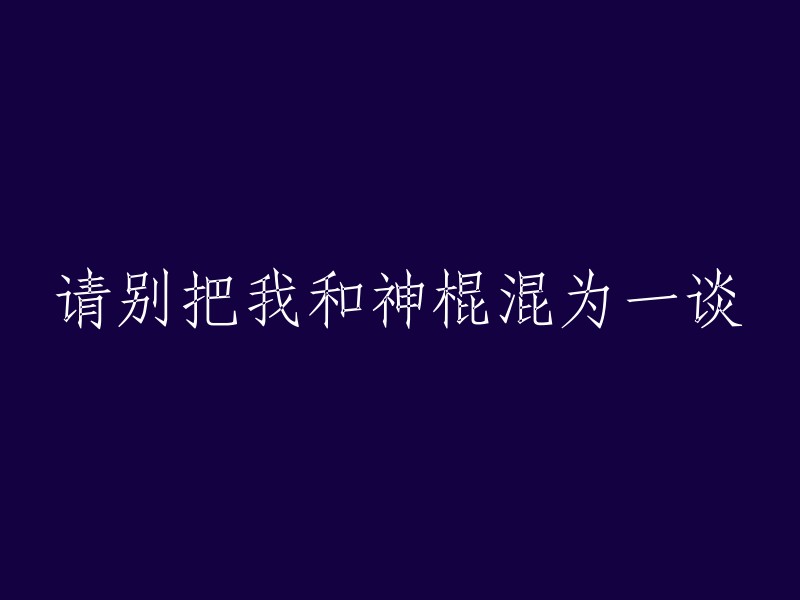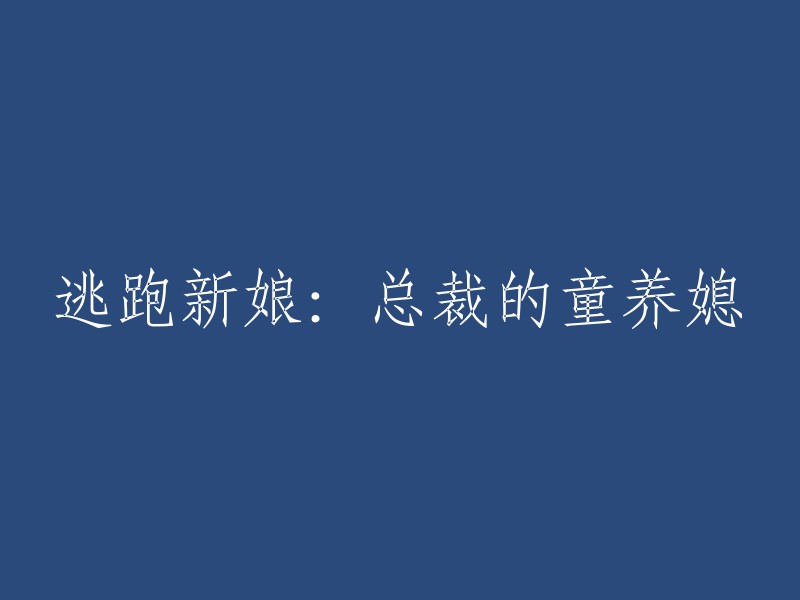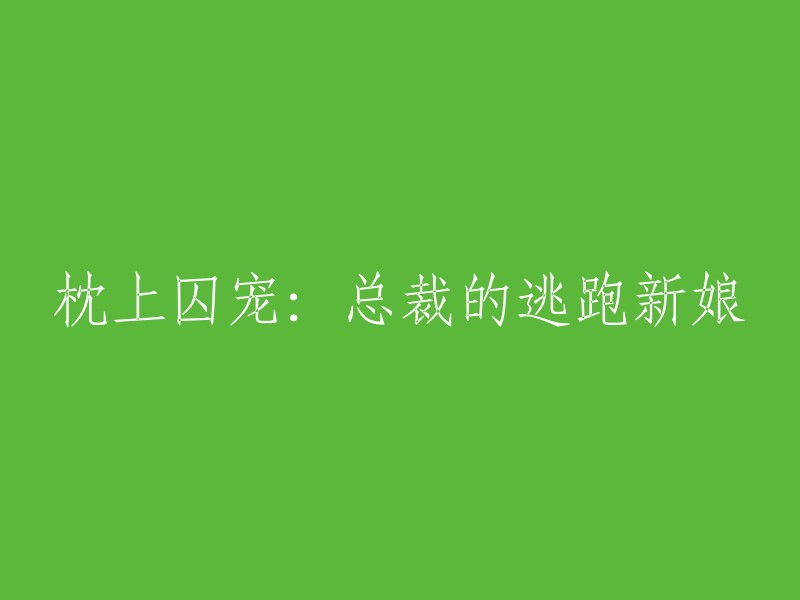汴京,大乾神都。然而近日,这座神都并非太平无波,内部鬼怪异事频发,外部藩王躁动不安。正月廿三,丑时,龙桥外,顾温正在清溪水房履行职责。他坐在马车内,小厮一丝不苟地轻拍马屁股,发出规律的啪啪声,马车行驶稳定,轻微的摇晃让人昏昏欲睡。
外面马路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灾民,他们蜷缩在道路两侧颤抖不已。尽管三月的汴京已经不再寒冷,但夜晚依然难以忍受。顾温问道:“最近灾民很多啊,我还记得前些日子还说丰收来着。”
“爷,丰收顶个屁用,就算地里长出金子来,也不够交税。”
“也是,前征十年逋税,后征十年田税,这钱都收到十年后了,也没见地里长出十年的粮食。”
大乾原本还算太平,皇帝继位名正言顺,而且连年丰收。然而,天下百姓却被苛捐杂税逼得活不下去,两道国策改稻为桑和马政直接导致两郡之地民乱四起,匪患无穷。顾温本想再说些什么,但突如其来的咳嗽让他无法言语。
这具身体贫弱,时常生病,若不是在王府讨得差事恐怕早已离世。但好在只是体质弱,并没有什么非常严重的疾病。他摆摆手表示没事,空气中只剩下饥民们在寒风中的颤抖,以及远方隐约传来的欢愉。
从朱雀门出发,直至龙桥,百余人步入夜市。人群熙攘,商贩众多,两侧玉楼林立,每逢日落灯火通明。水夫们推着独轮水车穿梭于坊巷之中,将一桶桶水运到酒楼、茶馆、勾栏瓦肆、达官显贵府邸、长乐坊青楼等地。
酒楼贩卖海参、鱼翅、熊掌、干贝、鱼肚、鹿尾、鹿舌、燕窝等珍馐美味;而青楼勾栏卷帘之下则是扬州瘦马、教坊女、角妓等美女。长乐坊纸醉金迷的赌桌上,骰子、斗鸡、斗鹌鹑、摊钱等各种赌博盛行。
尽管已经过了子时,大部分人已经入眠,但对于汴京的食利阶级而言,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既不因劳作而早起,也不因明日的劳作而休息,生下来就是为了享乐。家中的粮山肉林会将“饔飧”二餐化作三餐、四餐乃至十二餐。有的是金银珠宝豢养美婢男妾仆奴,行有轿、食有婢、居有妾,纵然是掏粪的都有专门人员。
有的是烛光油火将夜色割裂,有的是垂帘细纱隔断朝阳。最近的汴京虽不太平,但与他们这些达官显贵无关。繁华从来不是特指某个地方,而是你走的是什么道。闹市纵马,一路上不知惊扰了多少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世家子弟.....有醉汉闪避不及,在前方开路的护卫抬手便是一鞭子,嗷嚎声引得更多人瞩目。
两边花楼玉庭不断有人投来目光,窥见坐在马车内平平无奇的脸庞,初入龙桥者无不询问是哪家的公子如此大排场。而在龙桥中混迹过一段时间的只敢在马车渐行渐远后回答: “九皇子府的温侯,龙桥的千岁。”顾温面无表情,车窗外昏黄的灯光照在他脸上,面容平平无奇,不显山不露水,落入人群之中估计很难引起他人注意。他理所当然享受着权势带来的种种,早已习惯踩在他人头上,厌倦他人的敬畏,也变成了一头吃人的怪物。前世的道德、文明、观念只会害人害己。
封建礼教从来不只是一个观念这么简单,它是一尊不可忤逆的神明。只有当它死亡时才能被骂。顾温不过是这尊大神座下的奴仆,半个能站在这里的水房经营者。他不是达官显贵、皇亲国戚或实权大京官。他是一家水房的经营者和一位皇子的家臣。
卞京内外城人口三百余万,六成倚靠流经汴京的涛江支流过活,剩余则依靠打井。而偌大的汴京仅有两千口井,其中苦水井一千六百之多多为寻常百姓用度。清水井占三百余,乃官吏之家、小康之家所用每月需交水钱。甜水井不过百余,皆为“水金矿”。城中私人凿井水甜者多经营卖水营生,掌柜置木独轮水车上方木桶伙计灌满后推抵买者家倒入水缸取钱走人所以顾温以此为生占据龙桥附近最大的水房半个龙桥商铺都需要仰仗的水房每月经过手上的钱财没有黄金万两也有个八千两人送外号“温侯”。
-----------------
九皇子府
“温侯王府到了”顾温走下马车抬头望去高门大户石狮耸立崇垣围绕并覆绿色琉璃瓦屋脊上安置吻兽赫然是亲王居所没有让家丁奴仆引路快步走进府内路上十步一哨守卫对他视而不见无人阻拦顾温已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却是第一次深夜召见他进府邸让他感到十分惊讶到底需要什么才会深夜来王府急于揭穿谜底的心情催促下加快了步伐王府内还沉浸在漫漫长夜到处静得落针可闻让顾温的步伐越发清晰明显以至于还没来到书房坐在其中的贵人就已经察觉华光异彩的珠帘被太监拨起顾温走进书房淡淡的熏香从兽炉中弥漫贵人正俯身在案台上书写字画明黄色便袍在烛火中微微反光五官英俊而贵不可言九皇子赵丰也是大乾储君有力竞争者十年前太子落水身亡当今圣上并未新立太子至今皇帝年迈朝中风云涌动
顾温走上前,单膝跪下。在大乾帝国,除了极其正式的场合,朝中大臣见皇帝都不需要跪下。而需要跪拜的只有一种人——家奴。任何地方都有三六九等,有人的地方就有高低贵贱之分。家臣分为两种,一种是带资进组的世家子弟,另一种是像顾温这种毫无依仗却有能力的普通人。前者才是臣,需要主家以礼相待,后者则是奴,任杀任剐。
然而,聪明的主家会默许家奴下跪的规矩,同时又表现出亲和不拘小节的态度。这便是作为家臣的另一个好处,可以轻松地取得主人的信任,并成为心腹。顾温便是九皇子的心腹之一,凡是关于经商方面的事情都会找他商谈。但这是第一次大半夜找他,今日九皇子的态度也有些奇怪,比以往更加亲近,甚至是多了一丝丝“尊重”。
对于权贵而言,商只是一个体面的吃法,而对于自己这个一介布衣,能力多是在商业上的人而言,这是一种难得的信任。赵丰以讨论家常的口吻问道:“爱卿拜入本王府中应该有五年了吧?”
顾温有些恍惚,五年前的记忆涌上心头。原来他已经穿越到了大乾汴京,成为一个乞丐已经有五年了。身上带着一个祖传的石头玉佩,据说内有仙缘。还没等顾温研究明白九皇子的太监就找上门来,要他手中的玉佩。那人带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军士,又表明了身份,顾温自知留不住宝贝于是提了个条件,他想要荣华富贵。穿越成乞丐煎熬了大半年,留不住宝贝至少趁机脱贫。对方答应了,然后将他带入九皇子府,一直到今天。
起初顾温听闻“九子有太祖遗风”时,第一反应就是跑路。九皇子挂着这个名头以后必然会被卷入皇位斗争中。但当他看到封建社会的种种,他发现其实皇位的权力斗争并不可怕,当一个普通老百姓才可怕。你就算有千万身家,下一秒也不过官吏屠刀下的肥猪,他们有的是办法吃掉你。
所以顾温留在了九皇子府,利用现代的一些公司管理经验,成为了对方的左膀右臂,负责九皇子府最大的现金流水房的“温侯”。顾温回答道:“若不是殿下,属下可能已经饿死路边,殿下恩情属下铭记五内。”
“卿可听闻最近城中奇闻异事?”赵丰接着问道。
“自然,龙桥下有人看到龙影游过,城南朱雀路一夜之间长出了一颗高十丈的树,白云寺大佛冒金光,汴京有人夜遇白鹿。此乃祥瑞,大家都说大乾可有万年国祚。”古代鬼神之说本就多,最近一段时间尤其多,且说得有鼻子有眼。
顾温让人去打听过,朱雀路确实突然长了一颗树,而且官府叫了百来名民夫都拔不掉、推不倒,最终无奈放任不管。如今朱雀路就因为这棵树,整日被堵得水泄不通。
“卿应该知道,这些都是真的。”赵丰取下腰上的石头玉佩,放在桌上顾温能看得见的地方,对顾温的称呼也忽变,道:“这是当年你的传家宝。”
“如今已是殿下的。”
“本王若想把东西还给你呢?”赵丰身躯微微向前倾倒,语气平静轻巧,好似真的要还给顾温一样,却不知暗处已经泛起了多少锋芒。
顾温不带迟疑地回答道:“那属下便需要归还殿下恩情,仅仅是上一年属下便已经花销三千两银子,五年恐怕有万两,属下掏心掏肺也还不上。”
“殿下难道要让我吃白食?”面对反问赵丰愣了一下,随后轻笑几声,笑声瞬间让杀机淡去许多,收起玉佩笑骂道:“爱卿倒是潇洒,一年能花三千两银子,在这汴京买个府邸也才千两不到。而本王若不算宗人府拨银,一年的花销恐怕还没爱卿一半。”
“殿下圣德。”顾温顺势恭维了一句,他知道今天又躲过一劫。伴君如伴虎,赵丰虽只是皇子,但现官不如现管,对于顾温以及九皇子府内所有人他比皇帝更有权威。
见赵丰颇为受用的点头,顾温更是心底发笑。此举无外乎一个恩威并施,时时刻刻敲打着下面的人,同时也在享受权力倾轧他人之快。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手段,他站在这个位置,所以能够压倒自己。所谓天家并不圣神,也不高贵。所谓帝王心性,不过是想着法子如何把人变成鬼。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或许真对赵丰感激涕零,可顾温心里有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灵魂,他脑海中充斥着不属于封建礼教的认知,并且他绝不会放弃这些认知。
但人嘛总要吃饭的,不隐忍还能翻天不成?说了这么多‘掏心掏肺’的话,赵丰也不再磨叽,言归正传道:“这些异象都是真的,天底下也确实有修仙长生,爱卿近日所见所闻可能是某位大神。”
顾温呼吸一窒,心跳都慢了半拍。因为传家宝的缘故,他时常怀疑这个世界有超凡力量存在。但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求证,拿到自己传家宝的赵丰也不见得飞天遁地。但如今却说,天下有修仙者存在,且近日一直出现在自己身边。
顾温问道:“为何以前小的从未听闻?”
“因为没有到时候,这天下就像一个果园,只有果子成熟的时候才会有人来采摘。”赵丰神情变得严肃,话到一半又没有说完,转头开始以命令的口吻说道:“那些方外之人并非我大乾所能抗衡,但大乾可从中获利。”
“本王与一位仙人取得了联系,仙家原本想见你。”
顾温消化完庞大的信息量后,疑惑地问道:“属下一介凡人,何德何能?”
“顾家中祖上应是有仙缘之人,而那位仙人本应该是找你的,如今你已经把信物卖于我。”赵丰言出如刀割,让人听得异常扎耳,随后又适当的表示亲近:“且这府上几百人,也就卿与大伴得以让本王放心。”顾温瞥见主家平静的脸色,其中带着毋容置疑的意味,他低头答道:“是。”
身为家臣,身不由己。
“去吧,库房领一千两银子。”
赵丰轻巧的丢出足够外边数万灾民吃喝半年的钱财,而对于这位皇子而言只是随手的赏赐。
顾温揣着一大堆宝钞离开王府,坐上马车又回到了水房所在的龙桥夜市外。清晨的寒风依旧冷冽,灾民聚集在官府设立的粥铺前,捧着一碗碗泛白的水。看那颜色不知道还以为是粥。
顾温走下马车望了一眼,随后心底暗嘲一声:“这家奴,天底下不知多少人求着当。”若是五年前,他会救济灾民,因为他来自一个文明的时代。他或许只是一个普通人,但在大乾他的道德水平、同理心、同情心要高于这个社会。
他穿越到这个类古代封建王朝不正是为了普度众生,传播文明之火,消灭已经与普通百姓形成‘生殖隔离’的公卿高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戏台,戏台与现实又犹如不同的隔阂,有人可能就一步之遥,有人可能是深渊。在没有把自己摔死之前,顾温花了五年从戏台爬了下去。回到救济灾民上。
他当了那个大善人,那不作为的官府就“不善”吗?那官老爷们就不善吗?那赵丰就不善吗?他一个家奴商贾的,出什么风头?我善了,天下就不善了。顾温在仆人婢女地拥护下走进那被烛火与垂帘细纱笼罩的府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