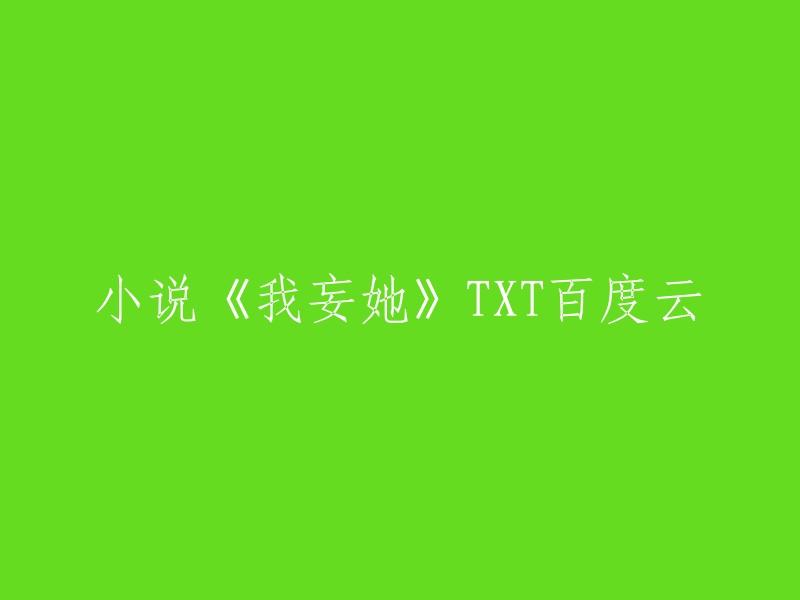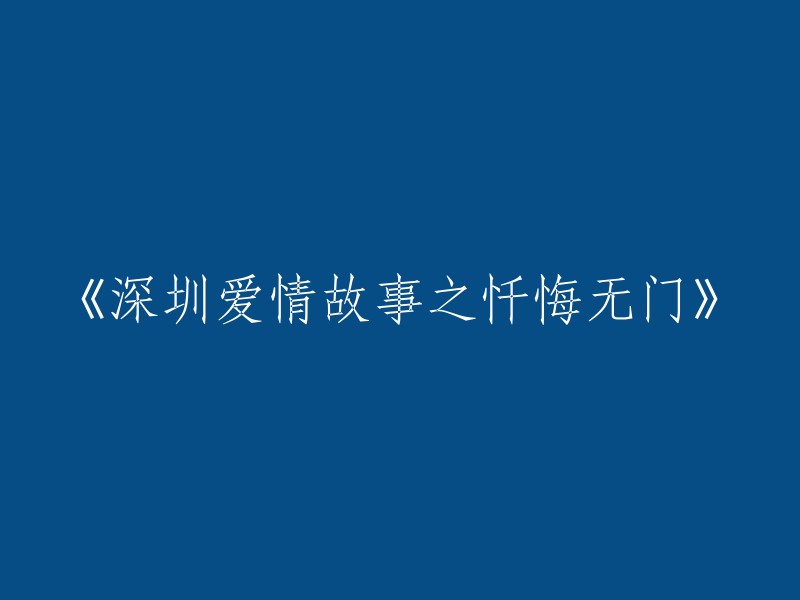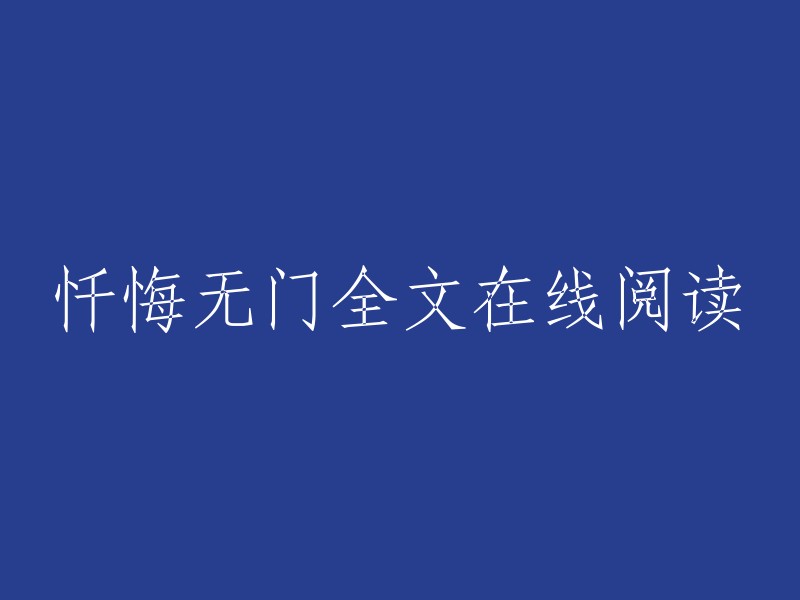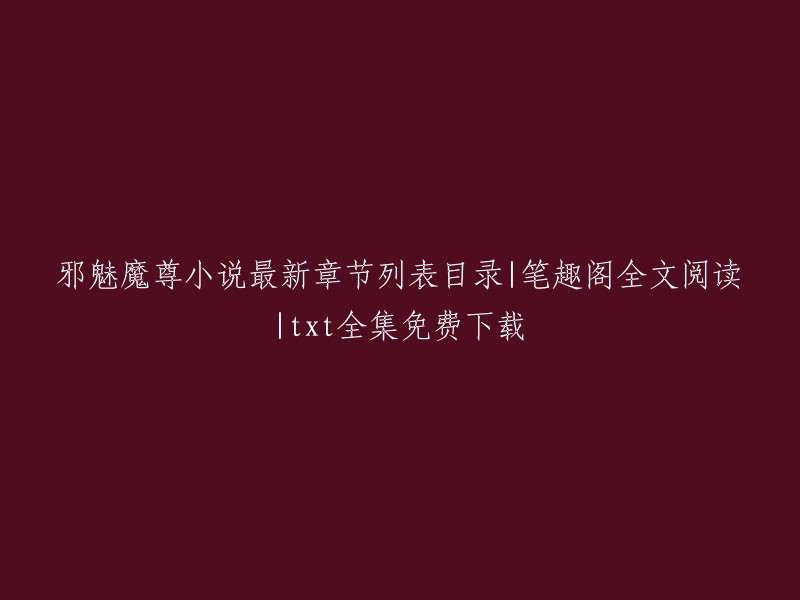。
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搭乘火车前往天津欣赏了一场《摇滚莫扎特》(法扎)。在那之前,我已经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里将这部法语音乐剧的影像看过多少遍了。当我踏上现场剧院的台阶时,内心的激动无法用言语形容。与其说这是一场演出,倒不如说这是一种满足执念的心情——毕竟这样让人喜爱的剧目,能够在剧院里亲眼目睹,实在是太美妙了。
演出结束后,外面已是一片漆黑。曾经璀璨夺目的光影,此刻被静谧的黄昏所取代。冬日的天际线呈现出灰白色的画卷。我只觉得有些头晕目眩,恍若梦醒之人。身后的大剧院和那场音乐剧,仿佛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境。
我一直深爱着那些能让人陶醉的事物,无论是诗歌、电影、展览还是戏剧。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它们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如水晶宫般的梦幻世界,值得我们用心去呵护和珍惜。而我所了解的语言,却无法完全表达我对法扎现场所带来的震撼之感。
当代生活虽然便捷无比,但同时也变得飘渺不定。一部小小的手机可以轻松存储数千张照片、数百首音乐和数十部戏剧的影像。然而,我仍然无法抗拒胶卷相机、黑胶碟片和现场演出所带来的真实感触。这些鲜活的实体让我能够面对自己短暂的生命,在其中找到一丝真实的存在。
2。
然而,我从未想过法扎会给我带来如此强烈的后遗症。
过去的一个月里,法扎中的歌曲几乎成为了我生活的背景乐。无论是早晨还是夜晚,无论是行走在路上还是坐在书桌前阅读,音乐总是在循环播放着那些浪漫激昂的旋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它的思念愈发强烈。我只能边听歌边默默嫉妒那些身处国内、可以轻易走进剧院观看法扎的人们。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戒毒后的戒断反应。
3。
为什么我会如此喜欢法扎呢?究竟是因为纯粹的审美原因,还是因为它蕴含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核?这个问题如同一把锐利的剑,直指我的内心,既带来了痛苦,又带来了难以割舍的快乐。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在与自己的对话中找到答案,但往往陷入更大的困惑。
4。
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的。那么好吧,让我们从头开始探讨吧。
首先,当然是因为没有人能抵挡住莫扎特的魅力——即使过去三百年,人们仍在聆听他的交响曲和协奏曲,仍会走进剧院观看《魔笛》和《费加罗的婚礼》。他拥有一种神一般的能力,将才华燃烧得如同熊熊烈火,短暂的人生里留下了无数美丽的乐章。他坚定而自由,无论面临多少苦难和世俗的枷锁,都没有被真正束缚住——他只为创作而来,不为宫廷、名利场,只为了让真诚的灵魂化为音符,流淌在乐谱纸上。
他就像一颗星星一样,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能一眼看到他。因此,《摇滚莫扎特》这部关于他的一生的音乐剧也同样拥有着浪漫激昂的鲜亮底色。米开朗琪罗扮演的莫扎特穿着亮闪闪的礼服,单手背后行一个夸张的鞠躬礼,犹如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少年。这让我想起了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写的那个穿着花色鲜亮、袖口宽大的袍服,雀儿似地跳来跳去的年轻骑士。
什么东西最打动我呢?是压倒一切的大决心,是为了心中一个愿景而甘愿献出的骨血和眼泪,就像车前子描述的那种“残局”似的诗,像两头尖尖的橄榄核,一点也不安稳,一点也不平衡,一字一句都生死攸关。所以我喜欢李贺这个通眉长指爪的细瘦诗人,呕心沥血一字一字地吐出句子,再将它们一点一点地连缀成篇。我也喜欢赫拉巴尔,他一生阅读、写作,最后死于从窗口探身想要触碰一只飞掠而过的白鸽子。我还喜欢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喜欢那部小说背后的影子保罗·高更——但是要画画!要画画!哪怕抛却一切,到遥远的太平洋上去。
这种近似于献祭的激情也是法扎的能量来源。在他演唱的那两首歌中——《好事之徒》(Le trublion)和《活到极限》(Vivre à en crever)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由意志、不愿意被宫廷束缚的态度。尽管莫扎特面对明枪暗箭的指责、冷落和打压,但Le trublion歌词中的狂气却尽显出来:“法官先生、检察官先生:Non, je n’ai cure de vos assises(我不在乎你们的立场)。Je suis assis sur votre Honneur(我高于你们的荣誉),et vos valeurs que je méprise(蔑视你们的价值),je suis un libre-penseur(我是自由意志者),un trublion(捣乱分子),un emmerdeur(让你们生厌的人)。”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写到,全世界的柯尼阿什焚书只是白费力气——如果书上记载得有道理的话,那么焚烧之时只会听到书在窃笑。那些嘲笑和伤害莫扎特的人又何时真正困住了这个神子呢?哪怕在人世间被折磨得一身泥血脏污,也仍会从累累伤口中迸出令人眩目的金色光芒来。
在阅读法扎的作品时,我不禁想起了塞尚曾经给左拉的信:“绝不要忘了艺术,我们因此达到星辰的高度。”这是怎样的一股力量,让人心生敬畏。而莫扎特也曾说过:“沃夫尔冈·莫扎特永不言败。”这句话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然而,法扎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关于力量、光明和浪漫的理想主义。他更深入地描绘了那些光明背后的阴影,追索之中的代价,天才的眼泪与痛苦。正如他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火,它的光把一切痛苦深埋在下面,脸上却挤出一个悲哀的微笑。”
刚读完法扎的作品,我在日记中写道:“有时候我想,法扎其实也是一个关于失去和别离的故事。莫扎特的短暂一生,经历了多少仓促的离别,多少次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挚爱的人和事离他而去,母亲、父亲、阿洛伊西娅、早夭的孩子、傲慢的巴黎人、宫廷的垂青......他三十五岁的人生,好像就是被一个接一个的离别和困苦拼凑起来的。”
小时候,我就非常喜欢《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书中讲述了一个人为了成为画家抛却一切,遁逃到太平洋的小岛上寻找灵魂的救赎和艺术的真谛。如今,我仍然很喜欢这本书,但也逐渐看到了毛姆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追求中的苦泪心酸。
《月亮与六便士》的故事蓝本是画家高更的人生经历。高更的名字在后世光辉万丈,然而他却一生困厄,为了生存辗转各地,最终在物质的贫寒和精神的折磨中故去。每次去波士顿美术馆,我都会来到《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这幅巨幅画布前静静站一会儿。画作作者高更在画这幅画时已经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物质上贫寒困厄,精神上也痛苦万分。
这是一幅毋庸置疑的杰作。然而,我每次都会想到高更在给朋友的信中那些浸满泪水的字句:“在我离开人世前,我希望能完成一幅一直在我脑海中的画作。这一个月来,我在不可思议的高烧中日夜工作......我相信这幅画比我曾经一切的作品都要更好,甚至我今后也不会有更好的作品了。在死神降临之前,我把一切的能量,那些在这可怕的境况下饱含痛苦的热情,全都倾倒进这幅作品里了。”
这样的代价是沉重的。即使找到了那件愿意不惜代价去追求的事,即使愿意放弃所有,献祭自己一切的生活、心血、甚至性命,但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世上并没有一种魔法或者炼金术,让所有的付出一定开花结果。只能忍耐,在所有的痛苦、恐惧、犹疑中忍耐,忍耐那些咬牙切齿、生不如死的时间。
对我而言,法扎最动人之处在于他对这些真实苦难与代价的描绘。这些描绘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也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求,去承受那些看似无法承受的痛苦,我们终将能够在生活的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高度。
在法扎中,莫扎特和萨列里成为了主要人物。萨列里曾是维也纳宫廷乐师长,备受尊崇,直到莫扎特的到来。尽管他懂得音乐,但面对莫扎特的天赋,他陷入了嫉妒和痛苦。
《杀人交响乐》成为法扎中最受欢迎的一首歌,它是萨列里在听过莫扎特新歌剧作品后的一段独唱。在猩红的光影中,萨列里走上舞台,手持匕首,在挣扎和痛苦中唱出:“Cette nuit昨夜,Intenable insomnie辗转无眠,La folie me guette癫狂已窥伺许久......”这首曲子动人至极,几乎是癫狂的呓语。
萨列里曾经教出了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等优秀学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莫扎特的作品一次次复排,而萨列里呕心沥血谱写出来的那些歌剧、那些曲目却慢慢湮没了。这种现象让人感到残酷,就像在博物馆看到印象派独立展览的宣传册,上面有很多现在令人眩目的名字,但却忽略了一些其他的名字,这些名字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可能陌生,艺术史研究领域也少有提及。
我们欧洲艺术史的教授在讲课时,常常会提到一个艺术家,然后对着底下茫然的目光解释说,“这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画家”,“这是一个被遗忘的人”。每到这种时刻,我都会感到由衷的难过。多残酷啊。他们也曾经,那么热爱他们为之献出一生的事业。
在法扎的末尾,有着雪白双翼的天使走到莫扎特的病榻前,在Vivre à en crever的乐声中,拥着他飞升天堂,好像上帝正召回他最疼爱的孩子。那个场景在我眼前反复地浮现,难以忘怀。我想着剧中要着重描绘的是这个所有灵魂中最真诚的一个,在一生的坚持和追索后,面对最终结局,露出的一个坦然的微笑。那自然是极动人的。不过我也在那一幕中,看到了更多的更复杂的情感。有眷恋,有遗憾,有痛苦,甚至有脆弱、不安、一点点犹疑......令人想到华托画笔下的伶人。
华托创造了那么多洛可可风格的瑰丽画作,我却私心觉得都比不上这个哑剧中戴着滑稽帽子的丑角。他局促地站在画面中央,宽大的衣服罩在他身上飘飘荡荡的,却又好像根本起不到遮蔽的作用。他仿佛整个人被剖开了挂在广场上示众。那么脆弱,那么孤立无援。最动人的是他的神情——你没办法说出那究竟是怎样一种神情。天真的伤感,压抑的不安,无辜者的苦笑,事不关己的疏离,近乎神性的悲悯......最脆弱,最敏感的艺术家。纤细敏感,哀乐过人。这的确是神赐的珍宝,然而却也同时注定了这些敏感的灵魂要承受经历的苦恼和困惑,承受更多曲解与指责,在那些“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的烈火中辗转反侧。就像法国象征主义的画家们说的,那些属于艺术家的天赋,那些对于人类感情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对于拥有它们的人而言,既是恩赐也是一种诅咒。
现在是1月27日的凌晨。二百六十三年前,也就是1756年的1月27日,沃夫尔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出生于萨尔茨堡。感谢你的音乐。以及,真希望你活得长久一点。你一定想象不到后来的三个世纪都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了一个温柔的绅士,你当时褒奖的年轻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变得比你还有名。人们谣传是萨列里毒死了你,普希金还为此写了一部剧,这个事儿算是彻底盖棺定论翻不过来了。《费加罗的婚礼》也终于恢复演出了,并且一演就是三百年,相信你知道的话一定很高兴。树长高了,萨尔茨堡和巴黎的样子都翻天覆地,如果你现在去,肯定认不出来。最重要的是,关于你的故事,和你最珍爱的音乐,仍在新的时代里生生不息。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以下是重构后的内容: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