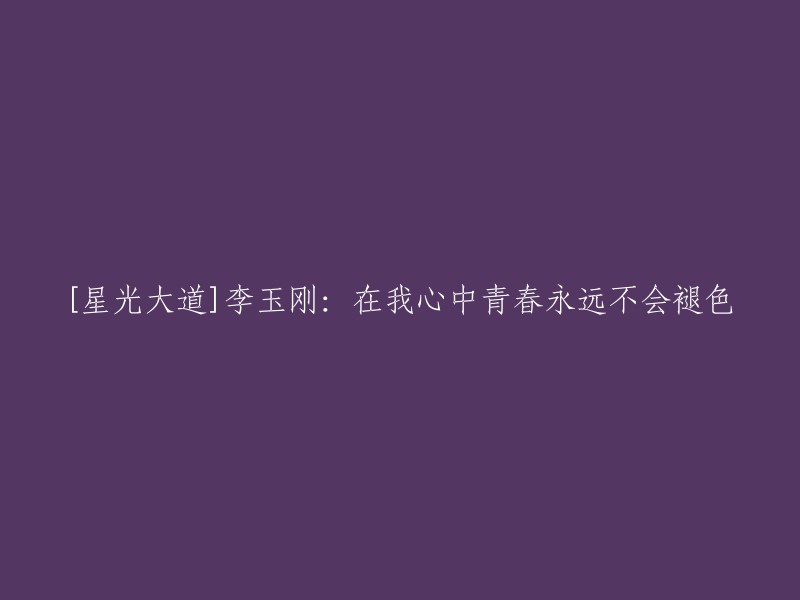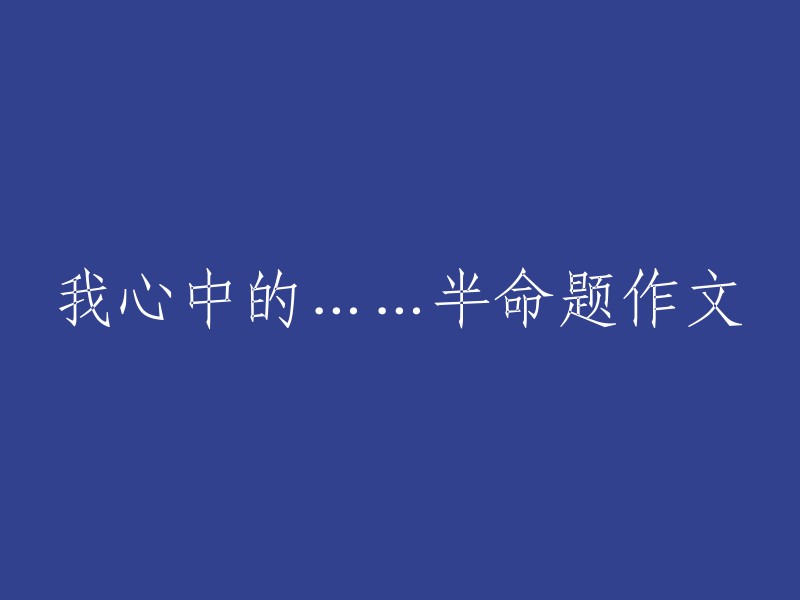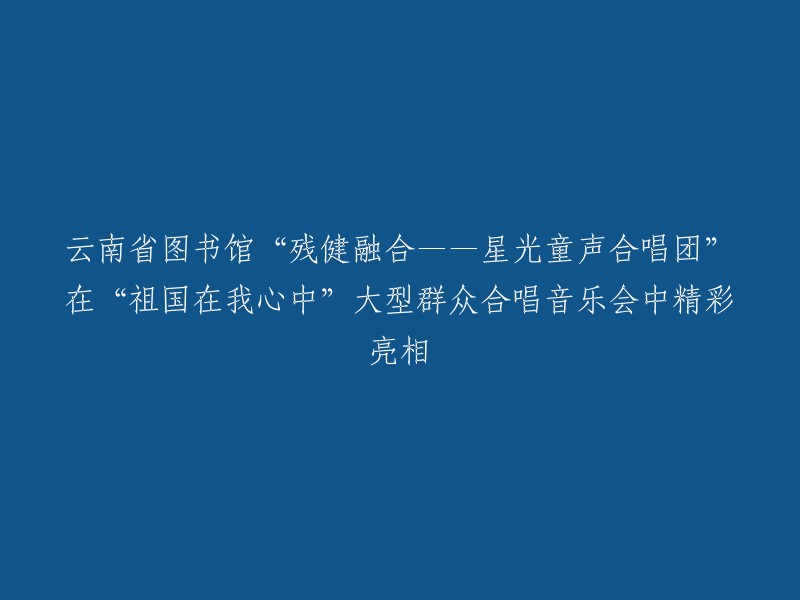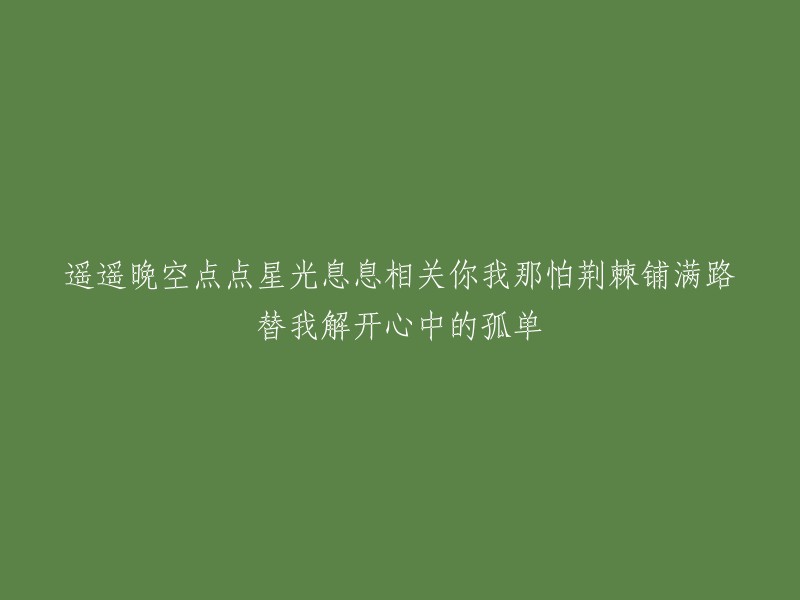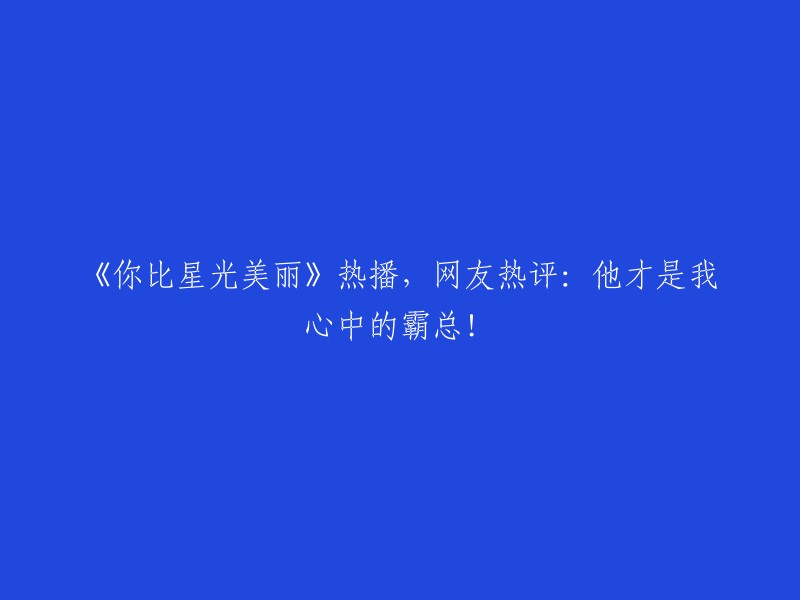在扣考山和我方19、20号界碑之间的越南境内,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捕俘战斗。这场战斗发生在1979年中越战争前夕,战前,我和我的战友们已经参加了两次捕俘行动。在这两次行动中,我们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这一次的捕俘战斗却让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979年1月18日,我突然接到去营指挥所的通知。胡绍洋副团长、刘付文营长和刘恒军连长都在。一看这阵势,我知道马上会有行动了。“我团侦察排将要在这两天出境执行捕俘任务。你们班将参加他们的行动。”“你们的任务,是在侦察兵捕俘前提早进入越南境内指定位置潜伏。侦察兵行动时,负责阻击和掩护侦察排捕俘及撤退。目标是越南扣考山和我方19、20号界碑之间的越军3师12团4营的一个哨所。根据广州军区情报部通报,越军在这个哨所驻有7个士兵,你们将在天亮前用微声冲锋枪干掉其中6个,然后抓1个舌头回来。撤回路线是20号界碑。”胡副团长和团侦察参谋详细地下达了战斗任务。
当天下午,我们到了米七前沿阵地进行现场侦察,并制定了进入越南境内的路线和后撤路线。团侦察参谋发给我一张已标好这次捕俘行动路线的军用地图。侦察排将由19号界碑前出,向左面的扣考山方向进发。我们则在20号界碑位置出境,然后向右进入指定位置。在地图上看,从出发阵地到指定潜伏位置路程并不远,但在阵地上可以看到沿线都是深山密林。我们预计需要约3个小时才能到达指定位置。回去后,我们马上开始准备,除了原先的装备外,每人特别多领了150发子弹,因为负责阻击和掩护,多带点弹药,总放心些。我多了个心眼,又领了两把开荒刀。接着营里又增派了一个重机枪班给我们。晚饭时,连长特别关照后勤给我们加菜。所谓加菜也不过是开了几个肉罐头而已。晚饭后,我们就接到连部通知,准备明天早上零时零分出发,7时零分前到达指定位置,7时30分开始行动。为了预防万一,我们把身上所有关于部队的文字资料都交了出来,让连部暂时保管。由于还没有正式向越南开战,连长特别告诉我们:“如果发生意外,上级指示大部队不能越境营救,你们必须独立作战,自己设法返回。部队会在19号和20号界碑我方一带接应,但不会有炮火支援。”从那一刻起,我们都非常紧张。虽然大家没有说出来,但看得出来,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哪能不紧张不害怕?
在深夜将近12点时,我们已经进入了出发阵地。突然,收到通知:“今晚取消行动,等待另行通知。”第二天是1月19日,米七村的老百姓都在忙着准备过年,而我们则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刻很快就要到来,我们将第一次将准星瞄准另一个生命,也可能第一次被人瞄准。
等着,等着,终于到了晚上10点钟,胡副团长来了。我们知道该出发了,没等他说话就开始拿起装备。记得那天晚上,天十分黑,既看不见月亮,也看不见星星。通过前沿阵地后,我们静悄悄地向指定位置进发。走在前面的是副班长带领的尖兵小组,我带着重机枪班和我班的轻机枪手走在尖兵小组后面,战斗小组长负责断后。沿途的土山被茂密的杂树草丛厚厚地覆盖着,藤葛盘绕,荆棘丛生。锋利带刺的茅草叶割得我们脸上和双手到处都是伤口。我们走的那段路,越南人当时还来不及埋地雷。一个月后开战时,他们在那一带埋满了各种地雷。
开战第一天,我连3排要在那里出发。广东籍的7班长叶添顺跑来问我:“那条捕俘时走过的路有没有地雷?”我很肯定地告诉他没有。很不幸,当他们出发时,叶添顺第一个就踩响了地雷。当他被担架抬下来时,一边趴在担架上,嘴里一边在骂我:“6班长,你他妈还说没地雷。”自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战友。如今快30年了,真希望在今生今世能再见到他,向他道歉。
密林中的路比想象中难走多了,其实根本没有路,我们靠着3把开荒刀在开路。害怕这个词,在离开阵地出发那一刻就已经远离我们。接着而来的就是担心,担心不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担心迷路,担心侦察排不能准时到达,担心开枪时会有臭弹,反正什么都担心。幸亏平时训练时地图作业和野外方向识别都过关,但仍花了整整6个小时,比预计时间多一倍,终于到达指定位置。人数点了一下也没少,刚把重机枪和班用机枪的火力位置布置完毕,天就开始亮了。
我班有好几个特等射手,在全军全师都挺有名气,再加上有一挺重机枪壮胆,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吧。大家对56半自动步枪情有独钟,在200米内都自信有百分之百把握。现在大家都按照平时训练方法,各战斗小组分别在不同位置准备好了。敌人哨所在我们右下方大概150米左右处。侦察兵将对这个哨所进行攻击捕俘,我们则负责阻击和掩护,射杀可能出现的越军,掩护侦察排后撤。
979年1月20日,星期六,正是正式开战前的第四个星期。约定的动手时间刚到,越军哨所那边便传来侦察排的微声冲锋枪声和敌人的叫喊声。没多久,又传来敌人的敲锣声,一听就知道是在呼救。过了2、3分钟,我们发现一批约一个连的敌人在越军哨所和果拢越军阵地中间的一个村庄弯腰冲了出来,企图包围侦察排。大约算一下,这批越军有一百多人,正兵分三路,中路冲向侦察排的捕俘手,其余两股敌人正企图左右包抄侦察排的火力组。一看就知道这批越军是久经战场考验的正规军。
为了分散敌人注意力和阻击越军对侦察排的包围,我下令开枪阻击。一瞬间,我觉得全身的血液好像都涌上了头部,心跳得像打鼓一样,害怕倒不害怕,就是紧张,气喘得要紧,准星和缺口老是对不在一起。一不留神,扳机扳了下去,还是一个长点射。平时总感觉自己枪法了不起,实在是徒有虚名的神枪手。到今天我可以肯定,打仗时的第一个点射肯定没有打中目标。连续打了几个长点射,引来了越军还击。这时人才慢慢镇定下来,想起连长平时训练时说的:第一、不是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长点射;第二、一定要边射击边转移位置。我赶紧照着做,并开始观察四周情况,进入状态。
侦察兵当时的情况又如何呢?有个和我一起参军的要好战友张锋,是个在军营长大的干部子弟,当时刚好在这个侦察排当兵,也参加了这次捕俘行动。几十年后写了一份回忆录,其中就回忆了这次战斗。张锋写道:“天已大亮,我被安排在火力组,覃凤宽班长是我的组长。我俩在半山腰以火力掩护排长带领的捕俘组。山顶是观察组,山下是捕俘组。7时35分,一个放牛的小孩经过,发现我和覃凤宽。我有点紧张地用手势问覃凤宽是否干掉他,覃凤宽摇了摇头。我开始观察周围地形,发现我的正前方约150米有一间草房,外面晾有衣物。我判断此屋有人住,估计是越南公安兵的哨所,应是我的观察重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还在担心刚才放牛的孩子是否会去报信。”
在8时5分,突然听到微声冲锋枪长点射后发出的声响,我知道捕俘行动开始。与此同时,我对面草房里冲出一个人,看了一看又回到屋里,拿来一个铜锣猛敲。我知道这是越南兵有情况的信号。覃凤宽让我干掉第一个,我举枪瞄准就是一个点射,越南兵应声倒下。我看他还在动又补了一个点射。在我开枪同时,屋里又冲出一个拿着枪的,覃凤宽开枪把他也击毙了。
枪声、锣声惊动了越南兵,他们的重机枪和高射机枪不断向我们山头打来。我看排长的捕俘组开始后撤并用手势通知我们各组掩护后撤。覃凤宽叫我上山顶通知观察组后撤。我一口气冲到山顶,但不见观察组(原来他们的位置不利于潜伏,换了地点)。我返回报告覃凤宽没有通知到观察组。
我们下山见到排长,并把观察组的情况报告了。会合后,撤到第二防线,组织火力反击。步兵在19号界碑355阵地左侧无名高地以重机枪支援。此时观察组还未返回,排长命令我和秦凤宽从后山迂回上去,再找观察组,其余各组提供火力支援。
我们冲过几个小山包来到一片开阔地停下,发现我们左翼有越南兵十几人向左后包抄,我们无法通过这片开阔地上山。秦凤宽叫我回去通知排长调一个小组来我们左侧掩护。我二话没说就往回冲,见到排长并报告了情况,来回两次已是筋疲力尽。排长只好安排我原地组织火力,叫另外一个小组前去。我简单说了情况和覃凤宽所在的位置。
不久,我听到覃凤宽所在位置传来枪声。突然,两个越南兵顺着山坡向下奔跑,正好位于我的瞄准线上,距离大约100米。我迅速进行了多次点射,才击毙其中一人,另一名则被身边的战友击败。
我回过头观察左翼的情况,意识到左翼非常危险。根据时间推算,包抄的敌人已经接近我们。于是,我立即让一个来自广东怀集的战友跟我一起去左边的小山包,掩护我排的左翼。这时,代替我的那个湖南兵站在对面的山顶大叫,并用手势表示有人受伤了,要求再派人过去。排长立刻让我带着一个战友再次冲了过去。
此时战场已是炮火纷飞,我们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4号、5号阵地的敌人也开始向我们开火,我们受到三面火力射击。排长用两瓦电台请求团炮兵支援,幸运的是,我们军队的炮兵力量强大。我来到与覃凤宽分手的地方,却发现他不在那里。由于当地树丛高达一人,我无法找到他。情急之下,我只好大声喊出他的名字。他听到我的呼唤后答应了我,根据声音判断他距离我身后约15米。
我立即冲了过去,发现覃凤宽身负重伤无法行动,身边还有一个越南兵,他中枪但仍未死去。我上前补了一枪。回过头问覃凤宽受伤的程度,他没有回答我,只是说很痛、很痛。当时我无法判断他哪里受伤。我看了看地形,发现不适合进行急救,便立即背上冲锋枪,再背起他的枪械,准备将他拖到山后的后方进行救治。
就在这时,从我的左后方传来一排子弹。我感觉其中一枪击中了我的后背。我心想这次完了!但我仍然保持清醒,慢慢地移动身体,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也没有感到疼痛。我立刻将背上的两支枪取下,这才发现原来子弹击中了覃凤宽的枪机,救了我一命。
我想应该是我在补越南兵的一枪时惊动了附近的敌人,但敌人并不清楚我的具体位置,否则早就瞄准我开枪了。我开始紧张起来,冲回山顶叫人下来帮忙。我们三人共同努力,你抬脚我抬手,好不容易将覃凤宽抬到了山后。我用匕首割断了他的弹带,撕开衣服,这才发现子弹是从右手臂进入,贯穿肺部,然后经左手臂穿出,血就像高压水泵一样向外喷射,用手都无法压住(他那痛苦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学过急救知识,但在这时候全都乱套了,加上这个部位无法包裹,只好立刻将其送往后方救治,希望他能坚持住。此时战场已控制在我军手中,周围不断的炮声和枪声让人分辨不清是谁发出的。当然,还是我军炮火猛烈地压制了对方。步兵增援分队也赶到了,掩护的任务交给了他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步兵吧。
10点多时许,我们轮流背着覃凤宽返回355主阵地。我已经背了一会儿实在力不从心了,将其交给其他战友背负。回到355高地后,救护队已等候多时。医生检查了覃凤宽的情况后摇了摇头说,他已经休克了。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医生为他注射了一针强心针。然而五分钟后,医生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就这样,我的最好战友、我的班长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站立了许久许久。
张锋可能记错了,当时我们并没有炮兵掩护。他听到的炮声是越南人发现我们负责掩护的机枪位置后向我们步兵打的迫击炮。
说回当时步兵的情况,对话机里传来侦察排有人受伤的消息,我只好派副班长带领一个战斗小组前出协助抢救伤员,并引领侦察排按我们前出路线撤退。我和其他战友继续阻击越军。班里的全部火力都集中打向村庄里扑出来的越军,重机枪则封锁扣考山脚公路上准备过来支援的越军,看来情况暂时受到了控制。越军的火力都被吸引到了我们这个方向。伤员抬回来了,是他们一个姓覃的班长,广西人。伤得很重,子弹从右手射入,穿过胸部,然后再从左肩部出。子弹应该是贯穿了肺部,血像水喉流出的水一样猛,军装被鲜血染红了,可人还是清醒的。侦察排开始撤退,我们负责掩护射击,每个人都恨不得把全部子弹立即射向越军。这时,越军在扣考山半山阵地的高射机枪当当当地打响了,迫击炮也开始向我们打来。炮倒没什么可怕,高射机枪则真要命。这是我们第一次被越军用高射机枪平射,也是第一批经历被越军高射机枪平射的中国士兵。我们的冲锋枪、轻机枪或重机枪,在越军高射机枪狂扫下都变得无力。因为高射机枪不在这些轻武器射程范围内,但我们却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周边的松树让高射机枪打得树叶直落。当时想,早知如此,多带一门60迫击炮就好了。自越军高射机枪和迫击炮开火后,我们开始交替掩护,不断改变射击位置。看来平日训练的单兵战术在战场上还真用得上。边打边掩护侦察排撤退,花了两、三个小时,侦察排战友才带着伤员回到国境线我方这边。大部队战友在边境山头上呼喊,可就是不允许越境支持。我们一边打一边退,好不容易也回到了国境线这一边。看看手表刚好是下午3时正,不知不觉打了整整8个小时。检查一下弹药,我的冲锋枪也就剩下2个还满的弹夹。侦察排的一班长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牺牲了。这是我们第一位牺牲的战友,他的名字叫覃凤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