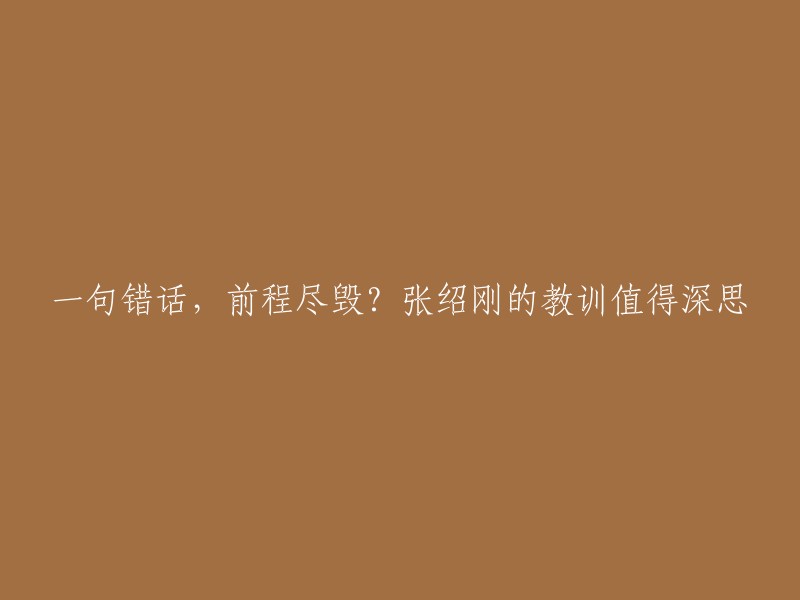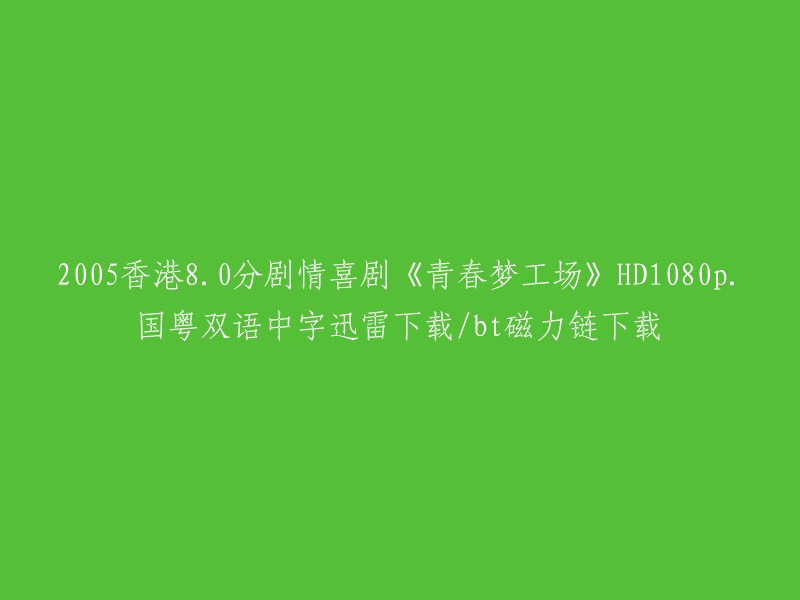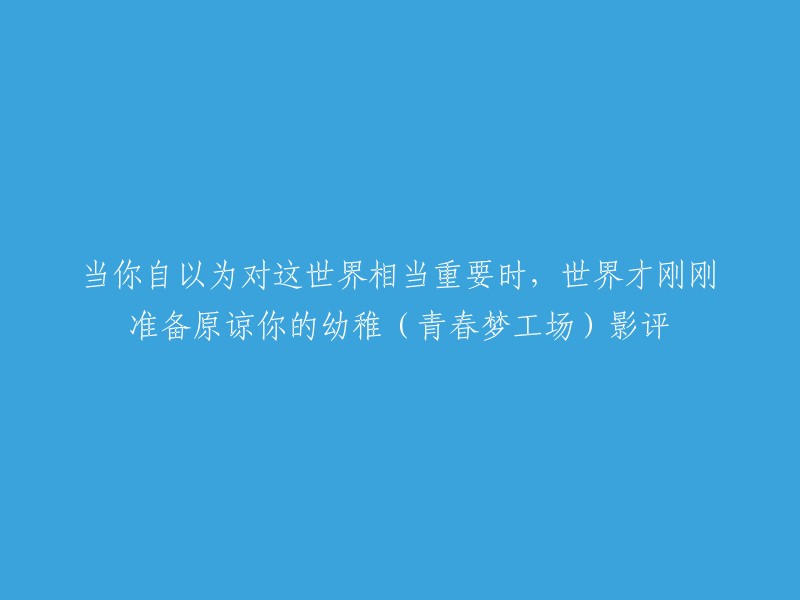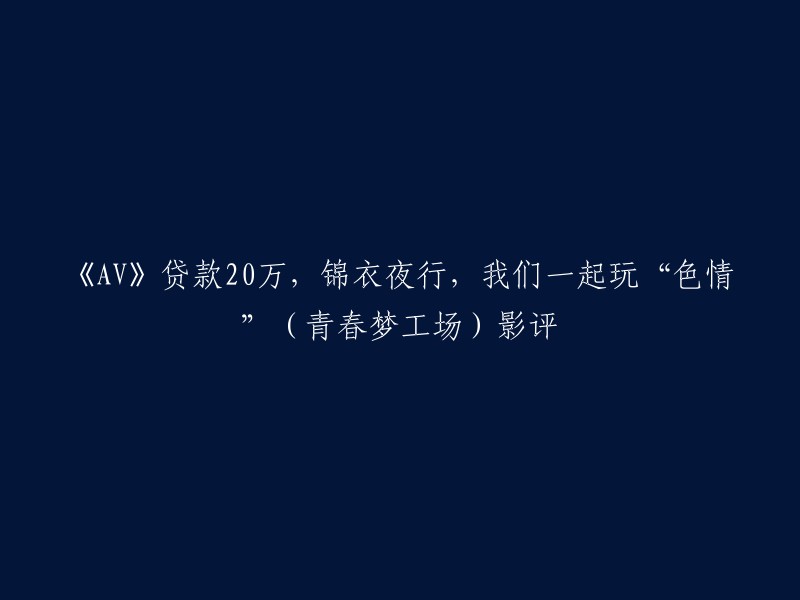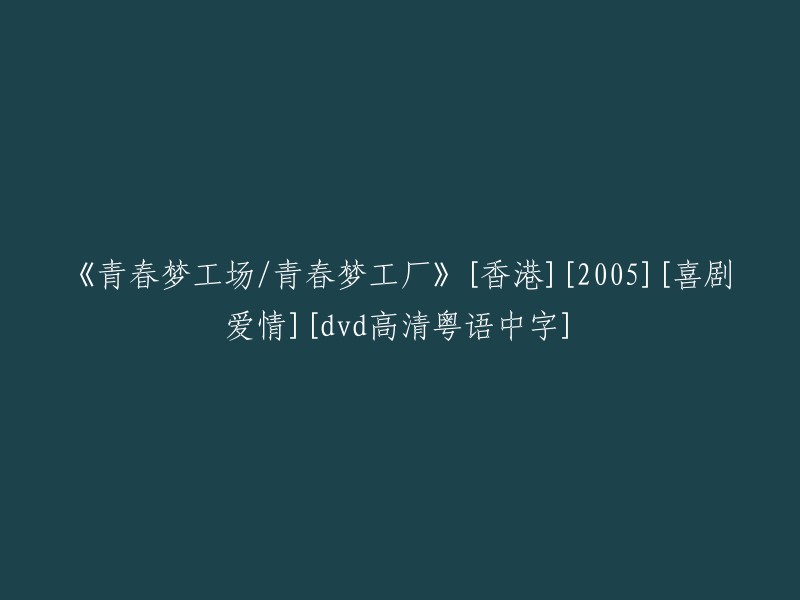BE预警,现背。
“当然了,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个关于黄子和高杨的很久之前和很久之后的故事。
我最好朋友的婚礼
1.
黄子弘凡千里迢迢回国来,参加高杨的婚礼。他下飞机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在飞机上因为没胃口所以根本没吃多少东西,匆匆奔波到酒店之后望着菜单发了一会儿呆,看什么都觉得腻,最后随便喝了一瓶酸奶,裹着被子卷上了床。他静静地把脸埋在枕头里,一侧的十字架耳饰硌得耳朵生疼。胃有点难受,脑袋昏昏沉沉,怎么躺也不舒服。他明明已经累到极致了,还是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于是蜷成一团,压住沸腾的胸腔。房间里死一般的空旷。
2.
他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吹着风,旷野和草原在隧道的尽头豁然开朗,天空张开手亲吻地面,而他却仿佛行尸走肉。他一头栽到在松软的泥土里,浑身软得不行,仿佛是被什么不可抗力狠狠碾进了地面,根本爬不起来。
高杨不知道为何忽然出现,蹲在他身边,二十岁的打扮,三十岁的语气,小心翼翼扯着他的一根尾指,依旧是别无二致的一声阿黄,说我们还没有好好告别,你怎么突然就不要我了。可没等他回答什么,少年便随即松开手,说那就算了吧,阿黄,我们算了。然后头也不回地冲向远方大得令人作呕的月亮。
一阵嘈杂。黄子弘凡费力地抬头看去,模糊的视线里,阿云嘎、郑云龙、方书剑、张超、梁朋杰、石凯、代玮、仝卓,他所有的好朋友,他的1975,他的老云家,他这些年热爱的挚友们,纷纷拉着手,一对又一对经过他身旁,目不斜视,渐行渐远。没有一个人看到他,没有一个人要去拉他一把。
他的父母、家人,也同样匆匆而过,当他是沼泽里散发出臭味的蛇虫鼠蚁,一滩烂泥。妈妈脚步踉跄,泪流了满面,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还是忍不住,飘忽地说“你怎么这么不孝呢”,然后被摇头叹息的父亲揽进怀里离开。
黄子弘凡想,是啊,他为什么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呢?怎么谁都不要他了呢?他虚无地伸出手,勾勾指尖,却只能抓住一把土。月亮像个酒桶一样滚过来,碾过他脆弱的躯壳。他想说什么,却好像被捏住了嗓子,什么也说不出。天空开始下雨,月亮碎了一地,波光粼粼的地面如同撒了满眼的盐,浸得黄子弘凡眼角酸疼。
黄子弘凡最后一次张了张嘴,但一开口嗓子里就呛进了土和雨水,最后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好真实的梦,他这样想道。可是为什么要重来一遍呢?他仿佛被撕扯成了两个个体,一半在受尽折磨,痛苦不堪,可是另一半却始终清醒地知道,梦都是反的。
似乎有“啪”的一声开灯的声音,黄子弘凡迷迷糊糊睁眼,玄关处亮起了光。“小黄子我给你带饭来了快来接旨......哎?你,你怎么哭了?”张超把打包好的食物放在桌子上,打开了卧室的灯,发现黄子弘凡居然闭着眼睛趴在床上泪流满面,这画面太过具有冲击性,让他一时间语塞。
黄子弘凡费力地从床上坐起来,他的领口都被眼泪染湿了,自己竟还没有意识到在流泪,只是觉得头昏脑胀,转转脑袋就针扎一样地疼。他接过张超递过来的湿巾擦脸,抽了抽鼻子,后知后觉才发现嗓子也沙哑干痛,整个人难受得厉害。难怪说不出话来。黄子弘凡有些奇怪地想,诶?我为什么要用难怪?
他敲了敲昏沉沉的脑袋,想回忆自己是为什么而哭,梦里到底有什么,然而这梦就像是随风飘散的一缕烟雾,他睁开眼就消失殆尽得彻底了,只能模糊地记起月亮,高杨,还有泥土的潮湿味道。
张超说:“我给你买了粥,你吃一点吧,我下楼给你买点药。高杨的婚宴在后天晚上,你要是好不起来就不能去接新娘了。”黄子弘凡“啪”地一声掰开一次性筷子,闻言抬眼看向张超,他本想点点头,但被病毒冲得眼框发酸发红,眼球转一转就胀痛得厉害,张了张嘴居然又不自觉地掉了眼泪,纯粹是因为头太痛而流下的生理泪水罢了,却同时让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
张超慌慌张张说一句对不起就拿着手机钱包出了门,黄子弘凡把白粥搅了两下,伸出手去擦那滴眼泪,才发觉自己脸上不止一道泪痕。他并没有想辩解。十年,他二十九岁了。
黄子弘凡的脸上逐渐失去了稚气,生活中的漩涡将他的影子冲刷得一干二净。他的脸色越发刻板,阴影中的他显得有些冷酷可怖。往日里,他的眼神总是温柔的,但现在的气质却越来越坚硬,不笑的时候简直让人不敢靠近。他的变化太大了,和十年前那个顽皮可爱的男孩儿简直判若两人。美利坚的大风大雨把他磨砺得如同钻石一般,冰冷、迷人、坚硬、闪闪发光。
他已经许久未曾生病,更不曾流泪。奇怪的是,他们年轻时都喜欢热闹,恨不得每天都聚餐唱歌,现在反而觉得别人的亲近和好意变得遥远陌生。他们曾经是那么要好的朋友。
张超大概是跑着回来的,额头上冒着汗,手里拎着一大堆东西。体温计、退烧药、感冒药、胃药、止咳糖浆、退热贴、冲剂胶囊等一应俱全,摆了一桌子。他催促黄子弘凡快喝粥,喝完后量体温。此时,黄子弘凡的嗓子已经沙哑得像破锣似的,但他还有心情开玩笑地说:“小张总果然雷厉风行,果不其然。”张超回敬一句:“滚你丫的!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别的!”
他看了一眼体温计,立刻拿出退烧药,给黄子弘凡倒水,把胶囊按说明数好放在手心,逼他喝糖浆吃药,然后又裹上被子捂汗。
三十八度二了,再烧一会儿他担心黄子直接羽化登天。到时候高杨在酒店里大宴宾客,而黄子弘凡却要在医院里挂三瓶点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俩的爱情推拉十年都没完结,还要称赞一句纠缠不清。
黄子弘凡生病后变得听话许多,知道这是最快退烧的方法。哪怕再讨厌吃药,他也得一口吞下去。真的睡饱了也要硬着头皮去睡。小时候最讨厌吃药片或胶囊,一旦卡住喉咙就吐不出咽不下,又难受又苦涩。
张超等他吃完,躺上床盖好被子,替他关灯,留下一盏床前灯。这段时间手机一直震个不停,但他没有去看一眼。他还买了一些水果,草莓、樱桃、香蕉等。张超知道黄子弘凡哪里缺这个,就算他想吃,酒店服务什么都没有提供,但他总是想尽力给他最年幼的朋友一点不一样的关怀。
“你快去吧,不用管我了。”
黄子弘凡躺在床上向他挥手,药里有一点安眠成分,困意已经上来。张超还想说什么,但黄子紧接着的话让他无法反驳。
“高杨的局应该还没散。”
说完他就翻个身,安静地躺在那里,似乎真的睡着了。
你看,他明明年纪最小,却从来什么都知道。
他又在做梦,梦见高杨对他说:“我不可以。”
高杨的美貌在他眼中依然迷人,即使是那模糊扭曲的脸也让他着迷。他伸出手去拉住高杨的手,却被冰凉的指尖轻轻推开,高杨说:“黄子弘凡,对不起。”
他说:“我们谁也没有活在小说里。我的父亲一生都献给了部队,脊梁从未弯过。他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与新疆的风雪为伍,直率、坦荡,从不妥协。他的血肉是雪山的地基。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人跪在我面前的样子吗?”
“他没有骂我,更没有打我。他只是埋怨痛恨自己,没有把我教好,让我走了歪路。他说他曾经有两个战友,轰轰烈烈地爱过,身败名裂,最后双双退伍,天各一方,一辈子都见不了面。他不愿意我吃这种苦头。他只是求我,求我放弃你,求我不要再让他让整个家族丢脸,抬不起头来。”
“他的膝盖不好,我怎么能这样害他?我怎么能?”
“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是我对不起你,我们分开吧,我一辈子都不会再爱上别人的,我们就这样吧。”
黄子弘凡仍然执着地去握住他的手,去擦他的眼泪,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他捉住颤抖的手指,揽在手心,说:“高杨,别叫我的全名。”
“我害怕。”高杨轻声说。
黄子弘凡眼眶滚烫,他听见梦里的他说:“高杨你别开玩笑啦,好不好?叔叔他那么喜欢我,他那么通情达理,不会这么对我们的。”
高杨静静地看着他自欺欺人,轻轻地说:“难道你也要我跪下来求你吗,黄子弘凡?”
流言如沸,烧得他痛不欲生。
他喊不出声,他开不了口。高杨的脸模糊着,梦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沸腾不止。高杨在天崩地裂中转身向山海走去。
“别走!”意识模糊的黄子弘凡感觉有人往他额头上搭了一块冰毛巾,给他盖上被子,不顾一切地将整件被子裹住他,不准他挣扎。那人对他说:“黄子弘凡,张嘴。”然后给他塞了一块薄荷糖,叹了一口气,小声地说:“你怎么还不会好好照顾自己啊?”
黄子弘凡半阖着眼,薄荷糖在嘴里融化,像雪的味道。他轻轻哼了一声,那人拨了拨他被汗浸湿的刘海,拍拍他的被子,温柔地说:“睡吧。”
这句话像镇定剂一样奇异地使他安心下来。他费力地抬手,想去握那人的指尖,却被一把按住。语气轻柔地哄孩子一般:“好好睡觉。”
黄子弘凡轻而易举地放弃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海面上漂浮的碎冰,遇到暖流就被融化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不是暖流的错,也不是他不应该奢求拥抱月亮。在昏睡前的一秒,他还是给了自己一点希望,他沉思着,也许是高杨吧?这是银色山泉的味道,是他喜欢用的香水。
该相逢的人总会再次相逢,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哪怕再相逢时已经面目全非。黄子弘凡仍然无法去接新娘。他的感冒好了大半,只是咳嗽依然严重,像个老旧的风箱。他坐在酒店沙发上,一边喝冰糖雪梨,一边给张超发消息:“我不做伴郎,我就去晚宴了。拜托你和代玮了。”张超过了很久才回复,看着屏幕上对方正在输入的内容反反复复出现好几遍,最后发来一个轻飘飘的“好”。
他没有联系高杨,因为他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他们的对话框停留在一周前的晚上,高杨突然给他发消息:“黄子,在吗?”他回复“在的,怎么了?有什么事吗?”高杨说:“我要结婚了,你可以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在北京。”“当然,我肯定会回去的,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黄子弘凡没有问新娘是谁,也没有问他们是如何在相识的,只是良久之后轻轻发送一句:“你开心吗?”高杨发来一个笑脸,圆圆的脸,憨憨的笑。这么多年了,他依然喜欢用这些小表情。
“为什么不呢?”他回复道。是啊,为什么不呢。高杨很特别,他的爱独一无二。黄子弘凡的爱是予取予求,你来爱我,我将同样以爱来回报你。我允许你从我这里拿走爱意,但不是全部。这更像是一场交易。而高杨不是这样的,他的爱是张开手,把最脆弱的怀抱展示给你看。把最小心翼翼的温柔捧个满怀。告诉你,你可以带我走,你也可以留下我。他简直是自杀式般爱人,粉身碎骨也要从血管里开出玫瑰,等你来摘。
很多年前,当他离开时,曾流着泪想,他会遇到更好的人。他会遇见下一个黄子弘凡。不管是谁先离开这次别再是他。可是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黄子弘凡这样的人。高杨挽着一双手踏上红毯的时候这么想道。
他能看到微笑鼓掌的双方家人和朋友,能看到父亲和母亲抬起手来掩面而泣;能看到张超和代玮坐在一起遥遥而望,目光穿过十年,笑容一如既往。他们是真心祝福他;能看到昔日同学冲他喊高杨今天真帅;甚至能感受到妻子搭在他臂弯上汗津津的手心。她捧着的那一束红玫瑰耀眼又夺目,开得正好。
可是他看不到黄子弘凡。
想想也是,假如教他来望着他怎样向别人许诺一生,那是多残忍的一件事。他的病还没好,十一月份的北京已经有点冷了,他还是不要奔波比较好。可高杨又矛盾地想,他这辈子,只能遇见一个黄子弘凡。这么重要的时候,他怎么能不在呢。
新郎的胸针在他心上滚烫,高杨竟然有些想哭。阿黄,你怎么不来祝福我。他想。他几乎看到了前半生认识的所有人,善意的,或者厌恶的眼神,伪善,或者真心实意。他全然接纳,也坦然面对,因为那些人不能再伤他分毫。可看不到黄子弘凡使他胸口酸痛,那是他十年的爱人和青春,甜蜜和苦涩的化身。
那是他这辈子最喜欢的人,最爱的人,是他曾经不顾一切想要一直在一起的爱人,是他如今,所谓的,最好的朋友。6.
黄子弘凡来的时候堵车了。他没有赶上高杨和新娘走红毯,等他推开婚宴大门的时候,正好是新郎上台讲话的环节。背景音乐被调小,混在嘈杂的人声里,可他听得真真切切。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But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your heart is all I own。
......
But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
是《perfect》。黄子弘凡站在红毯尽头的花环下,他抬头,正好看到高杨穿着一身黑西装走上台去。
他莫名其妙地想到,其实,在现实中遭受他梦中这一切的不是他黄子弘凡,而是高杨。现实中,众叛亲离的是高杨,先被放弃的人是高杨,到最后谁也没有拯救他的也是高杨。先松开手的,是他黄子弘凡。
他才是那个可耻的背叛者,懦弱的小人物,不敢抬头看光明坦荡的高杨、只敢躲在美国的混蛋,匆匆而来,连对视都做不到的胆小鬼。很多年前,他们恋情曝光,黄子弘凡的父母先封锁国内消息,然后赶到美国,牢牢地把他看起来,高杨在维也纳两个月都联系不到他,赶完final exam之后奔波到伯克利去见爱人,却被自己的父母同样拦下来。
黄子弘凡的家人朋友轮番给他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劝他迷途知返,劝他不要把一辈子浪费在一个男人身上,劝他治病。
父亲说:“你不可能一辈子呆在美国,如果坚持要和那个男生在一起,我会让你在国内身败名裂,你什么都得不到。他也是,你们都是学音乐的,知道人脉比才华更重要。”
到最后的时候,父亲也有些哽咽,他沧桑极了,看黄子弘凡的眼神就像看一块朽木,他说:“假如全世界你谁都不认识,只有你一个人,我当然可以让你做你想做的事,爱你想爱的人。可是你不是这样,你有自己的圈子,你是我的孩子,你要怎么活下去,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别人会怎么看你,怎么看那个男生,怎么看我们一家子?”
“为我们考虑考虑,为你考虑考虑,为那个男孩考虑考虑。算我求你,别毁了两个家庭的人生,你们原本都可以有光明又漂亮的前途。”
黄子弘凡被关起来之后从没有流过眼泪,父亲打他,母亲骂他,他都梗着脖子不肯屈服。可是当他听到为那个男孩考虑考虑的时候,却一下子泪流满面。他全副武装,为爱而战,可是他不愿他的男孩受伤。当他发现他已经开始有所偏颇的时候他当即明白,他完蛋了。高杨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到底爱谁,到底如何想,他们之间究竟会有如何的以后,他通通抓不住答案。
父亲扔下最后一根稻草,说高杨的父母也很生气,他母亲已经进了两次医院了,他是军人家庭,怎么可能接受你。他父亲要和他断绝关系,他会众叛亲离,他会孑然一身。
当天晚上,黄子弘凡接到了高杨的电话。
高杨颤抖着声音,手和声音一样抖,他就要抓不住手机了,他流着泪:“阿黄,我父母明天就要带我回国了,我现在在你家门口的咖啡厅等你。我会一直等你等到十二点,今晚十二点之前,只要你出现在我面前,我们远走高飞,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我给你我全部的爱。”
高杨的语速从没有这么快过。
“阿黄,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我会等着你的,阿黄,只要你来,只要你来!”
黄子弘凡张了张口,他听到高杨带着哭腔的声音,本来想说“你别哭”,可是开口的时候却说:“对不起。”
他又重复了一遍,一字一句:“对不起。”
这就是他留给他们之间的所有爱情的最后一句话。以你好开始,以对不起结束,平淡地、庸俗地,像这世间的所有褪色凋零的爱情一样。他屈服了,草率、直接又狼狈。
十二点的钟声敲响,面前的咖啡冷得像一杯冰山。于是高杨从此知道他们再也没什么特别的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回到十年前,二十九岁的黄子弘凡一定会冲上前去,紧紧拥抱他心心念念的人,用唇舌描绘未来的美好,告诉他,永远不让他流泪。然而,十年的光阴流转,一切都已改变。
当时的十七岁的黄子弘凡只能无奈地站在原地,说出那句对不起,而二十九岁的黄子弘凡也无法回应他的真心。多么荒唐,多么凄凉。
十年匆匆而过,如今他们都已长大,成为了真正的男人。他们穿着西装革履,一个站在舞台上,一个站在拱门下,遥遥相望。这一幕如同梦境般美丽,高杨的领针闪烁着光芒,就像黄子弘凡心中憧憬已久的新郎。他差一点就把这里当成了他们俩的婚礼现场。
“你今晚真美。”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高杨接过话筒,他依然保持着淡然、喜悦和羞涩的表情,从不让情绪失控。
他低下头,沉思片刻,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感谢之词,感谢大家、感谢父母、感谢妻子。最后,他说:“大家都知道,我这一路走来,离不开我这些朋友的帮助。”
他一一列举了许多人的名字,那些人向他举起酒杯示意,高杨也回以微笑。
“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黄子弘凡。”
“他们对我都很重要。”
“你们就都祝福他吧。”
高杨紧握话筒,他终于敢于低下头与黄子弘凡对视,目光交汇,仿佛交换了最后一个深情的吻。他再次露出温柔的笑容,眼底水光闪烁,瞳孔中充满了与十年前如出一辙的情感。
“祝福黄子。”他如此坚定地说。
黄子弘凡是否回应了一句“祝福高杨”?高杨下台时听着满场的掌声,心里琢磨着这个问题。
他根本不想在自己的婚礼上祝福前男友是多么不合时宜的事,也不想让父母难堪。他只想简单地祝福自己最爱的人,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他曾渴望拥有关于他的全部,如今只求一个微不足道的、卑微的随口祝福便已足够。
“祝福黄子。”高杨再次低声重复了一遍,这次是真心实意的,声音小到他自己都差点听不清。
他闭上眼,幻想着梦中的场景:刚刚二十岁的黄子弘凡,以及他们永不完结的爱情故事。他想,自己只是一个胆小鬼,明明看到黄子弘凡走进会场的那一刻,喂他吃薄荷糖的时候,走上舞台拿起话筒的那瞬间,他多么想大声告诉对方:“黄子弘凡,我喜欢你十年了!你能不能带我走?”
高杨安安静静睁开眼,轻轻牵起站在一边的妻子的手。尽管妻子的妆容有些凌乱,但眼中闪烁的喜悦之光让他的勇气瞬间消失殆尽。
然而,高杨始终不知道的是,十年前的那天晚上,他执着地坐在咖啡厅里等待着他的挚友黄子弘凡,其实黄子弘凡早已来到了现场。
黄子在高杨背后默默坐了一整晚,眼睁睁地看着高杨的咖啡冷却,看着他失魂落魄地从咖啡厅出来,悄悄跟在他身后,最后一次送他回家。当他看到到处寻找高杨的父母嚎啕大哭地抱住高杨时,心中五味杂陈。
黄子弘凡向来外向,唯独这一次,他以沉默而内敛的方式,最后一次,送别他最心爱的人。
那句话始终如雷贯耳,响彻在黄子弘凡的耳边:“为高杨考虑考虑吧。”他永远记得,高杨那天点了一杯蓝山咖啡,从此他再也不敢喝蓝山。
在高杨的酒宴上,他没有现身。然而他并不知道,他的男孩曾拼尽全力,想送给他一个完整的月亮。对于黄子弘凡来说,他早就已经把全部的爱送给高杨了。他是飘浮的碎冰,不自量力地想要去托举月亮,却首先融化了自己。
黄子弘凡回国之前,特地去纹了一个身。纹身师问他想纹什么?他想了想,回答道:“纹一个名字吧。”
"GYON。"
在我离开之前,在我胸口刻一个名字,以此来铭记我因爱而亡,希望我的爱人将永不回头,沿着最好的方向狂奔,不必再等我。
高杨领着妻子去敬酒,敬到黄子弘凡这一桌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黄子刚刚拿奖的那首歌。高杨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然后也举起酒杯说恭喜。他对妻子介绍说:“这是黄子弘凡,是我十年来最好的朋友。”
妻子点头,笑得甜美动人,伸手和黄子弘凡握手,说你好。黄子说嫂子好温柔,高杨说哦哟,你终于肯叫我哥?熟稔地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什么都没有。
只有黄子弘凡自己知道,他再听高杨讲话,心口还是不可抑制地滚烫了起来。可是他们插科打诨了这么多句,高杨还是没有问出最想问的那句话,或许这辈子都没有资格和机会再问了。
9. 在你写的那么多情歌里,有没有一首,或者哪怕只是一个旋律,是因为我?
全部都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