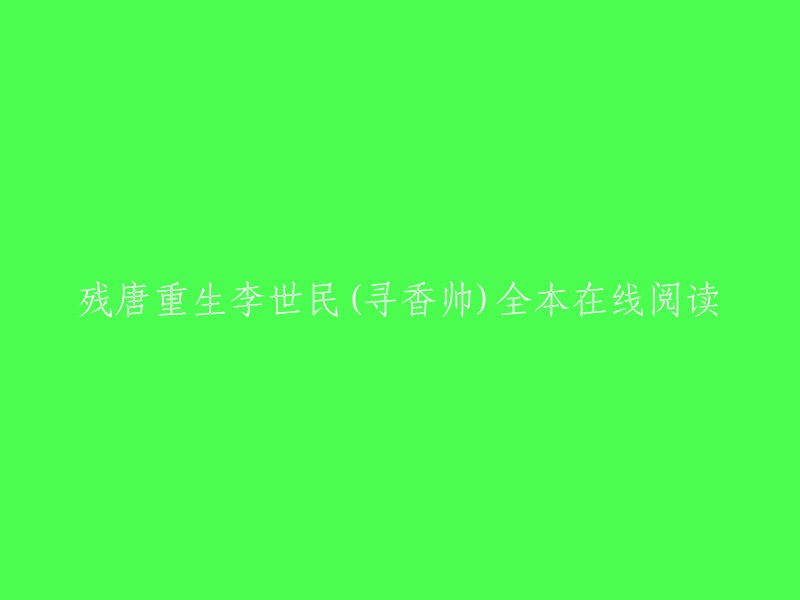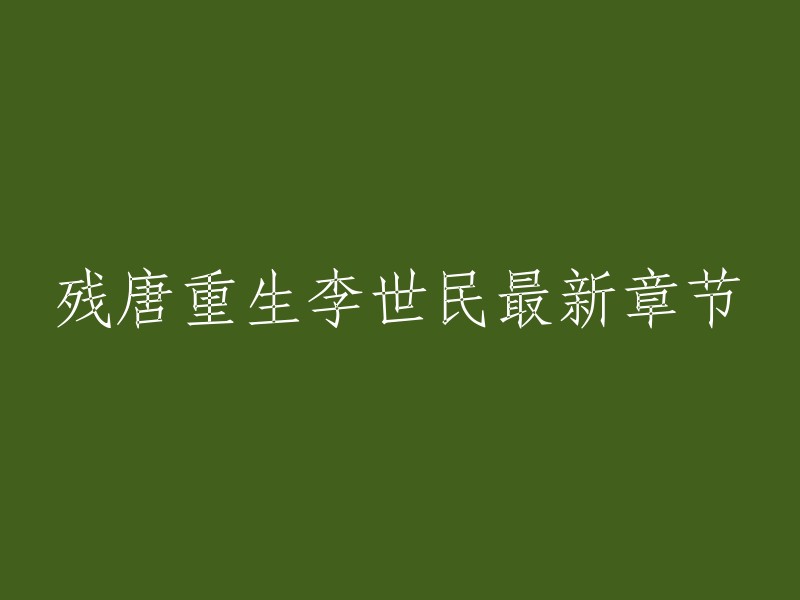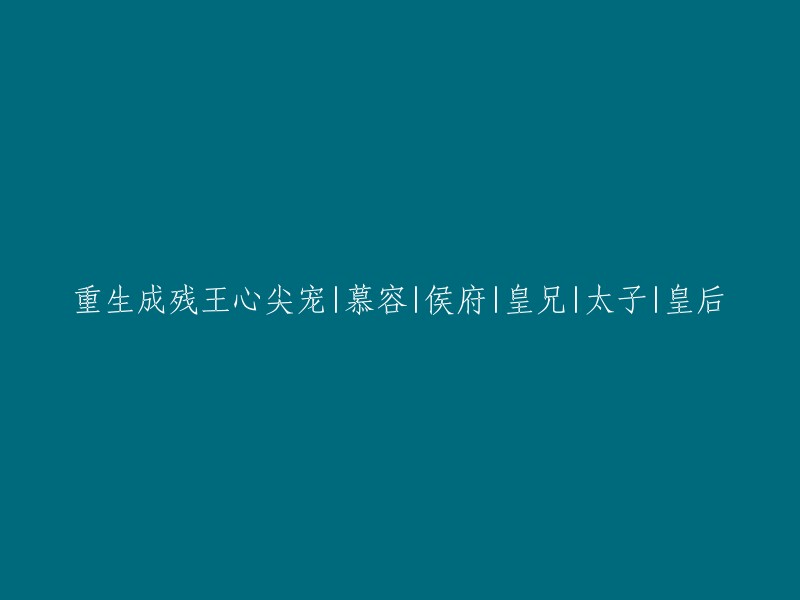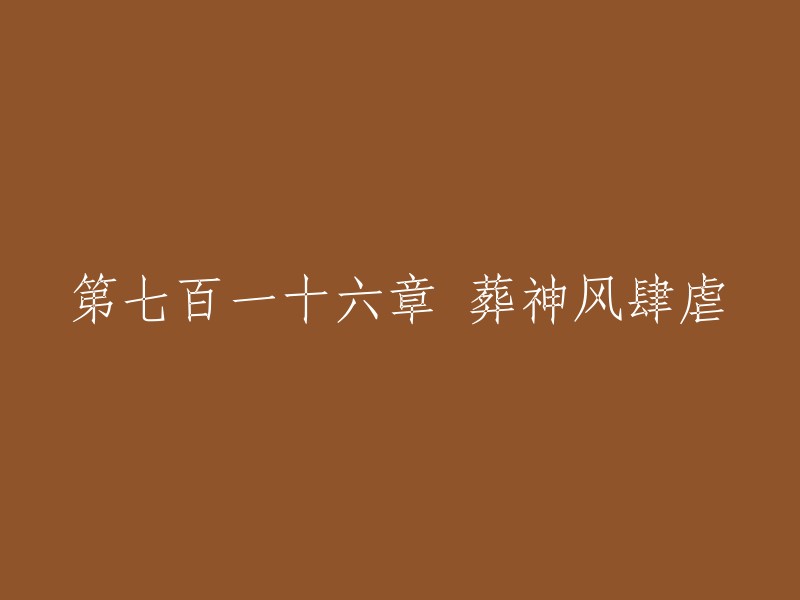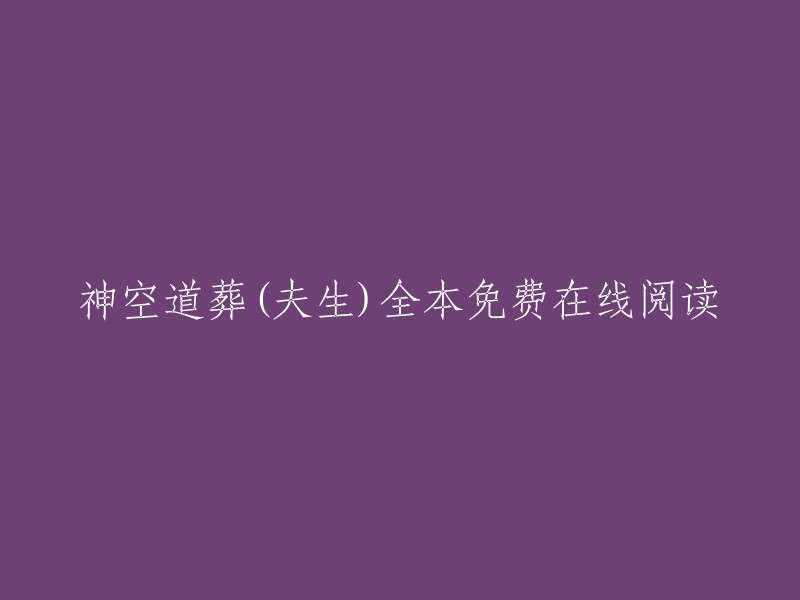初夏黄昏,华夏东州,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五毒教主许纯良赤着双脚走在粗糙坚硬的柏油马路上,他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上一刻还在昆仑之巅力战正派九大宗门,正准备放出绝招大杀四方之际,陡然间电裂苍穹,五雷轰顶,脑海中随之一片空白,清醒之后周遭一切都改变了。
没有了崇山峻岭,没有了九大宗门,没有了刀光剑影,也没有了舍命追随的十万教众。抬眼看——灯火辉煌,宛若置身星河。一辆辆形态不同的铁甲战车来来往往。一道道或惊诧,或嘲讽,或惶恐的目光向他投来。渡劫的想法刚刚出现,随之纷繁复杂的念头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之中——
许聪,字纯良,二十一岁,高三复读,父母离异,从小跟随爷爷长大,性情内向,敏感懦弱,悲观厌世。这是我第三次落榜了!爹妈不待见我!同学看不起我!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整个世界都嫌弃我,鄙视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许纯良诧异于脑中绝望悲观的想法,这绝不属于自己。十年身未死,卷土定重来。扛得住击打,耐得住寂寞,这是一个邪派魔头最基本的自我修养。若无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勇气,我许纯良焉能折服桀骜不驯的五毒教众?更谈何雄霸天下?
父母生我已是大恩大德,复有何求?同窗看不起我?老子也看不起你们。世间有人胆敢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吾必杀之!虐之!吾少年立志,此生纵横江湖,不求流芳千古,只求快意人生轰轰烈烈。天不生我许纯良,人间万古如长夜!心念及此,许纯良胸中升起豪情万丈。
吱嘎!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噪声,一辆黑色宝马X5在距离许纯良半米处急刹,司机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握着方向盘,嘴上还叼着一支烟,凶神恶煞般盯着马路中心高瘦羸弱的年轻人。车灯投射下的许纯良犹如站在舞台的中心,身高一米八零,面色苍白,和普遍营养过剩的同龄人相比过于瘦弱了一些,两道刺眼的强光让他感到有些眩晕,眼前白花花一片,笼罩着一层雾气。
许纯良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鼻梁上架着一个新奇的玩意儿——眼镜。他过去虽然没有见过这物件,仍然毫不费力地想起了它的名称。不断涌入的全新意识迅速丰富着他对周遭世界的认知。摘下眼镜,眼前的世界顿时清晰起来。雨越来越大,黄豆大小的雨点爆豆一样击打在他骨感白皙的胸膛上。
许纯良仍然沉浸在这全新世界带给他的震撼之中,甚至忽略了这近在咫尺的铁甲战车。哔!哔哔!车内的司机按捺不住火气,摁响了喇叭,催促眼前只穿着一条裤衩的年轻人赶紧让路。
许纯良被喇叭声惊了一下,抬头望向车内的司机。双眼之中迸射出凛然杀机,宝马司机本想骂他,但接触到他慑人的目光,身体突然有种如坠冰窟的感觉,不由自主打了个冷颤,即将脱口而出的脏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许纯良转身迎着车流走去。正值下班高峰期,马路上车来车往,车主们看到一个只穿着裤衩的青年大摇大摆逆行在快车道上,纷纷选择转向避让。突然出现的状况让道路上乱成一团,紧急刹车、狂按喇叭声此起彼伏。
许纯良熟视无睹,大道独行。值班警员发现这一状况时,他已经步行来到和平大桥上。扶着凭栏,心潮起伏,记忆如同滔滔江水汹涌澎湃。他意识到自己并非遭遇雷劫,而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他不再是五毒教主许纯良,只是一个三度落榜的复读生许聪。
正在此时,闻讯赶来的警员陆奇在距离事发点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停车。任何人看到眼前的这一幕首先想到的是有人想要投河。自从和平大桥十年前建成通车之后,几乎每年都会有悲观绝望的厌世者从这里一跃而下。
陆奇第一时间就认出了许纯良。他们是市三中的校友,陆奇高许纯良三届。别看许纯良在学校算不上什么风云人物,可他的爷爷许长善却是东州的知名人士,一位医术高超的老中医。顺堤路的老字号中医诊所回春堂就是他家祖传的堂号。
陆奇不敢轻举妄动,他让搭档驱散围观群众,以免进一步刺激轻生者。先向总部寻求支援,联系许老爷子,让他尽快赶来现场。围观群众纷纷掏出手机拍摄,现代科技的进步让新闻从业者的门槛无止境降低。都在看热闹,可心思各有不同:有好心人奉劝许纯良回来,有人指指点点发表评论,其中也有人唯恐天下不乱。
“你倒是跳啊,我特么顶这么大雨看了半天,你咋不跳......”陆奇怒视怂恿者,对方被正义的目光震住。许纯良深深吸了一口气,刚才他试图运行内息,却发现经脉之中空空荡荡。昔日引以为傲的浑厚内力竟然凭空消失了。没有了神功、失去了十万教众,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他彻底成为了孤家寡人。若宿敌来袭,不堪设想。
“许聪!”呼唤声打断了他的沉思。许纯良循声望去,看到制服笔挺的陆奇向他走了过来。虽然从未见过,但陆奇出现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想起了陆奇相关的一切:自己同校的学长,篮球打得特棒,运动天赋很高。
陆奇向许纯良笑道:“怎么?不认识我了?我也是三中毕业的,咱俩还一起打过球的。”许纯良平静地望着陆奇,脸上的表情风波不惊。
陆奇将他的表情理解为对生活的绝望,站在距离许纯良三米左右的地方停下,扶着护栏向桥下看了一眼:“水流够急的,再好的水性也施展不开,掉下去就没命了。”
许纯良饶有兴趣地看着陆奇:“你以为我要投河自尽?”
陆奇笑着摇了摇头:“你不会,年纪轻轻的,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老人家着想吧?你爷爷今年有七十岁了吧?身体还好吧?”
雨渐渐停了,陆奇掏出一盒烟,在许纯良眼前晃了晃:“抽烟吗?”
许纯良眨了眨眼睛,过去从未尝试过。
“来一根!”陆奇趁着上烟的机会向他走近,当距离拉近到一米左右的时候,陆奇一个饿虎扑食冲了上去,在这样的距离内,他有足够的把握控制住许纯良。
然而,眼前白光一闪,陆奇志在必得的出击竟然扑了个空,连目标的衣角都未碰到,就因为失去平衡重重扑倒在了地上。
许纯良只是向左移动了一下脚步,内力虽然消失,可步法仍在,利用灵蛇八变轻松避开了陆奇,他非常清楚陆奇是要救自己,所以并未反击。
此时闻讯赶来的警员从四面八方冲了上来,许纯良内心警惕顿生,正准备出手之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从警车上赶了下来,因为太过焦急,下车时候立足不稳,脚下一个踉跄,身边警员慌忙将他扶住。
老者焦急大喊道:“纯良!千万不要做傻事!”
许长善在得知在和平大桥寻短见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了过来。老爷子七十有三,身体虽然硬朗,可毕竟年事已高,一路奔波过来已经是气喘吁吁。
看到宝贝孙子只穿着一条裤衩站在桥边,老爷子一颗心悬到了嗓子眼。今天是高考放榜之日,许纯良再度名落孙山。三次高考,一次比一次成绩差,这次竟然连本科线都没过。
依着许长善的意思,与其去野鸡大学浪费时光,不如跟着自己学习医术。现在国家刚刚出台了中医师承政策,自己年事已高也的确需要一个衣钵传人。虽然在当今时代西医已经完全占据主流,中医式微,但只要继承了自己的衣钵,守着这间祖传的诊所,纵然不能大富大贵,至少可保衣食无忧。
许长善不止一次跟孙子提过这个建议,但这小子对学医毫无兴趣。加之性情内向、沉默寡言,很少跟他人交流。尤其是第三次复读以来,全年跟他说过的话不到十句,爷孙俩之间的代沟越来越深。
许长善虽然医术高超,但对孙子的状况也无能为力。心病还须心药医,针灸药石之术也只能帮助许纯良怯病强身、疏通经络。
“不要过来!”许纯良大吼一声,灿若惊雷。
十多名警员硬生生停下脚步。刚刚扑空摔了一跤的陆奇哭丧着脸从地上爬了起来,示意大家自己没事,是自己扑空摔倒,跟许纯良没有任何关系。
许长善来到近前,颤声道:“纯良,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他和孙子许纯良骨肉相连,十八年前老伴去世后,他们爷孙俩相依为命。如果孙儿出事,许长善将失去活下去的意义。
许纯良打量着老泪纵横的许长善,脑海中的记忆一点点被唤起。“爷爷?”“嗳!”许长善大声答道。“纯良,爷爷答应你,不逼你学医,你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跟我回家好不好?”许纯良环视四周,围观人群越来越多,还有闪烁着红蓝灯光的铁甲战车呼啸而来。既然九大宗门没有发现,他决定先离开这里再做打算,于是点了点头道:“好!”
位于顺堤路的回春堂是东州的老字号医馆,据许长善所说,这块牌匾是雍正御赐,许家祖上曾经当过宫廷御医。不过木器厂的老冯关于这块牌匾有另外的说法,牌匾是他爹一手打造的,之所以记得如此深刻,是因为他穿开裆裤的时候认字就是从回春堂开始的,他亲眼目睹了牌匾制作的全过程。
无论怎样,回春堂历史悠久毋庸置疑,许长善的医术也是有口皆碑,尤其是在治疗骨伤方面,祖传的膏药极其灵验。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国医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呈断崖式下跌,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医道之中西风压倒东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样的大环境下,回春堂的生意自然受到了影响,年轻一代前来光顾的越来越少,再加上许长善年事已高,正骨推拿都对体力有要求,身体所限不得不减少了这方面的业务。以许长善的名气,慕名拜师的不在少数,可许长善在授业方面因循保守,秉承着传子不传女的原则,眼前能指望的只有孙子许纯良。如果孙子不肯学,许家的医术只能失传了,许长善也因此而忧心忡忡,生恐无法面对列祖列宗。
许纯良自小性情孤僻、沉默寡言,按照时下的说法,有着非常严重的社恐症。学习成绩也不怎么出色,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特长。根据学校老师反映,这小子注意力不集中,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不爱交际,也没什么朋友。如果不是许纯良自己坚持,许长善是不会让他复读三次的。高考成绩一次比一次低,这次总分连四百都没过。民办本科都对他来说都遥不可及。以他的条件完全可以选择出国,可许纯良不肯去。许长善也只好作罢。
许长善并不看重学历,他自己就没学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医术被认可。中华医术博大精深,研究得是天人之道。西洋医学岂能相提并论?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医学基本上都是师父带徒弟的传承方式。足以证明这种方式是符合国情的。
陆奇开车将这爷俩送到了回春堂,途中了解到许聪的身份证丢了。他让许聪尽早去分局补办,顺便开导了他几句,高考成绩并不代表一切,自己也没参加过高考,现在不一样端着铁饭碗为人民服务?
许长善望着身边只穿着一条裤衩一言不发的孙子,心中又爱又怜。许纯良才三个月大,他爹妈就分了手,两人把孩子往自己这里一丢,一个飞去了美利坚,一个去了欧罗巴。不久以后,各有各的小家,各有各的儿女。不到逢年过节,谁也想不起国内还有这个孩子。
许长善认为孙子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父母造成,当然自己也有责任。这些年来,忙着治病救人,忽略了对孙子的教育。回头想想,这孩子小时候还是很聪明的。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将店里的草药认识得清清楚楚,六岁就能将人体奇经八脉、三百六十二个窍穴倒背如流。只是上学后性情突然就改变了,许长善到现在都清晰记得,有一天他放学哭着回来,问自己:别人都是爸爸妈妈接送上学,为什么他没有?也是从那时起,就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越来越不爱和外界交流。
警车在回春堂门口停下,陆奇第一时间下车,帮忙拉开车门。许老爷子颤巍巍走了出去,陆奇体贴地搀扶住他的手臂。随后离开汽车的许纯良道:“我来吧!”他主动搀扶住爷爷。陆奇看到他的举动,稍稍放下心来。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在意的人是不可能去关心别人的。种种迹象表明,许纯良已经放弃了寻短见的想法。
许长善提醒孙子:“小心脚下,别扎着。”到现在许纯良还赤着脚呢。“瞧,你爷爷多关心你。”陆奇向许纯良笑道。许长善正想交代孙子请陆奇进来坐坐喝杯茶,不等他开口,许纯良道:“陆兄,刚才真是辛苦你了。如不嫌弃,还请移步寒舍,在下略备薄酒,与陆兄把酒言欢。”
许老爷子懵逼了:“我孙子这是受啥刺激了?过去没见他跟人这样说话啊。”
陆奇心说到底是国医世家,话说得跟文言文似的。这么年轻的小伙子,跟时代脱节了。他笑了笑道:“改天吧,我还在执勤,门口不能停车太久。快进去吧,照顾好老爷子。以后别再让老爷子担惊受怕了。”
许纯良暗忖:“真乃义士也!此人可交!”向陆奇抱了抱拳,话不多说,搀扶着爷爷进了回春堂。陆奇目送他们进门,这才驱车离开。
回春堂是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楼下是诊所,楼上便是爷俩住的地方。店里有一位姓林的中年妇女,平时负责看看店、打扫卫生、帮忙做饭。至于抓药看病一样不会。许长善之所以雇佣她就是因为她不懂医术,祖传医术岂能让他人随意窥探?
许长善担心孙子再寻短见,所以一直跟着他回到房间,让他去洗澡换衣。许纯良保存着前世的记忆,相较而言,今生的意识有些支离破碎。然而,他从这些碎片中迅速汲取有用的信息,意识到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不可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赤身裸体的站在浴室镜前,许纯良发现自己的样貌和之前变化不多,只是白皙了一些,瘦弱了一些,头发也短了许多。这个世界的男人发型大多如此。浴室狭小,方寸之地并无浴桶。许纯良心生诧异,但很快从记忆中找到了有用的信息:头顶这个莲蓬状的铁器应当就是浴缸,用手摸了一下,质地却并非金属。小心打开阀门,百多条水线倾泻而下。许纯良吃了一惊,向后退了一步,仍被热水溅到。他的反应力和移动速度明显下降。
关上阀门后,又打开阀门,水线随之停止开启。机关极其巧妙,很快发现阀门可左右旋转。左旋水流变热,右旋变冷,端得是巧夺天工。许纯良反复启闭把玩,良久方才开始沐浴,洗去一身的雨渍和前世的血腥。闭上双目尽情享受温暖水流的冲刷。
一只五彩斑斓的寸许长蜈蚣沿着许纯良背后的墙面迅速游走,贴着地面来到他的足跟处,准备发动攻击时,一只手抓起了蜈蚣。原来这是许纯良及时发现的小虫子。百足蜈蚣在他的双指之间挣扎拧动,却不敢发起攻击。许纯良盯着这蜈蚣,双目灼灼生光,张开大嘴一口将蜈蚣吞了进去。
许纯良沐浴完毕,老爷子许长善在外面守候已久。足足等了半个小时,将自己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的许纯良换上衣服走了出来。望着神清气爽的孙子,许长善松了口气。中医的基础就是望闻问切,数十年的行医生涯让老爷子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经历这场变故,宝贝孙子变得精气十足,明显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破不立,这次的挫折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练,也许会帮助他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此时林妈已经准备好了晚饭,招呼他们爷俩去吃饭。一只蜈蚣根本满足不了饥饿难耐的许纯良。面对美食,他早已食指大动。尽管如此,许纯良仍然没有忘记礼仪之道。先给爷爷盛饭,一举一动尊足礼数。
许长善没什么胃口,微笑道:“我不吃,看着你吃就行。”许纯良点了点头,又去给爷爷泡了杯茶,这才坐回饭桌前吃了起来。
许长善端着茶杯笑眯眯地望着狼吞虎咽的孙子,心中生出些许安慰。他想起塞翁失马的故事:“安知非福”,这次的经历对孙子来说也许是一次难得的历练。过去别说是给他盛饭了,就连话都懒得多说一句。如今看来,纯良明显懂事了很多。
天下长辈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出人头地,但天资各异,有些孩子并不是学习的料,也不能强迫他们去学习。可是如果他们不愿意继承家族的事业,年纪轻轻就一直待在家里,那岂不是会与社会脱节,变得越来越孤僻?
许长善陷入了沉思。正当他陷入思考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许叔在吗?”来访者是长兴医院的副院长高新华。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来回春堂拜访,目的并非求医。因为长兴医院位于回春堂隔壁,医院的二期规划将包括回春堂在内的棚户区划入征迁范围。其他住户基本上都同意了,但最难说服的是回春堂,因为许长善在这里德高望重,只要他同意,征迁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医院方面也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包括现金补偿、在院内以合作方式为许长善开设中医专家门诊,或者另觅新址重开回春堂。然而,老爷子认死理,说什么都不肯搬家,还拿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招牌,放言除非他死,任何人都别想让回春堂搬家。
由于父亲和许长善是至交好友,高新华还算说得上话。因此,说服许长善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为了这件事,他从年初跑到了年中,从冬天跑到了夏天,但许老爷子的态度仍然没有半点改变。
今天,高新华之所以过来,是因为他听说了许纯良投江未遂的事情。在这个信息社会里,没有什么秘密能守得住。看到许长善后,他立刻收起了笑容:“叔,我今天不是为了公事,就是顺道过来看看您,还有看看小聪。”说完这话,他瞥了一眼许纯良正在埋头吃红烧肉的样子。
许纯良太饿了,根本无暇顾及礼数。许长善不想让孙子听到他们的对话,便起身向外走去。高新华还没来得及坐下,便屁颠屁颠地跟了出去。来到门口,他忙不迭地掏出香烟,恭敬递了过去。
许长善接过香烟,高新华又恭敬地帮他点上。两人默默抽了几口烟后,高新华看着繁华的街道说:“市政规划显示,明年这里将修建地铁。”
许长善猛地吸了一口烟,斜了他一眼道:“有话直说,别跟我拐弯抹角。”
“叔,那我就直说了。修建地铁会影响您的生意。按照规划,至少三五年内肯定不会完工。”
“地铁又不是打回春堂经过的。”
“可是它会影响您的生意啊。一旦开工,门口就会围挡起来。搞不好道路从北路口就封闭了,这样下去,您的生意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折腾吗?”
“高院长,您的话都说完了?”许长善已经不耐烦了,指着门口的马路示意高新华说完就走人。
高新华哈哈地笑着,试图缓解紧张的气氛:“您别急嘛,今天我在手机上刷到许聪了,高考成绩出来了?考得怎么样啊?”
然而,许长善却将半截烟扔到了地上,穿着圆口布鞋的脚狠狠踏了上去。他那不怒自威的眼神让高新华从心底感到一阵哆嗦。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不如你家闺女,水木高材生,让你见笑了。”
“叔,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跟我爸什么关系,我看谁笑话也不敢看您笑话,我今儿来是想帮忙。”
“谢了,用不着!”
尽管遭到拒绝,高新华仍然笑容可掬:“叔,咱们是自己人,我肯定向着您对不?”
“高院长,没看出来。”
“叔,别人不知道您还能不知道,我是个副职,负责后勤,在长兴医院连前五都排不进去。我今儿来啊的确是为了小聪,网上的视频都刷爆了。您先别急,我绝没有看你们家笑话的意思。别说小聪高考失利,就算他考个普通一本,毕业后也很难就业。现在医务界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拿我们长兴医院来说,普通的本科生来求职,人事部门都不带正眼瞧的。硕士毕业想进临床也得关系过硬。”
许长善听出了高新华这番话背后的意思,伸出手。高新华领会了精神,马上抽出一支烟递了过去,再次恭敬帮他点上。他是退伍军人,能从医院保卫科混到现在的位子,靠的就是察言观色的能力。
医院内部给他下了死命令,年内说什么都要把回春堂拆迁的事情解决。他也是想尽了办法,可始终徒劳无功。今天偶然在手机上看到警方解救许聪的视频,高新华霍然开朗:任何人都有短板,许长善也不例外。
从许老爷子抽烟的节奏上,高新华判断出他的情绪已经平复。给老爷子半支烟的时间考虑,然后才开口道:“如果您现在提出让医院解决您孙子的就业问题,我想院方肯定会答应下来。”
许长善抽了口烟,抬头看了看仍然阴云密布的天空:“你还真是不择手段。”
“叔,我可全都是为您考虑啊。这事儿不管您答不答应,一定别对外人说。不然医院得认为我吃里扒外。”
两人目光相遇,同时露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笑容。高新华内心忐忑不安:目前还不知道老爷子的明确态度。医院二期扩建计划迫在眉睫,院长给他下达了死命令,他压力很大。
许长善回头看了看里面,终于下定了决心:“上次的条件不变,再给纯良安排一份正式工作。”
“没问题!”高新华说完又意识到自己答应得太痛快。
“别忙,咱们把话说清楚。我要得是正式工作,正式编制。跟你一样,五险一金一样不能少。”
高新华皱了皱眉头,许老爷子的要价确实不低。五险一金还算好说,但是正式编制?许聪毕竟只是个高中毕业,他怎么能不要个院长当当呢?然而,当他看到回春堂那金字招牌的时候,又看了看不远处那些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病房大楼,高新华很快就权衡出了孰轻孰重。
“许叔,我一定会尽快将您的诉求向院领导反映的。”
许长善摇了摇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和你们合作?我最讨厌的就是机关那种拖沓繁琐的办事风格。现在就决定,你说了不算就得找说了算的人做决定。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答应吧!明天就签合同,我明天就搬过去。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就把回春堂传给我的孙子,你们长兴休想再打这里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