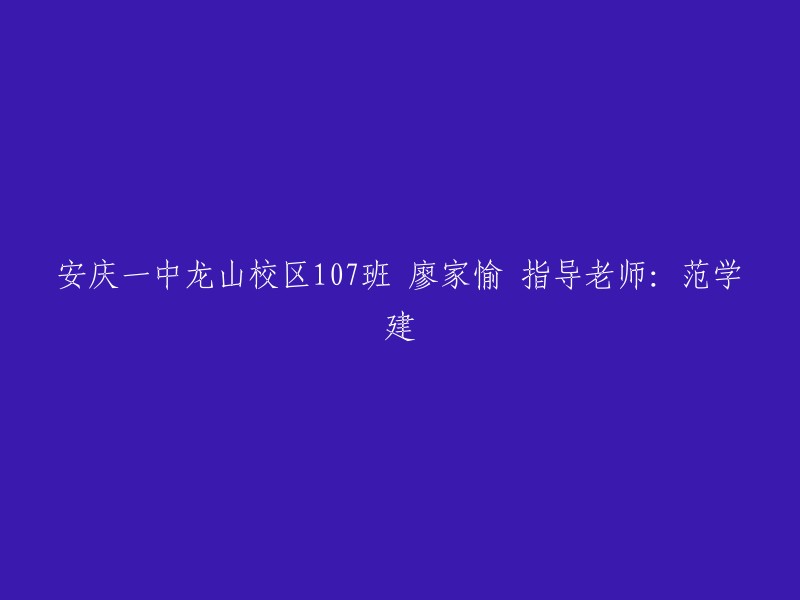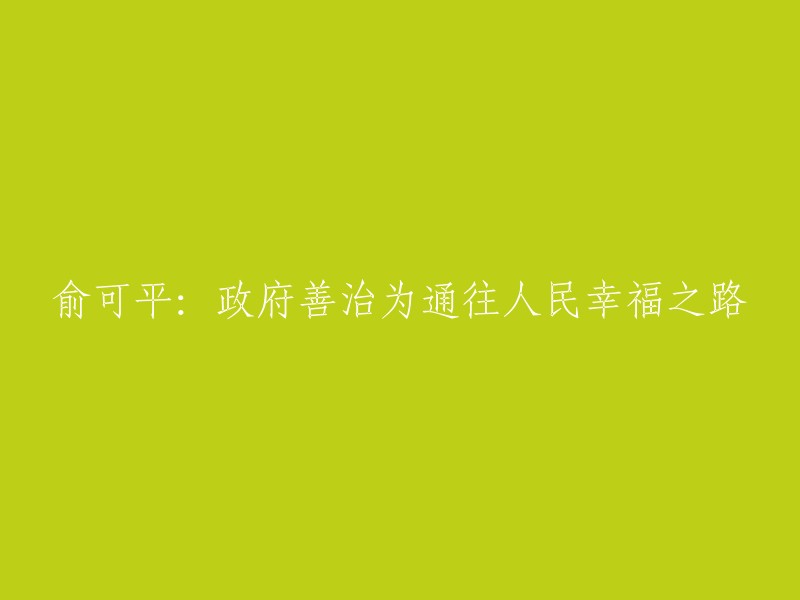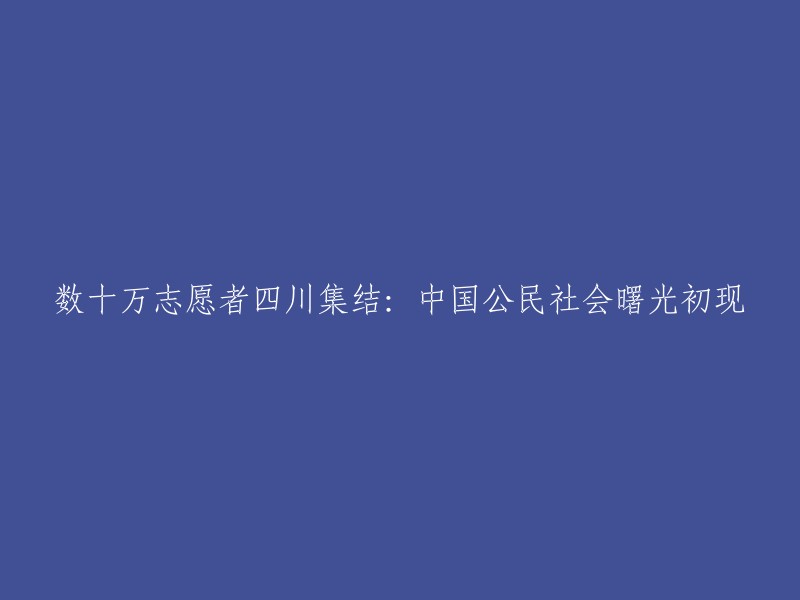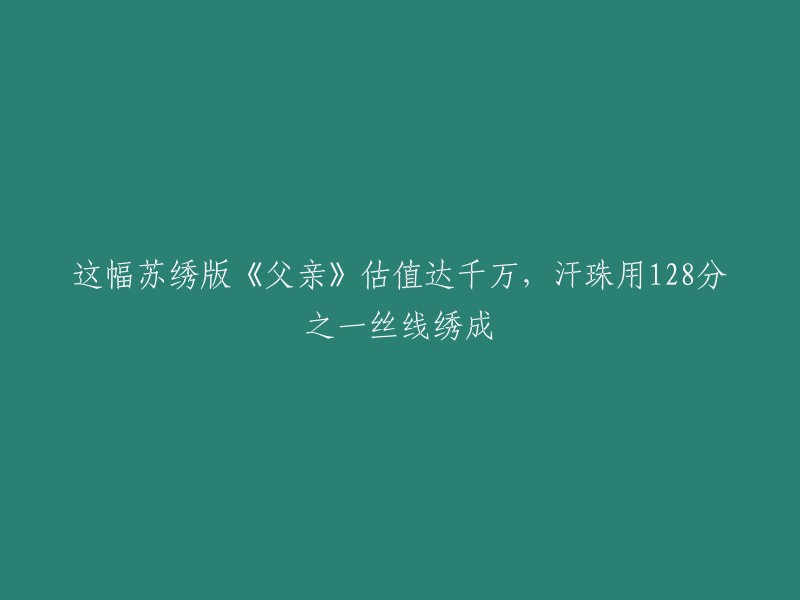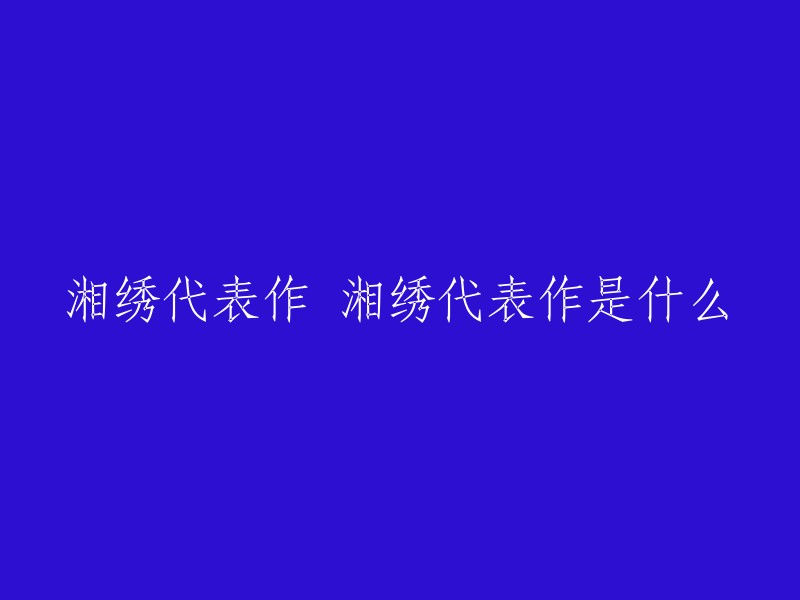【世界教育之窗】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在多个学科的历史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同时也出现在诗歌、影视作品中。英国诗人艾略特在诗作《烧毁的诺顿》中,以当下为背景,对时间与空间、虚与实进行了描绘。美国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回到未来》系列电影则开启了一场时光之旅,探索平行宇宙之间的互动。OECD新近发布的报告——《回到教育的未来:经合组织关于学校教育的四种图景》重新思考了未来与当下的关系,指出“通向未来的道路不仅只一条,而是有很多条”。
关于未来与未知,人类有很多畅想和探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加速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全球大量学校关闭,线上课堂迅速铺开,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决策系统快速进入大众生活。与此同时,种族歧视、民族冲突、网络暴力、关税贸易之争在疫情期间愈演愈烈,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全球团结变得扑朔迷离。
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次未来的预演,把不确定性、脆弱、复杂的系统呈现在世人面前,夹杂着痛苦与希望,不安与努力。各国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不断升级的未来风险上,思考如何在全球蔓延的疫情中支持生活、生产与学习。其中,有关未来素养、教育未来指数的研究即是人类为进入未知社会所做的积极准备。
1.未来已来 素养成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2年出版了《素养的未来与未来的素养:工业化国家的成人素养研讨报告》,指出“发展人的素养技能反映了新的社会条件,应将素养视为人类在不断建构其未来的证据”。构成素养的能力丰富多样,是成人及其社群的语言、文化、伦理、地理和社会背景与情境的统一反映。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评估素养教育的有效性,主要视其能否满足学生及其社群发展的需求。人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其素养的内涵与组成在不断地变化。英文单词“Literacy”在特定时间段被直译作识字或读写能力,“Illiteracy”被译作文盲,反映了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时需要的基本能力是读、写、算;后来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功能性文盲的出现意味着简单的读写能力已不能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随之,素养一词的前缀也不断发展,例如媒介素养、数字素养,都体现了社会进步对人的能力提出新要求。
一、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的WEFFI指数与未来素养
2017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制定了“全球教育未来指数”(Worldwide Educating for Future Index,WEFFI),从政策环境、教学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三个维度综合评价教育面向未来的准备度。WEFFI强调未来教育应该培养“跨学科技能、创造性和分析技能、创业技能、领导技能、数字和技术技能、全球意识和公民教育”六大技能,该指数清晰地呈现了学习者所需的技能,但对技能的讨论并没有超越原先的“教育为未来社会做好准备”的视角,没有包含变革所需的能力,如在变革中或冲击中学习的能力。
与此同时,另一些研究在探讨政府、企业应对未来的准备度时,考虑了变革的环境及其所需的相关能力。例如毕马威(KPMG)2019年的“变革准备度指数”意在为气候变化环境下的国家层面的能力建设提供洞察力,以为未来做好准备。这个指数由企业能力、政府能力、公民社会能力三根支柱构成。每个维度具有若干指标,如企业能力包含了劳动力市场、经济多样化、经济开放度、创新与研发、商业环境等。德勤数字化未来准备度研究(2017)则以企业数字化为背景,从组织、文化、人员和数字环境四个维度阐述变革模型,提炼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公司需具备的能力,如展望未来环境、在失败中不断尝试、孕育积极进取的文化、拥有合适的心智模型等。这两个研究对变革的环境做了具体的描述,由此展开为未来做好能力建设的论述。而这些指向未来能力的数据多来自熟悉的领域,其基本研究方法是根据已有的表现优秀的、适应性强的系统提炼出应对未来之策。
二、不同主体构建的未来素养
由此,不同主体、不同情境下构建出的未来素养不尽相同。那么,未来素养究竟为何物?需要明确以下两点:
首先,未来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目前我们可以从教育、企业、政府等多重视角论述未来之准备度,但是落实到个体素养层面,应是统一协调的。这意味着未来素养应该包括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以及适应未来社会的综合能力。
其次,以某一领域先锋者或当下表现卓越者为依据界定的未来素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未知世界的素养。这就对未来素养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需要摒弃单一视角的局限,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去研究和构建未来素养。
三、历史思维在未来素养研究中的重要性
虽然当下表现卓越者不能全然代表未来努力之方向,但以史为鉴的历史思维在未来素养研究中不可或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修缮的未来”,旨在重访过去,改变未来。对于过往存在的不公正做出区分与确认,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处理对人的身心情感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这种历史思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从而更好地为未来做好准备。
教育长期以来被视为治愈世界诸多问题的良药,然而,传统的国家、私营部门、多边主义机构和公民社会对教育所持的期望却各不相同。国家希望公民掌握读写、计算等符合社会发展的能力;多边主义机构则希望教育在发展人的素养的同时推动人权的发展;公民社会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全球公民终身学习的能力。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其愿景自然就不同。若对这一点未加审视与沟通,未来则可能各行其是,重复既定的路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7/18年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教育问责:履行我们的承诺》中强调,实现教育目标需要互相之间的合作、沟通与信任。“信任的建立需要让不同利益攸关方参与创设共同的目标,并通过相互问责承认各行动者的相互依存关系”。换言之,问责不是简单的结果检查,更非责难政治,而是通过问责确定彼此的责任和相互的依存关系,让权利和义务对等。决策者除了澄清其目标,还要审视其以往的行动理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成立之初就持普适性的人文主义,将教育视为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基础。然而这些年来,专家团体与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活动忙于确认赤字、填补缺口,相对忽视审查其运作的初衷。多边援助之下,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仍在继续,种族暴力亦从未停止。与此同时,一些经典政策的推行也有所简化。例如,联合国推行的“全民教育”理念无论是“教育”还是“全民”二词的内涵均已不同于1990年在泰国宗滴恩会议上取得的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础教育专家罗萨·玛利亚·托雷斯对“全民”的内涵变迁做了总结:首先,全民教育的范畴从所有国家逐渐缩小至发展中国家;其次,全民教育的对象从成人、青少年缩减至儿童;再次,全民教育的责任从国际共同体缩小至政府对其公民的责任。这固然与全民教育取得的阶段性成就有关,也与国际共同体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的定位有关。倘若长久以来,事务运营的心智模式未经检视,由此产生的促进种族融合,为不发达地区提供支持的口号会重复出现,但行动成效却渐微。这一对过往的简化也被视为发展中的“时间政治”。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里指出,“历史思想的独特性乃是历史学家的心灵作为今天的心灵,在领会这个心灵本身是怎样通过过去的精神发展而得以产生的过程的那种方式”。教育若要修缮未来,需具备历史思想,向过去持续地提问,审视历史记忆中的不公与误解,培养倾听、质疑、思辨与对话。
携预期而变革 带未来至当下。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其20世纪70年代的代表作《未来的冲击》中指出,对未来的合理探索不仅可以为现在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借鉴,而且运用适当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远比预测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更为重要。这一想法被同时代及后期的未来研究的各类组织、协会、会议所践行。例如,成立于1973年的世界未来研究联盟(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WFSF)是一个集合了多国、多学科,致力于未来研究的非官方学术型组织。该组织长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合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判未来”提供意见、合作撰写相关领域的前瞻性报告等。
世界未来研究联盟成员吉德利在2017年的《未来通识读本》指出了时间意识的转变,即从预测未来转向“通过我们的思想、感受和行动”塑造可能的未来。这一思想影响了“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s of Education)的价值理念和行动思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9年创设了“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展望知识和学习如何塑造人类和地球的未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于XXXX年X月末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指出:唯一能与不确定性相抗衡的是确定性和承诺。不断变化的复杂环境带来的是不确定性,而大多数行为体的举措则相对可确定。承诺则是指,让知识、教育和学习发挥关键作用,并基于此进行畅想和规划——从“预知的”和“可能的”种种未来当中,探寻并规划出通往人类和地球理想未来的前进之路。
伴随未来研究的兴盛,预期理论与系统成为未来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届“国际预期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ticipation)于2015年在意大利召开。随着这一双年会的推进,当下与未来的关系也更加明确。国际预期会议从“未来影响当下”的视角探索文化、生态、经济、认知、政治、社会结果的预期过程如何影响当下的行动。
未来定位:与预测和先见有所区别
预期对未来的定位有别于“预测”和“先见”。以往大量的数据统计或多或少对未来的组织动力、政治发展、经济需求等做出了预测。例如,经合组织自2008年开始发布《塑造教育的趋势》,对教育的人口结构、全球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政治环境等社会变革进行追踪,对教育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而先见则意味着赋予行动者以洞察力和多重可能性以面对未来。
教育在其中承担的责任是:为未来做好准备。与此相应的是,课程的设计优先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的培养注重聆听未来雇主的需求。例如,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倡导博雅教育,定位未来人才素养时,则以企业高管的认知判断为依据。由此,批判性思维、分析推理,有效的书面、口语交流,自我激励,团队合作,创新等能力成为人才培养的标配。这在可见的工业社会里是行得通的。
但是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人类一部分工作被机器人所取代时,人类又需要“进化”何种素养,才能与机器共舞呢?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工作的未来》指出,目前就学的学生长大后,约有65%的人将从事目前未曾听过,未曾见过的工作。人类如何在一场由“摩尔定律、大自然和市场所引起的飓风”中生存,托马斯·弗里德曼给出了“加速时代”的应对之策:回归信任与合作,终身学习,加速技能,放慢内心等。
预期研究则给出另一类答案。预期视角下的未来不是研究对象,而是一种崭新的时间知觉和心智预期练习;教育不是工具,而是错综复杂的生态世界里的一部分,所以教育的功能不在于逃避、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而在于调动心智模式,将未来视作建设当下的资源,促使行动者更加积极有为、灵活地应对不确定性。
“共同世界研究团队”认可这一预期视角,在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写的题为《学会与世界共生共进:为未来生存的教育》的报告中指出人类与世间万物、全球发展本为一体,教育需在这万物互联的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与世界共生共进”是对西方理性主义、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的挑战,意味着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恰如“庄周梦蝶”。由此生态意识、生态正义较之于人文主义、社会正义更为合适,教学也不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而是处理世界关系时内嵌的方法......若以此为出发点,未来已在改变中。
未来素养的研究越来越依赖预期理论,这一理论重构了时间序列关系,将未来视为影响当前的重要条件。未来素养强调与“使用未来”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熟悉预期的流程和系统,对未来进行假设,以便用于当前的理解和行动。
有关此论述,可以在米勒等人的《转变未来:21世纪的预期》一书中找到。这一思想也影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思考未来教育的视角和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