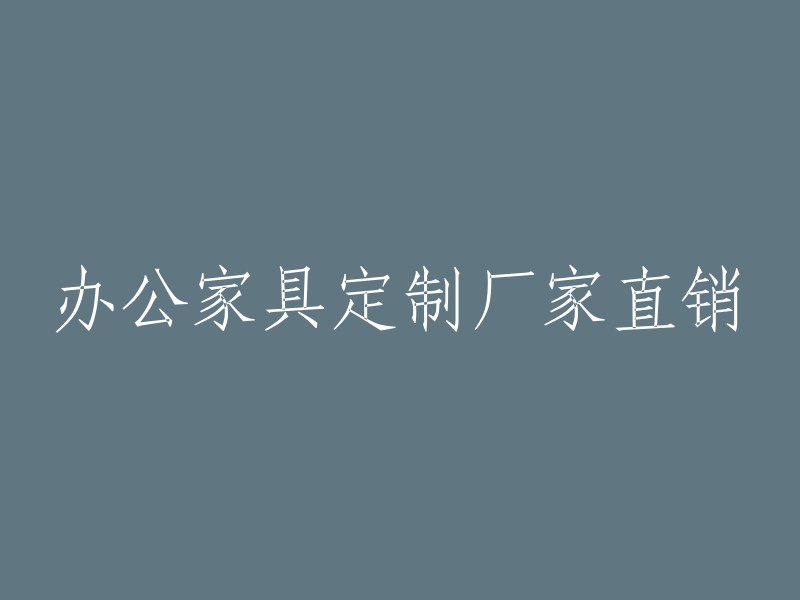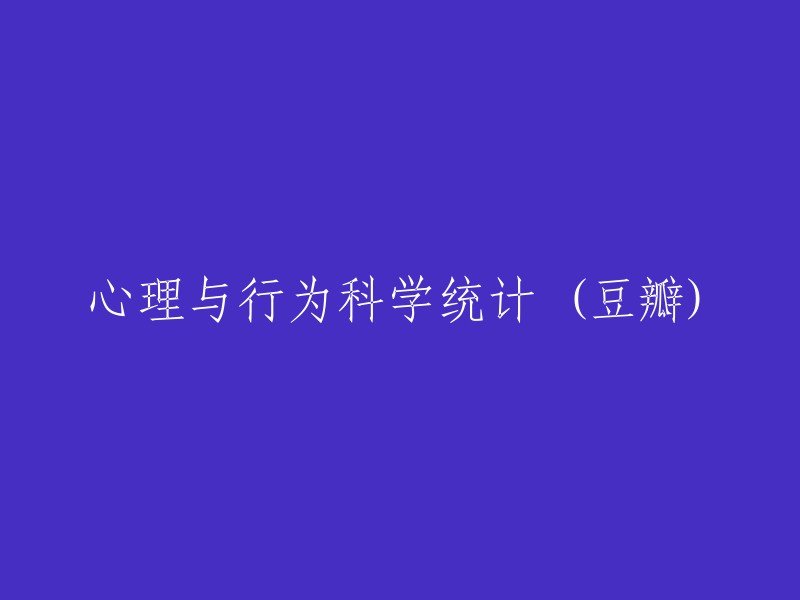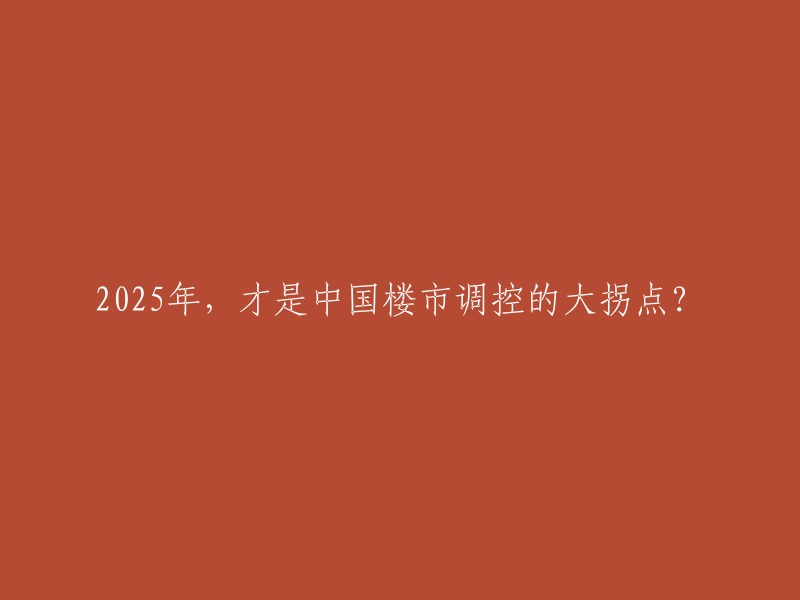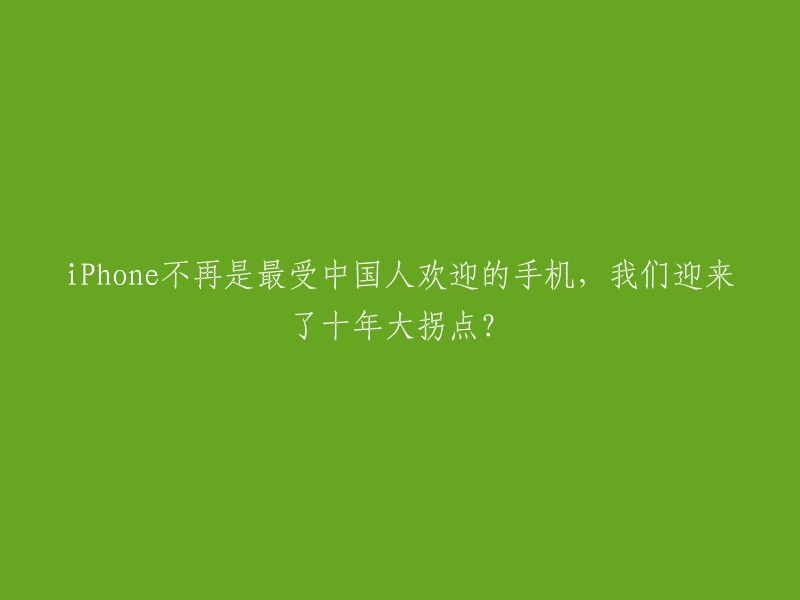谈及藏地,最独特之处无疑是其高原风景、民俗风情和神秘色彩,以及萦绕在藏族人漫长历史变迁和现实境遇中的生存方式、宗教信仰和情感体验。在藏地小说叙事中,如何将文学书写与宗教信仰有效地联系,进而展现出藏地文学独特的话语形式和审美张力,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梅卓是一位从青海高原牧区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书写藏族人和藏地,她的小说创作整体上极富魔幻色彩,既有大开大合的史诗气象,又有细微幽深的情感剖析,笔耕三十余载,逐渐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以魔幻联结藏地宗教与文学书写的叙事方式。正如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封底的出版社推荐语“大草原魂魄激荡,藏民族雄魂史诗”,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的推荐语“史诗与当代交融,神话与现实焊接”,这“交融”与“焊接”的润泽方式,正取决于长篇小说《太阳部落》(1995)、《月亮营地》(2000)、《神授•魔岭记》(2019)、中短篇小说集《麝香之爱》(2007)等在整体上所反映出的史诗性宏大主题1、小说文本的魔幻要素及其中涌现出的美学价值。
一、宏大主题与史诗重构
史诗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歌颂英雄业绩,记录历史事件,传承宗教或神话传说,广泛流传、不断丰富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史诗性通常是一种美学范畴,其“选取历史性的宏伟题材,反映社会整体形象,表现以社会进步力量的意识为代表的民族伦理道德倾向和民族性格,表现时代精神,风格粗糖或混茫的长篇叙事作品;这种作品的思想、艺术特性即史诗性”3。以此来梳理梅卓的小说创作:如果说早期小说《太阳部落》追求一种宏大的部落生命史诗的话,那么《月亮营地》则重在塑造藏地头人家族细微的心灵史诗。《神授•魔岭记》则以双线叙事的结构方式融合了格萨尔神授艺人的成长史诗与格萨尔降服魔域的英雄史诗。梅卓小说的史诗品格是藏民族集体记忆转述与文学表达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史诗品格使得梅卓小说具有极为丰富的主题内涵。梅卓小说细腻的语言和匠心独运的结构之上承载着对藏地深厚历史和现实主题的史诗性重构。
梅卓的小说中,权力与战争的主题体现了藏地生存与生命力法则。在早期小说《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中,梅卓表现了藏地“权力的游戏”。在这些小说中,索白机警而沉着,获得了象征部落权力的太阳石戒指,并买通了省府护卫队队长朵义才,获得了伊扎部落千户的官方授权。为了部落的生存,索白带领伊扎部落与邻近的沃赛部落继续着代代延续的战争。然而,在《神授•魔岭记》里格萨尔王领导的征服魔域的战争中,则是至高形态的战争,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战争。
除了权力和战争主题,梅卓小说中最为成功的主题还包括藏族的爱欲和轮回观念。轮回是一种生命价值观,也是藏族人沟通生死、寄托此生情感的重要方式。在《神授•魔岭记》中,阿旺罗罗唱词中提到了“六佛出”、“六星升”、“六谷同时熟”等词语,都是表达了对轮回观念的信仰。此外,在梅卓早期小说中,她特别迷恋对爱欲场景的细致描绘,饱含深情地描述欲望满足的场景。
《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是梅卓的两部长篇小说,其中《太阳部落》充盈着对爱欲场景的美化笔调,事实上这些爱欲都发生在非伦理意义上的夫妻之间,属于“偷情”。 《月亮营地》仅有的一次爱欲书写便是第三十九章《天作之合》中甲桑与守寡的阿•吉的爱欲。 问题自然没这么简单,正如桑旦卓玛所说:“你不是最初....../但你是最好......”6种种“偷情”都是建立在绝对的真情挚爱之上的爱欲满足,而爱欲满足者无一例外都是情感苦难的承受者,爱欲成了苦痛之后发泄并获得补偿的有效方式。这样的情节设置中,对藏族人炽烈情感经验的人文观照不言自明。毋庸置疑,爱欲书写,尤其是罗桑达吉和桑旦卓玛的爱情纠葛,是《太阳部落》最成功、最富有审美表现的部分。可以说,守住爱欲的情感底线也就是在坚守文学爱欲书写的伦理底线,书写爱欲又避免对爱欲的道德质疑,这便是梅卓爱欲书写成功的关键。
通过家园与抗争主题的背景设置,表现藏族人在时代洪流下生存意志的高扬,是梅卓小说的第三类主题。自清末至民国,马步芳家族在青海、甘肃、宁夏盘踞四十多年,成立割据一方的军阀政府。马家政权民族政策的基本形态是压迫、劫掠甚至屠杀,梅卓小说中的挑动部落之间的纠纷、侵夺部落草场、施行汉化教育等皆是历史事实的文学表现,“四十多年来,经他们制造的这种民族纠纷,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三万多起”,“更加毒辣的是,这个家族借部落之间的草山纠纷,利用政治特权,居然施展狡计,竟将同一地区的一块草山的放牧地界写成同样的执照两份,发给彼此争夺这块草山的两方,促使双方相互械斗,连年不休。黄南同仁加吾和甘甲之间的草山纠纷连续达三十五年之久。......一九四四年...
梅卓小说的史诗品格是藏民族集体记忆转述与文学表达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史诗品格使得梅卓小说具有极为丰富的主题内涵。梅卓的小说细腻的语言和匠心独运的结构之上承载的,是对藏地深厚历史和现实主题的史诗性重构。在这些作品中,梅卓通过对“末法时代”的隐忧和批判,反思人类命运,呼唤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信仰的坚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梅卓小说史诗性重构的主题之间存在着丰富的逻辑关系。在史诗性宏大主题之下,有着“子母题”的表现,几部小说中反复出现英雄“出走-回归”的母题。权力与战争、爱欲与轮回、家园与抗争、自然与信仰等宏大主题组成复杂的网络,它们牵扯出的是藏族人物质层面的生存方式、精神层面的情感结构、历史层面的家园意识以及信仰层面的自然观念。
梅卓的小说《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讲述了20世纪中期藏族部落面对马家军团入侵的命运遭际,以及部族几代人之间的爱恨情缘。这两部小说的魔幻要素并不是主要的叙事方式,而是为叙事提供抒情和渲染的效果。叙事主线是马家政权挑拨部落之间的冲突,部落出现英雄人物带领族人进行联合的抗争之路;叙事副线是情感世界中每个人注定要走入心魔,又都寻求走出心魔的心路历程。
在《月亮营地》中,梅卓用奇幻的笔触描绘了部落成员对自我身份丧失和恢复的过程。当营地中的人们沉浸在自我封闭的狭小世界中,不去理会部落所面临的危险境地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失忆症袭击了月亮营地内内外外的所有人。记忆的丢失便是家园的丢失,是历史与未来坠入荒芜的隐喻,折射出作家对藏地未来深沉的隐忧 。
在小说中,梅卓还使用了魔幻元素来表达对生活片段的表现。例如,在《佳姆萨朵黛》中,画家古古瓦痴迷于修炼魔法:在葱白上写“大银元”三个字,他的女友息尔在舞场大喊自己是巫婆并且成功预测了即刻要发生的地震。这样的情节表现出了对艺术创造的神性想象。
《神授•魔岭记》是一部格萨尔史诗魔幻元素的百科全书,它追求用全景式的魔幻叙事来表现格萨尔史诗的恢宏气象。小说的魔幻元素有三类:自然、物象和人物。自然方面,诸如阿尼玛卿神山、措琼诺日依则湖、药佛泉等自然事物都具有神圣的属性;物象方面,最为重要的有神授艺人的圆光镜、魔王路赞抢夺的九股如意能断神剑、阿旺罗罗的阿达拉姆魔戒、降服魔王路赞的姜嘎贝喝神杖、森伦箭、松耳石奶桶,还有最终象征神授艺人身份的仲夏帽和昭示宇宙未来的金焰魂石;人物方面,如精灵扎拉是阿旺罗罗家族的保护神,活了四百年,“全身是一种半透明的蓝色,披着一条洁白的哈达,后脑勺上皱皱巴巴地飘着几根头发,有两双与身体很不相称的大手和大脚”,它有变化的能力,能够翻阅历书,知道四百年的事情。在以上种种魔幻世界的系统内,叙事的焦点便是阿旺罗罗磨炼心性的过程,他需要修习圆光能力,完成从“他圆光”到“心圆光”的历程,成为集神授艺人和圆光艺人二者合一的格萨尔说唱艺人。
《神授•魔岭记》最终囊括了魔幻现实叙事的所有要素,小说表现的主题恒定,情节可以不断延展,故事围绕着主人公不断展开。人物、情节和环境以及表达的主题都实现了全魔幻形态。魔幻叙事所表现的史诗内容既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信仰体系。
梅卓是一位从青海高原牧区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她的小说创作整体上极富魔幻色彩,既有大开大合的史诗气象,又有细微幽深的情感剖析。梅卓的小说通过对民族历史和族裔文化的追溯、民族品格的揭示和反思,以及对民族文化现实处境的关注,表现出民族自觉意识。她也在此基础上努力提升着藏地文学书写的美学品格。梅卓小说对藏地文学书写的美学提升最为显赫之处在于拓展了小说作为地方史和情感史的价值向度 。
藏族聚居地并不仅限于西藏,卫藏、安多和康巴三大地域跨越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形成了通常所说的“法域卫藏、马域安多、人域康巴”。不同于阿来《尘埃落定》书写康巴土司,梅卓小说所表现的是青海玉树以外区域和包括甘肃甘南州、四川阿坝州在内的安多千户。安多地区的历史正是草马部落的历史。有学者论及梅卓早期小说的薄弱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把民族生存和民族文化的延续问题,集中于一个小部落内部,难以建构宏大的历史感19当然,以部落、家族历史为镜建构民族历史确实有其局限性,即便《神授•魔岭记》事实上依然具有阿旺罗罗家族史的属性。但是,过分强调所谓整体宏大历史感,不免落入以主流文学审视藏民族文学的惯性窠臼。需要辩证地指出的是,部落家族属性本身就是安多地区特有的文化形态,部落家族史的书写,完全可以表现其深厚宏阔的历史,也可勾连历史轮廓,表现个体生命意义、族群生存境遇和宗教信仰等深刻的主题内涵。
梅卓开始写作的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进入汉语写作场域与中国本土文学产生共鸣的年代。藏族人聚居之地本身就是一片充满传奇与魔幻色彩的土地。魔幻与地域文化具有天然的契合优势。扎西达娃、色波等的小说都具有鲜明的魔幻色彩。无论是藏族的本土魔幻资源还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魔幻为小说叙事带来的最大助力之一便是叙事层面的“时空自由”,这又与藏族轮回转世的时空观念不谋而合。魔幻不同于梦境、意识流、幻想和意念等。在文本中,魔幻叙事可以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梦境、虚幻和现实三位一体冲破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隔膜表达超越时空的意涵
《神授•魔岭记》是藏族一级女作家、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卓的长篇小说。作品共十三章、三十九节,约30万字,以《格萨尔史诗》四大战役之首——《魔岭大战》为背景、围绕主人公——少年阿旺罗罗的出身、遭遇、品性和梦想的线索,以少年的视角,推进式叙述其在阿尼玛卿山区不同地点发生的故事,最终完成事件描写和性格塑造。
小说作为情感史的悲剧意识和宗教救赎。小说接续格萨尔传说的藏文化传统,以小说化和个性化的审美方式,重构《格萨尔史诗》四大降魔篇中“魔岭大战”的原叙事为背景,围绕主人公——“东查仓部落”13岁少年阿旺罗罗成长为格萨尔神授艺人的神奇生命轨迹,多角度展现了当代格萨尔史诗传播的生态空间和民俗基础。
整体来看,梅卓的小说具有“向内的”价值依傍,对马家政权的批判、对藏族文化的隐忧以及对自然生态的呼唤都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当我们深入文本细部之后,会发现其小说文本自身散发出的审美魅力远超出这些价值诉求。梅卓借助宏大命题表现细腻情感的叙事特质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例如,《神授•魔岭记》虽然不及格萨尔史诗本身的宏大、磅礴,但却展现了女性文学细腻敏锐的独特情感魅力和新时代女性叙事的别样气质和瑰丽丰赡。这样的评判不仅适用于《神授•魔岭记》,而且在笔者看来,藏族人情感史的延展是梅卓所有小说最重要的一条美学脉络。
梅卓所坚守和突破的并非惯常意义的宏大历史叙事,而是在探索藏地小说书写的美学品质提升,书写藏族人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独特情感史。当小说所反映的情感具有民族地域属性的真切,能够产生独特的审美意蕴时,这样的小说便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藏族情感史诗性小说。
梅卓小说的情感史诗性审美品格集中表现在情感悲剧的塑造上。悲剧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其特质在于能够集中表现叙述主体的情感结构,极大地引发人的情感共鸣。早有论者注意到:“梅卓的《太阳部落》在青海两个相邻部落争夺草场相互厮杀的历史背景下,着力描绘了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这是我国藏族安多地区近现代史上屡屡发生的故事,也是一个被作家多次重复的创作题材。23《太阳部落》中最为精彩的悲剧情节是阿莽和香萨的爱情悲剧。香萨比阿莽大四岁,幼年香萨的一记耳光打醒了阿莽的爱欲本能。因为家族恩怨,香萨没有同意阿莽的求亲,阿莽绝望了,骑着爱马小雪狮坠崖而亡。香萨因为愧疚而噩梦连连,在发现母亲桑丹卓玛和洛桑达吉的婚外情后出走,寻找自己唯一能够信赖的阿爸嘉措。父亲和阿莽,香萨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最终都如风般不见踪迹。香萨决定出家,去玛冬玛山洞静修,静修前砍下一截小指,包在头发里,埋在了阿莽的坟头。山洞中一个人身蛇尾的修行者出现,“香萨匍匐过去,去吻那人的裸着的脚......”24香萨和修行者最终生下了女婴安,阿莽的父亲阿•格旺发现了安,安的“左手的小指边,奇怪地多长了一根小指”25。马丽华认为:“这是一部令世俗震撼的作品。她把那一时代的草原女性的心灵之凄美,在现代心灵的观照下,无以复加地推向极致。”26这段爱情悲剧融合了梅卓小说所有的艺术元素,契合梅卓最为擅长的情感表现领域,达到了趋近完美的审美品格。心理缺陷、爱欲本能、家族恩怨、生死相隔、异形人物、宗教救赎、轮回转世......一个个情节次第生发、此起彼伏。阿莽死后,香萨的迷狂、无意识、心灵感应以及自我救赎等并非情节层面的“硬魔幻”,而是宗教层面的“软魔幻”,这样的魔幻叙述真正实现了对宗教救赎审美品质的有效提升,可以说形成了藏族文学爱情悲剧叙事的一种范本。
在后来的小说《月亮营地》里,章代-乔和甲桑“弑妹”之后的灵魂救赎延续了情感悲剧的审美基调,形成了审美意义上的宗教魔幻。宗教魔幻能够“为生者开天门,为亡者断死门”27。《太阳部落》书写过程中生成的女性悲剧叙事资源成为之后梅卓小说情感表现的重要方式。
梅卓是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中的佼佼者,她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等或聚焦于安多地区百年来的部落苦难历史,或以格萨尔史诗的传奇与藏民的现实相交融,构筑亦真亦幻的神话叙事,藏族特色鲜明,叙事曲折,艺术韵味浓厚。
梅卓的小说《佛子》讲述了一个心灵苦修故事,藏族少年才让从对佛法的猜疑,到与阿依奶奶通过转湖亲见白文殊显灵的圣迹,最终成为神授的佛教徒。小说结尾,当大喇嘛再次大兴土木之时,才让出走外乡,办了一所学校。小说中僧人才让最后的出走办学属于梅卓小说中溢出文本的异质性情节。这昭示出藏族文学叙事更值得深思的层面:在情感结构的深层逻辑背后,是隐含在历史、文化、宗教复杂关系网络中的集体无意识,类似马家政权、现代化进程等外部因素所触及和引发的可能是藏族宗教文化内核本身的悖论性因子。以小说叙事触碰这个内核,或者说重塑藏族的文化之魂,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