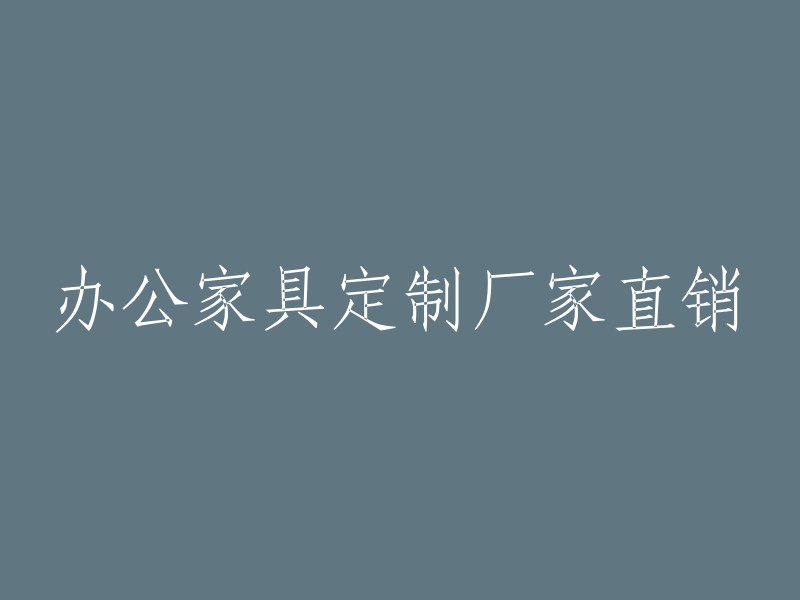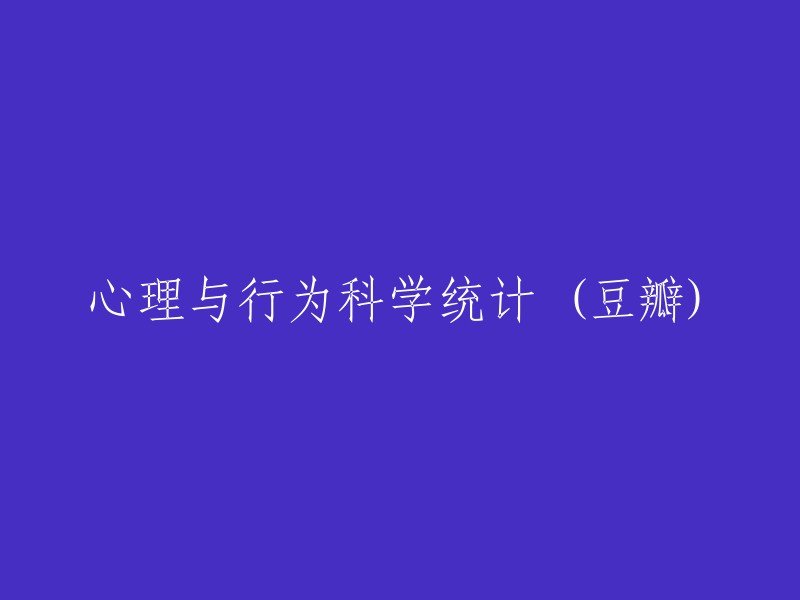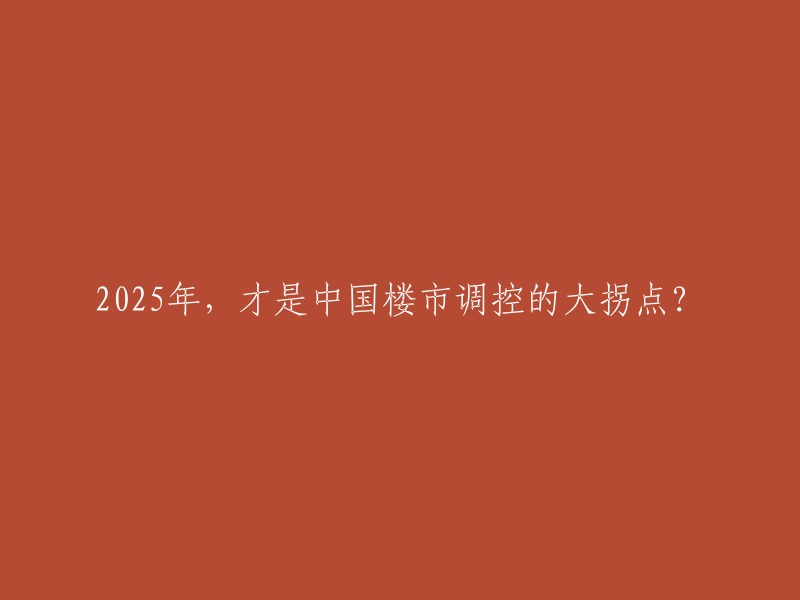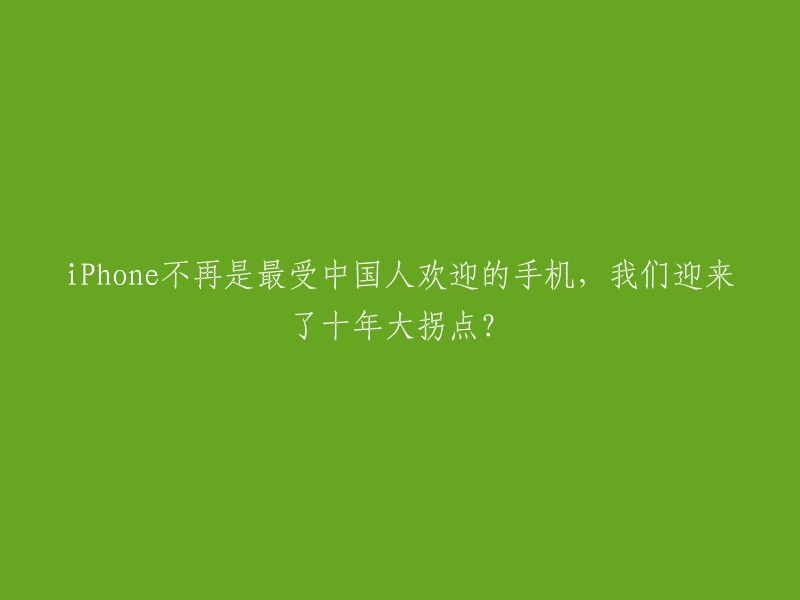以下是重构后的内容:
“你是我的人类法庭”
1913年8月,卡夫卡当时的女朋友菲利斯在度假时结识了一位能通过笔迹看出人性格的占卜者。他对卡夫卡的判断是:行事果决,极其感性,善良,节俭,对艺术有兴趣。然而,卡夫卡对此断然否定:“全都不对,连他说我对文学感兴趣也不对,甚至是最大的错误,我对文学没兴趣,我就是文学,除了文学我什么都不是。”
他讲了一个刚刚读到的故事:一名牧师嗓音美如天籁,听者无不神往。某日,一位神父听到后说:“这不是人的声音,而是魔鬼的。”于是他当众驱魔。魔鬼离开时,尸体瘫倒在地发出阵阵恶臭。是魔鬼而非灵魂让这具肉身活着。卡夫卡对不理解文学甚至希望他放弃文学的菲利斯说:“我与文学的关系与此相似,只是我的文学没那么美。”
四年后的一天,已和菲利斯订婚、分手又第二次订婚的卡夫卡夜里突然咯血不止。确诊肺结核后,卡夫卡再次写信给她剖析自己:“你知道吗?在我内心有两个我一直在斗争很激烈:一个好的那个属于你......你是我的人类法庭。在我之中斗争的那两个中较好的一个属于你......尽管节节败退,我最后还是相信最不可能的事情终究会到来(最可能的是永恒的斗争),而这些年来变得凄惨、卑劣的我终于可以拥有你了。”(1917.9.30)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挣扎和矛盾。他在追求文学的同时也在逃避现实生活中的责任和义务。他试图找到某种平衡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愿望被他写在同时期的一则笔记中(编者注:卡夫卡保存下来的文稿中,有8本8开本笔记)。
您好!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卡夫卡的小说《堂吉诃德》并不是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阐释或续写,而是非凡的创作。其中最突出之处就是“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关系的大逆转”。如果像卡夫卡所说,堂吉诃德是由桑丘·潘沙创造的,那么,桑丘·潘沙则真正属于卡夫卡的独创。
在这一年圣诞节,卡夫卡第二次解除了与菲利斯的婚约。
根据盲诗人荷马的记载,塞壬是一群坐在海上绿茵间的女性,周围环绕着腐尸、骨骸和风干的人皮。她们以优美而嘹亮的歌声迷惑过往的行人,使他们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为了抵御塞壬的诱惑,奥德修斯听从了仙女基尔克的建议,让同伴在耳朵里塞了蜡,并命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他告诉同伴,如果他请求解绑,就把他绑得更紧。这样一来,奥德修斯既能听到塞壬的歌声,又能够安然度过危险。
然而,在卡夫卡的叙事中,仙女基尔克消失了,她提供的方法成了“自古以来谁都会”的把戏。卡夫卡认为,“全世界都知道,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塞壬的歌声能够穿透一切”,那一小块可笑的蜡根本不在话下。更何况,即使有人逃过塞壬的歌声,也逃不过她们的沉默,沉默是“一种比歌声更可怕的武器”。奥德修斯也不再是荷马史诗中群雄簇拥的大英雄,他孤零零地上路,在自己的耳朵里塞了蜡,让人把他绑在桅杆上,毫不怀疑这“拙劣甚至是幼稚的伎俩”,怀着某种天真的喜悦,向塞壬驶去。
令人惊讶的是,奥德修斯竟然成功脱险。这是命运女神的安排,这个结果谁也改变不了。卡夫卡通过揭示真相来说明,奥德修斯之所以能平安脱险,是因为塞壬根本没有唱歌。实际上,奥德修斯只是看到了塞壬“脖子的转动、深深的呼吸、满含泪花的眼睛、半启着的嘴”,以为她们正在唱咏叹调,以为歌声正在身旁回荡。他并没有听到塞壬的沉默。故事讲到这里,已具备卡夫卡的黑色幽默。自我感觉良好的奥德修斯,希望穿越腥风血雨、打妖降魔,却只是沾沾自喜地上演了一场毫无惊险的荒唐。被琐碎、庸碌、无聊消解的英雄气概,让奥德修斯成了海上的堂·吉诃德,同样满腔抱负,同样自欺欺人。
奥德修斯真的没有“听到”塞壬的沉默吗?他那么老奸巨猾,怎会一无所知?卡夫卡说,也许他已经发现了真相:“只不过将上述虚假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幌子,在塞壬和诸神面前演示一遍而已”。关键在于,比歌声更可怕的塞壬的沉默,为何在奥德修斯身上失效了?
其实,不论歌声还是寂静,都只是没有暴力的诱饵罢了。真正让人纵身跳入大海的,不是诱惑本身,而是受诱惑的人自己的“激情”,它足以“崩碎一切链条和桅杆”。也就是说,奥德修斯安全逃命的真正原因是,面对塞壬的沉默,他不为所动。也许是他心里充满“天真的喜悦”,再容不下任何波澜,哪怕塞壬“伸展、转动的身体,飘扬在风中的头发”,让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奥德修斯望着远方,“恰恰在他离塞壬最近的时候,看不见了她们”。或许,单凭内心的坚定,奥德修斯就能平安通关。塞壬、诸神、荷马和两千多年来的读者,都上了奥德修斯的当,我们只是看到他愿意让我们看到的表现,但永远都不能了知他的内心。
这个版本的奥德修斯,像极了打发走魔鬼的桑丘,他故意要人看到一个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他,一个努力拒绝诱惑、被求生欲支配的他。可那块什么都屏蔽不了的蜡说出他真正的欲望:他想要听到歌声,他希望受到诱惑。可惜,塞壬没有唱歌,沉默对他也没有力量——沉默的凶狠在于,它会让人萌生出“那种以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塞壬的感觉,那种由此而产生的忘乎一切的自豪自傲,人间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对抗”。见多识广的奥德修斯,早已超越了建功立业、流芳百世的虚荣,他不想战胜谁,只愿在蜡和铁链的虚掩下,安安静静、不被打扰地听一听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哪怕因此丧命也在所不惜。
也许,一辈子都在奔波流浪的奥德修斯累了,充斥着计谋、嫉妒、欺侮、名利的伊萨卡已是他乡,能够打动心灵的歌声才是他最理想、最温柔的家园,他想要投入歌声的怀抱,又不能拒绝诸神的好意,不忍无所顾忌地打破世人对他的期待。粗糙、幼稚的自救手段,并非他愚蠢的证明,而是他装傻的道具,或者说,是他内心坚定的符号——献身歌声的坚定。
卡夫卡并非桑丘,无法一了百了地推开堂·吉诃德,若无其事地回到菲利斯身边去做好的卡夫卡。他是奥德修斯,孤零零地在路上,用脆弱、荒谬、人人如此的方式假模假样地附和着让他疲惫的现实,内心早已被文学填满。语言是他永远的诱惑,是他真正的使命和追求。然而,事与愿违,塞壬没有唱歌,听闻寂静的奥德修斯淡然远去,只能继续漂泊在返回伊萨卡的海上。如果这的确是卡夫卡为自己写的寓言,我们不妨继续追问,塞壬为何沉默?
卡夫卡提供了两个解释。也许是因为,奥德修斯这个对手太强大,她们自认为歌声威力不够,只能试图用更可怕的沉默勾起他的欲望和激情。也许是因为,看到奥德修斯那一刻,本该去诱惑猎物的塞壬惊呆了,全都忘了唱歌,不想再诱惑,宁愿“尽可能多看看他那双大眼睛里的余光”。卡夫卡说:“如果那时候塞壬有自己的意识,也许会毁了自己。她们仍然活下来,只是奥德修斯从她们手中逃脱了。”
卡夫卡长篇小说《城堡》手稿
按照荷马的记述,塞壬“知悉丰饶大地上的一切事端”。那么,惊呆失语,就一定是因为她们在奥德修斯那里看到了她们不知道、唱不出甚至迷住了她们的东西。她们看到了什么?是“奥德修斯陶醉的脸色”,是他“望着远方的目光”。他那不依赖外物而自足自在的放松、喜悦、坚定,不属于“大地”,而是纯粹的精神极乐。面对“连命运女神也无法进入的内心”,语言失效了。任何对内心的描述,都只是在描述它的某种外在的投射,而那不是内心本身,能够被言说的内心,已经翻转到外部。内心,只能体验,无法描述。倘若语言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意识到那些自己无法言说、无法解释的东西的存在,这种羞耻感,就会让它毁掉自己。万幸或不幸的是,语言不自知,它没有“意识”,只能看着自己无法捕获的东西脱身远去。
审视那“不可解释的”
这本笔记里的第3个故事,是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传说(1918.1.16):普罗米修斯受到惩罚,诸神派鹰啄食他不断长出的肝。疼痛把普罗米修斯挤压入岩石,他最终与岩石合一。几千年后,他的背叛被遗忘了。再后来,人们厌倦了这件没完没了的事。故事最后这样结束:“剩下的只有那无法解释的岩石——传说试图解释这不可解释的。可是由于传说来自一个真实的基础,所以它也必然在不可解释之中结束。”
这个令人费解的收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普罗米修斯身上引开,审视那“不可解释的”。首先,传说不能讲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连同他的罪和罚,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整个故事已经被遗忘、被厌倦。
遗忘和厌倦可以讲,但遗忘和厌倦的对象无法讲——讲述遗忘的对象,就意味着没有遗忘,讲述厌倦的对象,就意味着尚未厌倦。那么,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传说只能讲一块岩石?岩石本身无需解释,它存在着,就是真相。需要解释的,是它提供的时空,它抓住了一段抓不住的过往,罪、折磨、遗忘、厌倦,全都消失在它里面,却又全都留在它里面。消失的,如何存留?存留的,消失了吗?岩石像一个符号,表征着普罗米修斯,却不是普罗米修斯。
遗忘、厌倦、表征,均终结于某种空无,均以对象的缺席换来自己的意义。传说又何尝不是?传说想要言说真相,可如果真相在场,又何必传说?传说的真正主角,不是普罗米修斯,而是这种“不可解释”,普罗米修斯可以被随意替代,真相的阙如却始终不变。又何止传说?终有死亡的人,谁能逃过时间?时间规定了遗忘,遗忘规定了空无。言说一旦启动,就只能围着这空无打转,语言啮噬着有和无的界限,却只能终止在空无开始的地方,而那里,藏着某个被遗忘的、等待着解释却永远无解的真相。
但这不能归咎于语言或文学的无能,这是我们的原罪。“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也由于我们还没吃生命树的果子。”精神和肉体之间不可通约的张力,永恒和时间之间无法缩短的距离,是人的本质,本质无善恶。但对这种“处于特定的过渡状态的意识”,让肉体和时间显现为恶,让精神和永恒显现为善。善中无恶,沾染了恶的善,已不是纯善。但恶包含了善,没有善,一切恶都无所谓恶。“恶认识善,可是善不识恶。”卡夫卡的这个公式,可以套用给很多形而上的对立,比如“时间认识永恒,可永恒不识时间”,“肉体认识精神,但精神不识肉体”。因此,人类对善、永恒、精神的一切言说,都是谎言,比较可取的是,“在尘世中生活,但不追求善/永恒/精神”。
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 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
卡夫卡曾经说过:“延续,献身于生活,表面上看似乎无忧无虑地一天天过日子,这才是冒风险的勇敢行为。” 他在生活中感受到虚无,正因如此,大概人人都需要某种不可抵达,以赋予自己意义,不论在他人看来有多么荒诞,这至少是一种懂得忍耐的英雄主义。
很抱歉,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你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你的问题?或者你可以告诉我你想了解什么方面的内容?我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