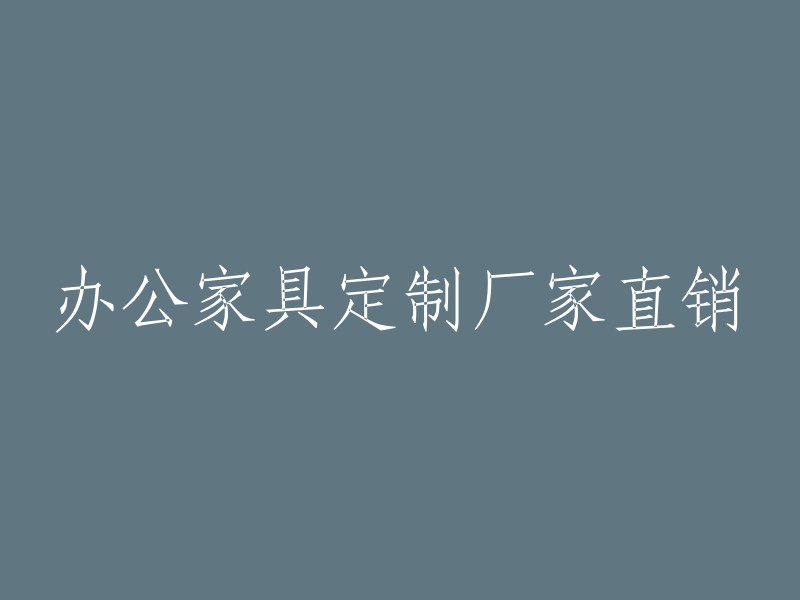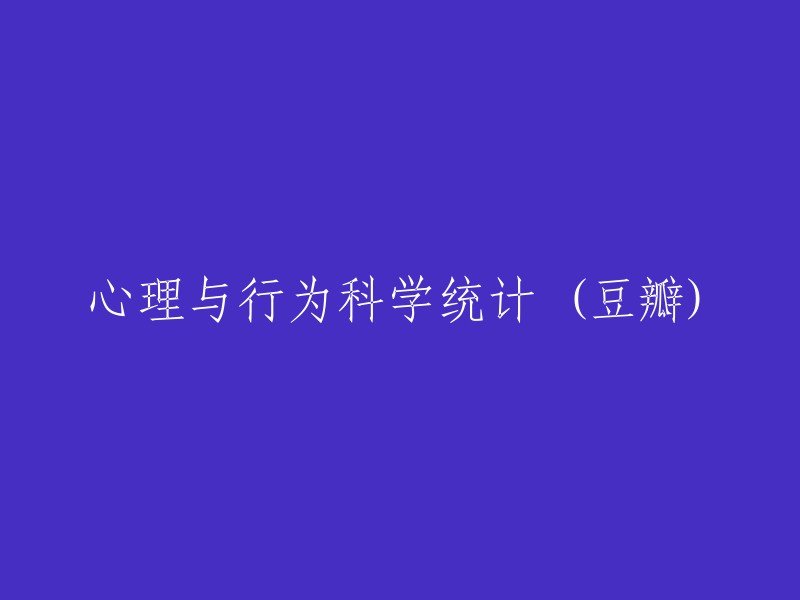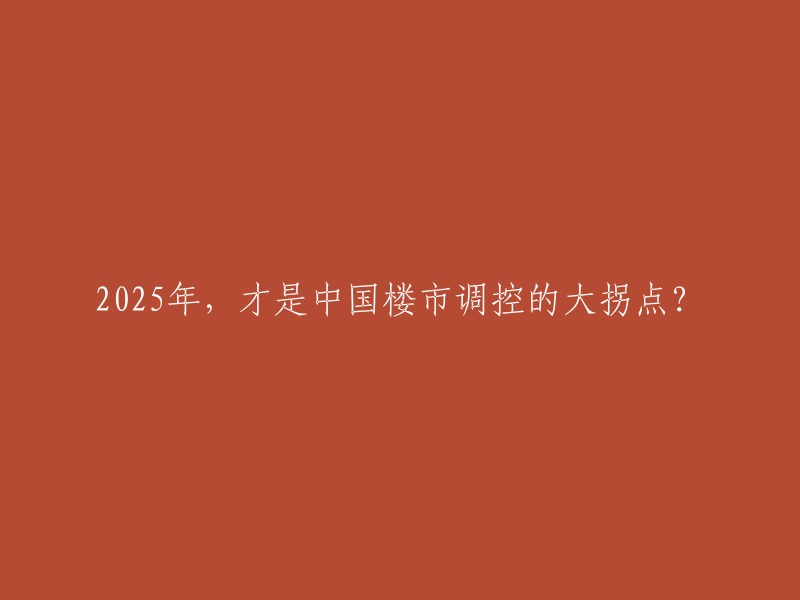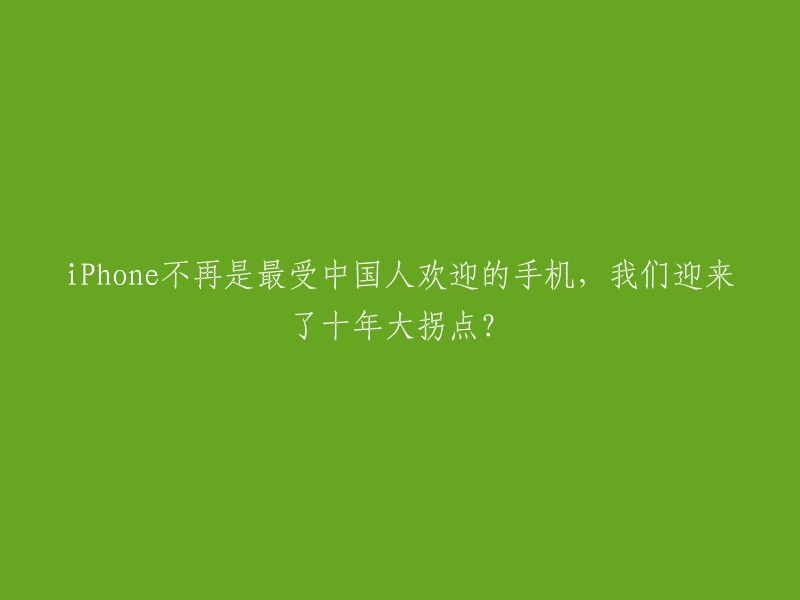山门内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当年两廊漫长的厢房庄严而恢弘。然而现在东边已经倒塌,只剩下断壁残垣,用支棚子、堆柴草和搭架子来烧开水。尽管庄严已经消逝,香火依然缭绕,气数仿佛未尽。
剩下的孤独西厢房,一溜分不清间数。虽然门窗紧闭,但房架仍然高耸挺拔。只是这边那边或钉上板条或糊纸,或者挂起枕巾花布,好像浑身打了补丁。道姑斋娘们都不叫它做房间,而是按照本地方言称之为“窠巢”,倒也别有风味。
正殿经过维修,油漆粉刷得光鲜亮丽。绣伞黄幡、铜罄木鱼都显得庄重肃穆。地上三行蒲团蓬松柔软,仿佛在发酵一般。图样、针黹、配色都散发着女人的居心和信徒的虔诚。
其实道观里出家人只有师徒两个,师父是老道婆也是观主。前两年已经山门不迈,这两年连殿门也懒得出了。只在殿里敲木鱼,带领斋娘们做功课,在蒲团上发酵。世界上养生之道分两路。一路尚动,最响亮的格言是“生命在于运动”。一路习静,或盘腿或面壁,或坐关或辟谷......
徒弟小道姑出身于道土世家。道士如同佛门居士,是不出家的教徒。其中也有世代吃教饭的,填表格应填宗教职业。比如道场上的乐队,本地土话叫吹班。再如卖膏药草药也画符的郎中,叫巫医不好听,叫神医不够格。
小道姑一出世,父母就上道观烧香、点蜡烛、写黄纸名字,刚会走路就在正殿高门槛上滚进滚出,磕头拜老道婆做师娘。老道婆双手摩挲着小脑袋,笑眯眯地说了句丧气话:“冤生孽结。”
做父母的听了好开心,原来这句话挂在老百姓嘴边,可以微笑说出来,也可以是诅咒,也可以惊呼着表表快意。这是语言中的百草膏万金油。
小道姑十几岁进观准备接班是自然而然的事。走路还带跳,讲话自会笑,笑不笑的脸上飞红,满院子只有这一张桃花脸。
再说进进出出的斋娘们,那是不出家的老人半老人,住在观里念经、修行、吃素、养老。多半自家有儿有孙有吃有穿,是把这里当作躲清净的地方了。不论是谁,全都来去自便,多时住十好几个,少也八九不离十。
斋娘们做完早课,边走边脱道袍,从正殿西角一步跨进西厢房。进房先是小小起坐间——忽然,任谁也吃惊,魔术似的,刷啦,眼前出现层层洞窟。原来间间“窠巢”都从中间打开,两边铺床。铺铺相对搭竹竿,挂道袍、晾毛巾,经卷符篆、土黄袋子、明黄帖子,仿佛一个套一个又仙又俗的月洞门。
月洞门,月洞门,洞洞飘渺,门门神秘。随着众斋娘和跟进小道姑的脚步声响起。有拎桶的,有提壶的,全都嗤嗤冒热气,今天是“搞卫生”的日子。
蓝斋娘端着四样供果走进起坐间的八仙桌旁,合十跪在蒲团上,闭目低头。托盘里的粽红麻花、白面馒头、黑白麻团和花边素饺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小道姑疑惑地问:“今天是什么日子?”蓝裔娘缓缓睁开眼睛,凝视着小道姑,仿佛在望远山。随后,她微笑着回答:“冤生孽结。”
当时,小道姑还未得道,对“冤生”和“孽结”的含义一无所知。她回忆起蓝斋娘年轻时的情景:春天,她挎着青竹篮子,拿着月牙镰刀,随意漫步在草地上,如同画龙般挥舞着镰刀。她的牛尾巴晒太阳,牛角淋着毛毛雨。刘海上挂着串水珠,身上洒满阳光。人心口头上有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会有小鹿跑出来,跑到天边。这就是人心。
油菜花盛开的田野上,金黄与嫩绿交织,无尽的黄色延伸到天边。空气中弥漫着嗡嗡声和泥土的簌簌声,春天从大地深处的心脏开始涌现。嗡嗡声和簌簌声构成了天籁之音。一个牛倌骑在牛背上唱着“去不回”,歌声高亢激昂,童言无忌。这首歌曲无法重复,也无法重演。它可以表达人心,也可以唤起天籁。当看到小姑娘在草地上画龙时,牛倌会忍不住咽下口水。
小道姑听到远处传来的笑声,原来是月洞门里哗啦哗啦的水波荡漾起来。斋娘们正在水波中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传入耳中。她们变成了水妖,尽情享受这份快乐。小道姑回头看向蓝斋娘,却发现她已经认不出来了。原来蓝斋娘一直合十跪在地上,不知何时何刻,她突然扬起脸庞,脸上泛起了两颧桃红的红晕!
蓝蓝姑娘被定亲后,长大成人,大家用花轿将她抬走。吹奏唢呐,敲锣打鼓,放鞭炮。牛倌则躲进小店里喝闷酒。突然间,他的心口头空空如也,一只小鹿奔跑而出。牛倌忍不住跟着小鹿跑出了村庄,唱起了“去不回”。这首歌如同天籁之音,传遍大地。人们想念着“去不回”,称牛倌为牛背上的梅兰芳。
青春如同“去不回”的小鸟一般,一去不复返。大地干旱自旱,涝自涝。一年之后,大旱过后下了一场透雨,老百姓终于松了口气。他们纷纷准备道场,举行焰口仪式,恭请方圆闻名的演义法师光临。
道场上人头攒动,家家户户点蜡烛、插香、上供。供品包括米、麦、丝、麻、酱、醋、茶等,摆满了整整一张八仙桌。正中间摆放着一张八仙桌,上面放着一把太师椅。三更半夜时分,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丝竹悠扬,锣鼓齐鸣。
演义法师身披白领青袍,外罩宝蓝斗篷,前胸绣着金丝太极图案,后背则是银色八卦纹饰。他登上八仙桌,坐在太师椅上。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双目流转间透露出无尽的神通。
蓝蓝新媳妇眼尖,法师道头上那压臀的玉环,竟和自己压腕的玉镯仿佛。啊,这玉镯,原是牛背上的梅兰芳,唱着“去不回”,从天尽头拾回来的......法师诵经如唱,嗓音清澈如水。蓝蓝新媳妇失声叫道:“梅兰芳!道场上的梅兰芳!”
蓝蓝的老公叫道:“怎么又一个梅兰芳。”
蓝蓝赌气:“两个是一个。”
老公气堵:“一个是两个。”
一个两个,两个一个,从此在两口子中间,做下了争争吵吵。不论什么零东碎西,都是你左我右。好比扫地,这个朝里扫,那个就要朝外。各扫各的也没事,偏偏还要说嘴。这个说朝里聚宝纳财,那个说朝外清除垃圾。说说本不过打湿嘴皮,谁知内里有火,虚火闹心,动手开打。人众看不下去,请出老人来压阵,偏偏老人是儒释道三教不分的,不耐烦朝里朝外,当头来句儒家的“以和为贵”。“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接着是佛家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跟着来道家书空画符,大喝:“呸,噪!冤生孽结!”老公吃惊失手,老婆手镯落地,跌作两段。——气非凡,投奔道观,从此拿捏起斋娘身份。
此刻月洞门里水里雾里,一支支胳臂白生生,小腿光溜溜,众斋娘全是水妖,全都滚圆、幼嫩,爱娇,笑声散花散落,无不肉弹。蓝斋娘跪在蒲团上着实发酵了,两眼潮红,两颊飞桃,双手托盘,朝月洞门里走。
托盘上四样供果全部生动了:麻花蹦筋。馒头鼓胀。麻团渗油。素饺流汤。小道姑奠名其妙,却也不同俗人,能够说出妙语:冤生孽结。扭头走到院子里,哦哈,透了口气。那孤独的西厢房,清高架子,浑身补丁。只是破烂窠巢,没有半点魔力。
靠山门有棵枣树,剩下一个枣子叫小道姑看见了,退后两步,掖道袍,助跑,起跳,伸手,欢叫,散落一脸枣花。
不门
——去不回门之二
小道姑木鱼笃笃,老道婆铜罄昂昂。众斋娘随声随和,断句断落,太平经“自有自有”:自天有地,自日有月,自阴有阳,自春有秋,自夏有冬,自昼有夜,自左有右,自表有里,自白有黑,自明有冥,自刚有柔,自男有女,自前有后,自上有下,自君有臣,自甲有乙,自子有丑,自五有六,自水有草,自牝有牡,自雄有雌,自山有阜。此道之根柄也,阴阳之枢机,神灵之不变万变、万变不变也。
经音未落地,众斋娘已起身,边脱道袍边外走。今天是什么日子?一个个竟不回西厢房,由着脚头走过院子,直奔山门。嘴上也不说什么,好像脑子空白,单凭性子行动......小道姑连忙喝道:
冤生孽结,人众听着。莫小山门,莫要嘴多。菠斋娘和老公一跌两段,一家两起,老公千世也不来一趟,今天光临道门,万变不离一个变字。蓝斋娘,咦,蓝斋娘呢?蓝斋娘......”
山门外边,遍地绿苔。约二十步远,横一条沟。沟旁荆棘丛生,杂花烂漫,掩盖着叮叮水声,流过山门粉墙。到西角落那里,平铺青石小桥,桥上堆砌凉亭如轿,苔藓斑驳如青铜浇铸,好一幅古刹外景。轿亭上,凿有隶书对联。上联是“大道生生生万物”,下联曰“真人法法法不变”。眉批奇古认不得,据说是符篆道书,也叫做天书的一个变字。
沟外闪现平板三轮。那是当年新兴的交通工具,可坐人赶场,可载货上市,蹬三轮也是时式行当。此刻猴在车上的,竟是蓝斋娘,半脱半掖袍袖,暴露两条肉棒槌。因细嫩有比做藕的,也有形容做水晶糕,那是白净的意思了。也有叫声“肉弹”,弹不定是炮弹,多半指的弹跳之弹,因此可以写做“肉蹈”,只要生动活跃就是了。
蓝斋娘一拧车把,踩住前轮,道地巾帼打手的刹车模样。跳下车来,放下袍袖,拉平苫布,理顺麻绳,明显换了个人,是一位中年妇道人家了。人众心想:是不是故意放慢拍子,存心做出样子,特地摆个架子。人众暗地捏一把汗,莫非有得好戏看了?蓝斋娘只管从车上带下竹枝扫帚,打扫落叶。迈出方步,车转腰身,带动腿脚,又全是老婆婆的身段了。眨眼工夫变了三变。
人众不知该认真还是只当表演,一齐望着小道姑。小道姑指指凉亭,亭里朦胧,一位老人家端正坐着,不出声,不起身,不朝前迎,不往后闪,又把人众诧异住了,自律脚步,不出山门门槛。
蓝斋娘朝里扫扫,朝外扫扫,紧扫两下,慢扫两下,不觉开了口:“什么朝里聚宝,朝外破财,胳臂肘朝里拐,八字脚朝外撇。说着说着说反了,站到对面立场,帮着仇家说起来。这也不管,只管说话,竹筒倒豆子只要倒不完就好。什么朝里朝外,你根本不放在心上。你心里有一枚苦胆,偏偏吐不出来,你只能满嘴里跑舌头......咦,你的舌头呢?张张嘴看看,总不会一根也没有了。
哟,红光满面,气色比当初还实质,你没有变老,你怎么一点也不变!
不,你变了,变多了,你满嘴的舌头变哪里去了,你怎么变木头变石头了!
是不是哑巴了?嗓子有毛病?
老人回答:“没有毛病。”
再说一遍。
再说我好好听听。
暴听深沉,细听起来平平淡淡。怎么暴听和细听不得一样,究竟是深沉还是平平淡淡、不招不惹、没着没落?
——莫非是撞着了生老病死,那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眨眼万变。说话有没有障碍?
蓝斋娘看着老道婆,心中有千言万语,但口中却只能说出两个字:“没有障碍。”
老人回答:“没有障碍。”
再说一遍。
再说我好好听听。
怎么听不清是不冷不热,还是没心没肺?是不悲不喜,还是无情无理?是升天升华,还是麻木麻痹?
——除非是合上了生老病死,那可是天长地久、有生就有死。天经地义,生死永不变。
你坐着,你不要走。你就不说走哪里去,起码也得告诉我,你为什么来。来许愿还是还愿?来报喜还是报忧?报恩还是报仇?
蓝斋娘看看留不住,眼角里,仿佛青石栏杆上,老人端正坐着的地方,留下个手巾包。赶紧抢进凉亭,抖开天蓝缎子手巾,一只完整的翡翠玉镯。粘结完好不用辨认。
这是遥远如梦幻的牛背上的梅兰芳,从天边拾来,压腕的玉镯。这是现实如欠债的道场上的梅兰芳,午夜升座,压髻的玉环。这是两口子借口朝里朝外一个两个争吵不休,吵成两段还是吐不出来的一个两个苦胆。
小道姑看见蓝斋娘手举玉环,玉光闪闪。蓝斋娘自己双眼直直勾勾,直什么?勾什么?小道姑跨出山门,两步过去抱住蓝斋娘,顿时觉得怀里枯萎、干痞、空虚、飘忽。觉得心酸,又觉得自然,因为觉得拥抱了生老病死......
众斋娘也都随着围住凉亭,听见小道姑一声断喝:冤生孽结。
蓝斋娘应了一声,挣脱怀抱,抖落袍袖,谁也料不到,又看见肉滚滚两条胳臂,抄起水竹扫把。只好说肉弹还是肉蹈也就是肉感,不好意思出口,变着法儿形容做藕形容做水晶糕。
小道姑又一声冤生孽结,蓝斋娘应声道穿上袍子,捋下袖子,扫扫落叶,人众眼前明明是一位半老的妇道人家了。
小道姑再一声冤生孽结,蓝斋娘迈出方步,车转腰身,带动腿脚,人众都觉得自身的筋骨也生硬起来,蓝斋娘的身段,十足是老婆婆了。
三声断喝,三变身影。人众倒吸冷气,望着道姑,张大瞳孔。不知是道不是道,只见断喝断变。
小道姑领着人众,回到正殿。木鱼笃笃,铜罄昂昂。人众随声随和,断句断落,太平经“自有自有”。此道之根柄也,阴阳之枢机,神灵之不变万变、万变不变也。大道生生生万物,真人法法法不变。
道姑一声断喝:冤生孽结。
回门——去不回门之三
老道婆蒲团坐静,日久坐化了。仿佛发酵蒸发,世称升天了。
小道姑当然升座观主。本来生性快活,脸带桃花,笑随银铃。真是个吉人自有天相,赶上“开放改革”,好运道不是一步步踱过来,是翻跟斗那样翻到眼前,那声势挡也挡不住,想躲也躲不逮。
许愿还愿、放生放焰口、做“会”做道场,这些过去被称为吃迷信饭的活动,如今已经改变。初一排上十五算是运道,现在已经变成了公开的“业务项目”,记账记事,公事公办,有衙门一般的派头。
蓝斋娘趁着热闹“改革”斋饭,煎出五香豆腐鲞,煮来雷竹油焖笋。小道姑随时随地夸口,好吃好吃,先是斋堂屋里叫卖,跟着外卖打包带走。贴上招牌纸,走出轧轧品牌档子第一步。昨天卖个鸡蛋还要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今天全国做生意,全民生意经。昨天过年馋饺子,今天吃腻了,改改素食爽口。道观里有快活快笑性格,有肉弹肉蹈实力,初一还在摆摊,十五就开店了。前店盾作坊,摇身一变加工厂。硬包装硬码,软包装闯荡江湖。从此说话也要新潮。
道观完成了资金原始积累,出家人兼任企业法人代表。脚踏三轮早已靠边,买了部烧油的“面包”。蓝斋娘脱袍捋袖,把白生生胳臂藕一般、玉一般、水晶糕一般搭在方向盘上。配合马达的颤抖,不消说形容做“肉弹”和“肉踏”。还勾出土话中“肉涨”、“肉烂”、“肉大”(读如陀)、“肉痒”,都是一语双关多关,普通话里难找替身。
这天,方向盘旁边还坐着演义法师,法师现在功成名就,也和演艺界的明星一样,拿拿出场费,经头经尾都由徒子徒孙们做了。只在午夜灯光灿烂时,梅兰芳那样压轴升座,善男信女也和追星族一般喝彩。彩声中有点曲子“去不回”“去不回”,有呼叫艺名“道场梅兰芳”“梅兰芳”。
这天,蓝斋娘转动方向盘,和法师说着闲话,忽然从反光镜里看见“面包”后边,紧跟着一辆马达单车。转一个弯,跟上来。急转一个弯,尾巴一样甩不掉。端详骑车人,是一个不认识的男子。可怪这个男子有一双直勾勾的眼睛,仿佛用眼睛勾住前边车辆。这个男子怎么看也认不得,可是这直勾勾眼睛也许大有来头,这么个直勾勾叫人想起了少年牛倌。牛倌一走几十年,他的样子早就模糊了,记得起来的只是“去不回”。也不知道现在的长相,其实是忘记了,只因来了道场上的梅兰芳,才把牛背上的梅兰芳也挂在嘴边,他们都能把“去不回”唱得花一般红水一般清。原原本本是两个人,偏偏说做一个,那是跟老公闹脾气。老公说两个,老婆说一个。朝里朝外,夺扫把,摔玉环,老公做了孤老,老婆当了斋娘。住道观图个清净,清净为了自由做梦......
明黄水绿,一直延伸到天边尽头。泥土丝丝,空气嗡嗡,直至地心深处。小姑娘舞着刀,画着龙。小牛倌牛角上挂着毛毛雨,牛尾晒晒暖,抬起身子,唱起了“去不回”。他将小姑娘的歌声也唱了进去,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蓝斋娘叫着法师,问他是否能唱两句解闷?
法师想了想,回答道:“去不回。”
于是,演义法师开始演唱这首歌曲的“身影”口巴部分。什么是“身影”?“身影”是“去不回”的现代版,是将山歌、蓝调、摇滚和前卫元素融合在一起的“去不回”。
小鸟飞走了,半空中留下了扇动翅膀的身影。翅膀扇走了,半空中留下了青春的身影。青春飞走了,半空中留下了扇动翅膀的身影。翅膀扇走了,半空中留下了小鸟的身影。这句话句回还往复,却唱出了一去不回来的感觉。原来这个一去不回来,是回还往复才去去的。
蓝斋娘顺着野调无腔,轻轻唱出了她的歌词。一个飞走了,半空中留下又一个身影。两个飞走了,半空中留下一个的身影。在反光镜里,演义法师骑着单车像是在表演节目一样,单车掉下时他砸在地上。驾车的蓝斋娘震惊地一震、一肉、一弹,然后开心地飞起来。演义法师也像飞了起来一样蹦高,撞向玻璃。在诗歌、曲调、梦幻和玩笑中,三条生命似乎自行蒸发了,与集体自焚的过程差不多。
世界上有森林定期自燃的记录。森林衰老且拥挤时,会自行燃烧,在中国被称为天火。在灰烬中冒出新芽,抽出新枝,子孙看到森林重生。对于一棵树来说,当天火烧来时,也许只需一眨眼就焦完了。但如果认为这就是生命的终结,必须清楚地交代清楚。那就需要既描绘全景,又续够细节。一眨眼的工夫就是眼皮一张一合的过程,可以分做张时和合时两部分,相对清晰。
张时:
蓝斋娘肉弹一般紧急刹车,斜着飞身撞开车门,落在外侧路边草地上。前轮冲进路边,撞翻护路石块。车上的一个备用轮盘震动着掉落下来,飞向青草。演义法师弹起身体前倾,撞向窗户玻璃。后面的男子差点儿钻进“面包”车底,刹车带蹦跳着飞离单车,落在地上站定。
法师有道行,落下时紧急如闪电,还能闪现微笑。那是给世人看的笑容,眼前不会有世人出现。但即使这样给世人看也是法师的习惯。不认识的男子在站定脚跟刹那与直勾勾盯着的“面包”车交换了一个惊险的眼神。蓝斋娘飞落在路边草地上,脸贴着温柔的青草,嘬嘴做出亲吻的动作:“啊,生活多美好!”这是眼皮张开时的写真。百分之一秒后,眼皮合上了。
合时:
蓝斋娘飞身站在车外,演义法师落下身体并猛地撞向方向盘,口中喷出鲜血直接喷向窗户玻璃。后面的男子身材结实动作敏捷,像表演杂技那样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站稳了脚跟。然而车辆上的备用轮盘却震动着飞了过来,重击他的背部并使他向前扑倒再也没有动弹过
蓝斋娘落在路边草地上,青草柔软如丝绸。恰好路边撞翻的石块滚过来,两相合力,脑门开瓢,面目破坏。只是百分之一秒里眼皮合下时,全局改观。众斋娘齐集正殿,小道姑领头做道场。现在已经权威,喝道:冤生孽结。想当年小道姑刚会走路,拜老道婆做亲娘。老道婆双手摩娑她的小脑袋,笑眯眯说,冤生孽结。众斋娘这时心情沉重,虽没看见谁的眯眯笑容,却听出来小道姑权威声音透着轻松、清爽,好像雨后天晴,褪下湿棉袄,扳开旧绳索。木鱼笃笃敲响,铜罄昂昂高鸣。小道姑朗诵如道观里的月洞魔力,山门外的小桥流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一本万利,万紫千红。成立新公司,取名去不回。推出品牌菜,打出功臣牌。斋娘豆腐鲞,法师油焖笋。牛倌素、兰劳斋、素鸡、素鸭、素鱼、素肉、肉弹、肉涨、肉烂、肉痒。如今和为贵,互补又双赢。自阴到阳,自生到死。天人互动,道法自然。此道之根本也,阴阳之枢机,神灵之至意也。
选自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矮凳桥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