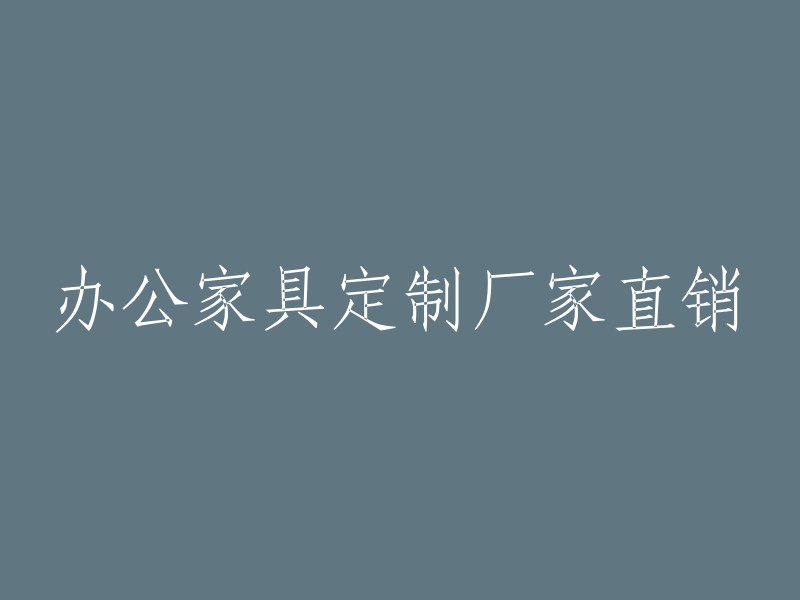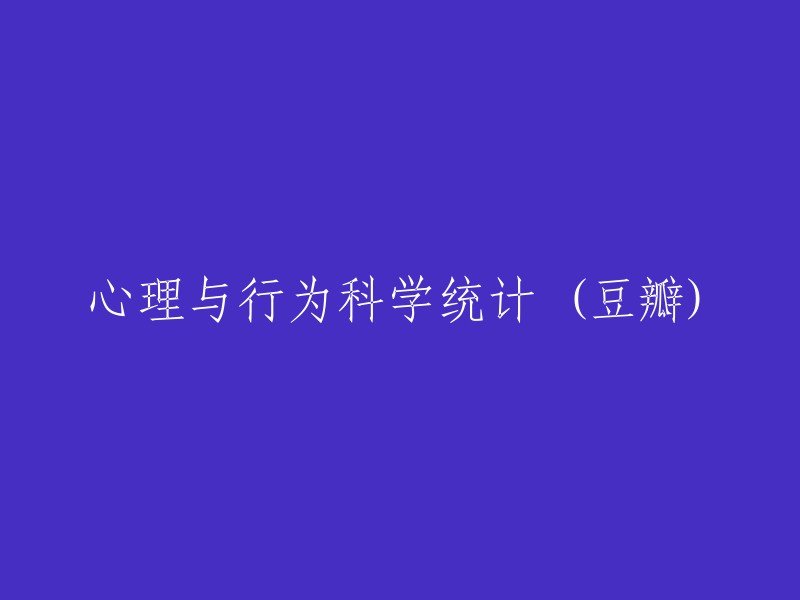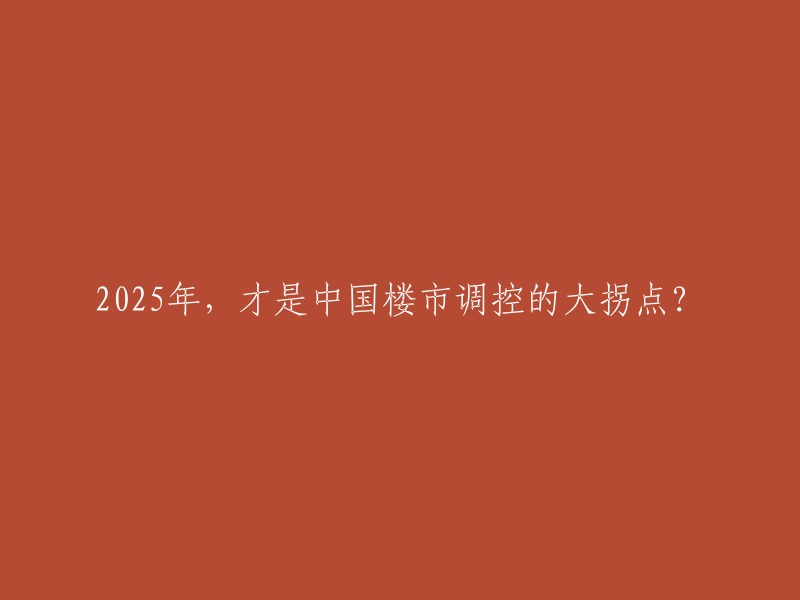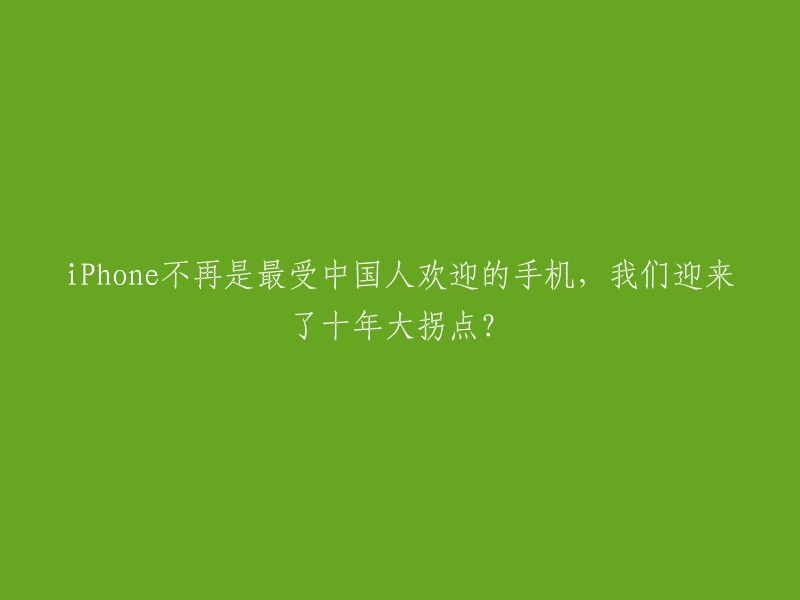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有《保卫社会》。他认为法律的目标应该是“扬善抑恶”,并且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商业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道德危机并不是说发生在哪一天哪一年,而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者没有把社会保护好,滥用市场原则到社会生活领域,以至越来越厉害。
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社会信任危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近年来,社会上的欺诈事件层出不穷,从网络诈骗到假冒伪劣商品,无不暴露出信任的严重缺失。与此同时,人际关系也日趋紧张,邻里之间的相互猜疑、亲戚朋友之间的疏离,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信任的流失。这些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社会信任危机日益严重的生动写照 。
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认为,社会信任危机已经深深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其表现多样且令人担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似乎逐渐失去了与他人的紧密联系。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邻里间亲如一家,孩子们在巷子里自由玩耍,大人们则聚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的聊家常。但如今,这样的情景已变得稀缺。邻里之间可能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心生猜疑,甚至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产生矛盾 。
罗教讲表示,当下社会“信任困境”的形成与破解需要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所谓“信任危机”,探索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有效地尽快化解“信任危机”,重建社会的信任。
郑永年:如果我们现在进行社会建设,谁来建呢?你希望有钱人来建吗?你希望有权的人来建吗?你希望知识分子来建吗?在所有社会关系都利益化的时候,共建的主体是谁呢?该叫谁来建设呢?还是那句话,立法者应该好好反思,要全社会来共建。
小悦悦这件事,我们是在海外看到的,有人称之为“中国震撼”。这种事情给人负面的震撼,要远远超过10个奥运会和10次世博会,再建几千所孔子学院,都没有这个效果。
《新周刊》:个人能做些什么?
郑永年:自上而下所能做的就是法律,道德的重建是全社会要来做的,比如我们现在的NGO,好多都很糟糕。中国现在好多运动,我觉得其实什么运动都不要,最重要的是进行公民社会建设。道德不可能自上而下,社会要自救。
发展并非只是GDP
《新周刊》:在你今年出版的新书中,提出了“保卫社会”这个概念。为何急需“保卫社会”?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保护机制?
郑永年:从很多年前开始,我就在写这一系列的文章,因为我看到中国社会缺乏保护机制,现在更是越来越体现出来了。有钱有势的人更应当思考这件事情,今天大家同情的是一个穷人的小孩,但如果同样的遭遇发生在富家子弟身上呢?说不定有人会觉得大快人心。中国社会现在就是这样,谁会同情有钱的人?谁会同情有权的人?社会搞得很对立、很分化。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是“凶手”,人人都是受害者,没有哪一个是赢家。
《新周刊》:你认为,现在正是从“发展第一”转为“保护社会”的时候。该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发展也成为坏的发展”?
郑永年:发展并非只是GDP,光有经济发展,没有社会发展,就会成为坏的发展。贫富分化很厉害,这样的发展肯定不行;以钱为本的发展,也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要讲发展方式,这非常重要。
《新周刊》:现在是我们开始进行自我救赎的时候了吗?
郑永年:对了,谁也不要靠谁。有钱没钱的,有权没权的,都要自我救赎,该是每一个人都思考的时候了。社会也要自救,个体要自救,知识分子也该反思了。
不要把这个社会理想化,在钱、权和社会三者之间,社会是最弱的一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社会是要被保护的。为什么西方法律体系要强调收入制分配、要遏制权力滥用、要完善税收制,要发展SEM(中小型企业)——这都是保护社会机制。为什么要让穷人看得起病?为什么要有社会保障不让穷人饿死?这些都是保护社会的。
《新周刊》: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不知道。但每次这种事情发生,总有人站出来说,中国并不是人性都没有了。我想,老人倒了以后,还是有很多人会去扶的,也并不是每一个小孩发生这种事情都是同样的遭遇。我相信人性还是有光辉一面的,但是体制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扬善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