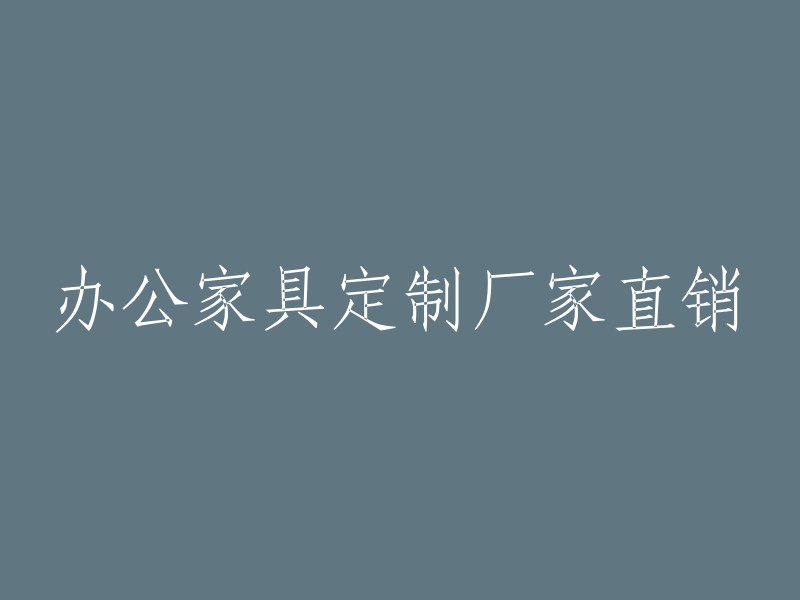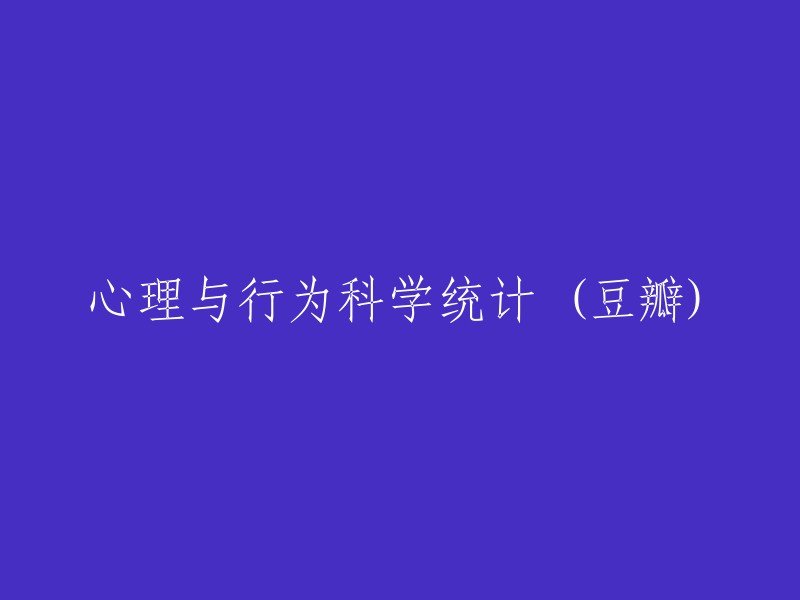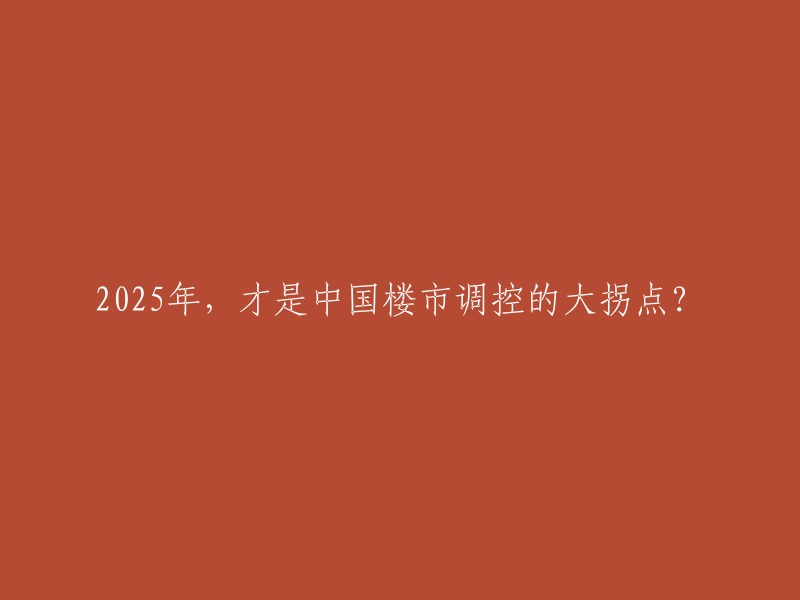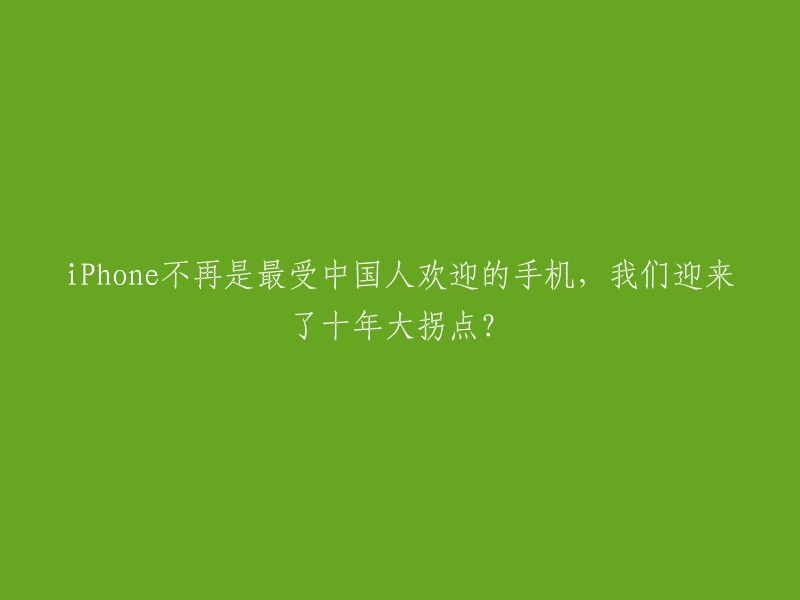在本次讲座的最后,我想对您们回顾一下我所分享的内容。我曾试图从战争的角度来探讨历史进程可理解性的问题,将战争视为种族战争的历史框架。我认为,这个种族战争的概念可能是我试图建立的。上一次,我曾向您们解释过民族战争如何通过民族普遍性的原则最终被历史分析所排除。现在我要告诉您们的是,种族主题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另一种形式中被重新采用,那就是国家种族主义。今天,我想让您们了解国家种族主义的诞生背景。
19世纪的一个基本现象是,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权力承担生命的责任:如果你们不反对,这实际上是对活着的人的权力,某种生命国家的化,或至少某种导向生命的国家化的趋势。为了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统治权的经典理论出发,它作为所有对战争、种族等进行分析的基础。在统治权的经典理论中,生与死的权利是其基本特性之一。然而,在理论层面上,生与死的权利具有一定的奇怪性;实际上,拥有生与死的权利意味着什么呢?换句话说,君主有权决定生死,这意味着他可以让人死也可以让人活。无论如何,生与死并非自然、直接、原始或根本的现象,它们处于政治权力领域之外。
如果我们继续推究这个问题,最终会达到一个悖论:这实际上意味着,面对权力,拥有全部权利的臣民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从生与死的角度来看,他们处于中立状态,仅仅根据君主的存在,臣民有生的权利或者也潜在地有死的权利。然而,臣民的生与死仅仅通过君主意志的作用才能成为权利。如果您同意的话,这就是理论上的悖论。理论上的悖论必须由实践的不平衡来弥补。实际上,生与死的权利意味着什么?当然不是君主可以像他可以使人死一样让人活。生与死的权利只能以一种不平衡的方式运转,而且总是在死这一边。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归根结底,他身上掌握的生与死的权力的本质实际上是杀人的权力:只有在君主杀人的时候,他才行使对生命的权利。
这本质上是刀刃的权利,因此在这个生与死的权利中不存在真正的对称。这并不是使人死和让人活的权利,也不是让人活和使人死的权利,而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当然,这导致了明显的不对称。
我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补充统治权的古老权利(使人死或让人活),用一种新的权利。这种新的权利不会取消第一个权利,但将进入它、穿越它、改变它。它将是一种恰好相反的权利,或毋宁说权力:“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
君主的权利,就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然后,新建立起来的权利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可以在权利理论中追寻它的进程(但我会讲得非常快)。你们看到,在17世纪以及特别是18世纪的法学家那里,已经提出了关于生与死的权利问题。当法学家说:当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也就是说集合起来任命一个君主,赋予君主以针对他们的绝对权力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受到危险或生活需求的逼迫。因此,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正是为了生存,他们才任命一个君主。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实际上是否能够进入君主的权利呢?生命难道不就是君主权利的基石吗?君主是否可以向臣民宣称对他们运用生与死的权力的权利,简单地说,也就是处死他们的权力呢?在生命是契约最初的、根本的动机的意义上,它是否应当处于契约之外呢?
这一切都是政治哲学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它衡置一边,但它仍然指出生命的问题怎样在政治思想、政治权力的分析领域中开始问题化了。实际上,在这里我想要跟踪这个转变,但不是在政治理论的层面上,而是在权力的机制、技术、工艺的层面上。那么,这里我们又遇到了熟悉的东西:即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主要围绕着肉体、个人的肉体的权力技术。通过这些程序,围绕这些个人的肉体和整个可视范围,人们保证了个人肉体的空间分布(他们的分离、他们的行列,把他们分类和进行监视)和组织。
也正是通过这些技术,人们对肉体负起责任,通过锻炼、训练等,人们试图增强他们有用的力量。权力的合理化技术和严格的节约同样也以可能的最便宜的方式运转起来,通过监视、等级、审查、诉状、报告的系统:这整个技术可以称之为工作的纪律/惩戒技术,它从17世纪末开始并在18世纪建立起来。
在18世纪下半叶,权力的另一种技术出现了。这种权力技术不排斥第一种,即惩戒的技术,而是包容它,把它纳入进来,部分地改变它。这个新技术没有取消惩戒技术,仅仅因为它处于另一个层面,它处于另一个等级,它有另一个有效平面,它需要其他工具的帮助。这个新的非惩戒权力的技术运用的对象(与针对肉体的惩戒不同)是人的生命或者说是针对活着的人。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因此,在第一种对肉体的权力形式(以个人化的模式)以后,有了第二种权力形式,不是个人化而是大众化。在18世纪进行的肉体人的解副政治学以后,在同一个世纪末出现了某种东西,它不再是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而是我所说的人类的“生命政治学”。
在权力的新技术、生命政治学和正在建立的生命权力的背景下,到底是什么构成了首要对象和控制目标呢?刚才我提到了出生率、死亡率、寿命等一系列与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关的指标。我认为,在18世纪下半叶,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结合,成为了知识的首要关注领域和生命政治学的主要目标。在这个时期,最初的人口统计学开始对这些现象进行统计研究。
观察这些统计操作:它们或多或少是经过协商的,或者至少是在人口中对出生率进行调查。简单来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这就是对18世纪实施的控制出生现象的一种定位。这也是对鼓励生育政策的一种描述,或者至少是对干预整体出生率现象的一种概述。
在这个生命政治学中,问题不仅仅是繁殖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中,还有发病率问题。到18世纪末,发病率已经不再是流行病的问题,而是另一种类型的问题,大致上可以称之为地方病。地方病是统治某地居民的疾病的形式、性质、传播途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
这些或多或少难以根除的疾病,以死亡更频繁的名义,不再被视为流行病,而是被视为削减力量、减少工作时间、降低能量和经济代价的因素(人们正是这样对待它们的)。这些因素既是生产的损失,又是治疗的代价。简而言之,疾病作为人口现象:不再表现为突然夺去生命的死亡(这是流行病),而是表现为永久的死亡,它在生命中不断地滑动,不断地侵蚀、打击和削弱个体。
从18世纪末开始,人们对这些现象负起责任,导致了这样一种医学的建立,其主要职能是公共卫生,包括协调医疗、集中信息、规范知识的机构,它还开展全民卫生学习和普及医疗事业的运动。因此,同样是再生产、出生率的问题,也是发病率的问题。生命政治学干预的另一个领域是,一些人是普遍的而另一部分人是偶然的这个整体现象,然而后者之中的一部分即使是偶然的,也有一部分永远不能完全被压缩,它们也会导致与无能力、排除在个人的循环、中和作用等之外类似的结果。
从19世纪初(工业化时期)开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老人,因此落入能力和活动领域之外的个人。另一部分是事故,残疾和各种异常。针对这些现象,这个生命政治学不仅建立了教济机构(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有更敏锐的机构,比既庞大又不能面面俱到的机构在经济上合理得多。它们主要附属于教会,此后,还将有更敏锐、更合理的机构,如保险、个人和集团储蓄、社会保障等等。
最后一个领域(我列举主要的,它们出现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此后,其他的还有不少);对人类的联系负责(人作为种类,作为活着的生物),然后对他们的环境负责,生存环境——无论是否地理的、气候的还是水文的环境的直接后果,如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的沼泽问题,与沼泽有关的流行病问题。同样,也有环境的问题,因为它已不是自然的环境并对居民有反作用:有居民创造的环境。这主要是城市问题。这里,我简单地向你们强调生命政治学建立于其上的某些点。它的某些活动和首要的干预领域、知识领域和权力领域:出生率、发病率、各种生理上的无能以及环境的后果正是关于这一切。生命政治学抽取其知识并确定干预和权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