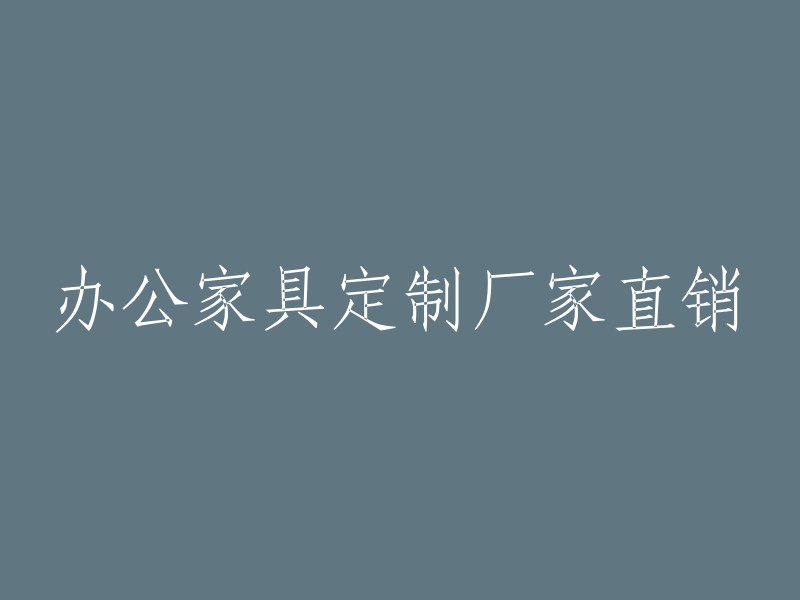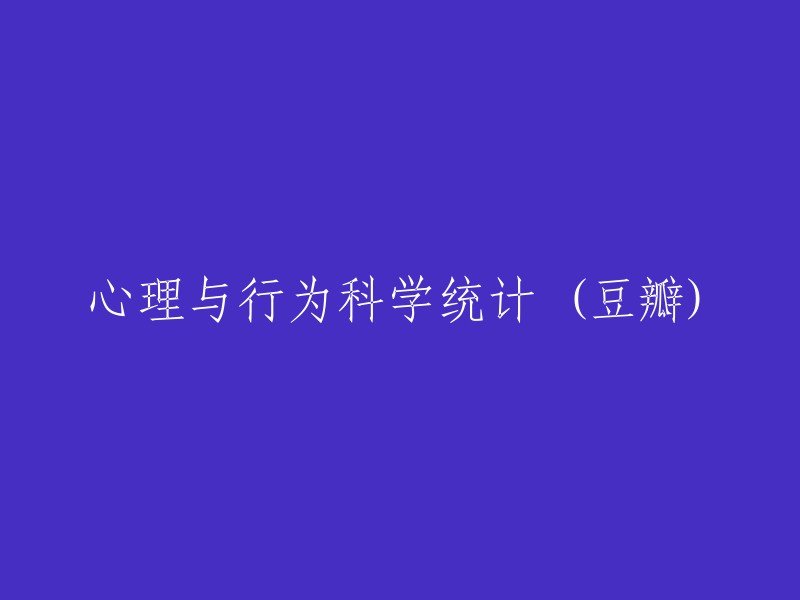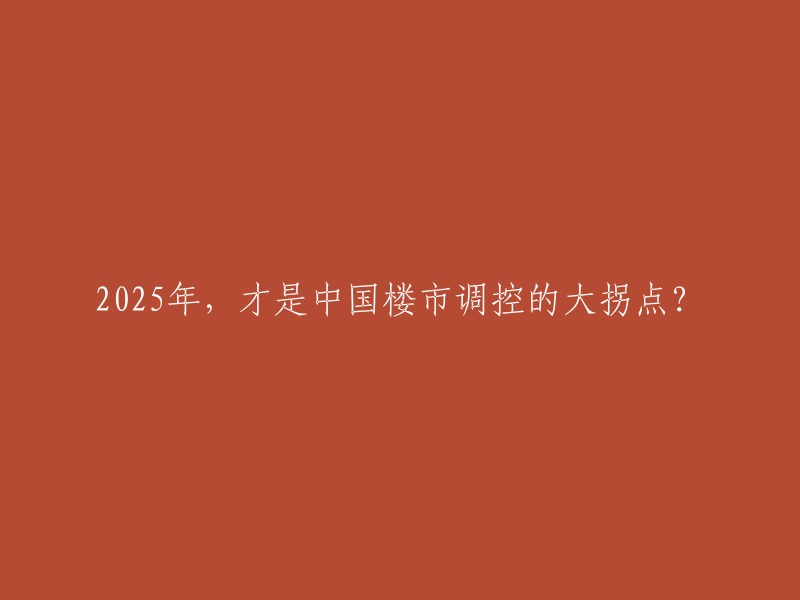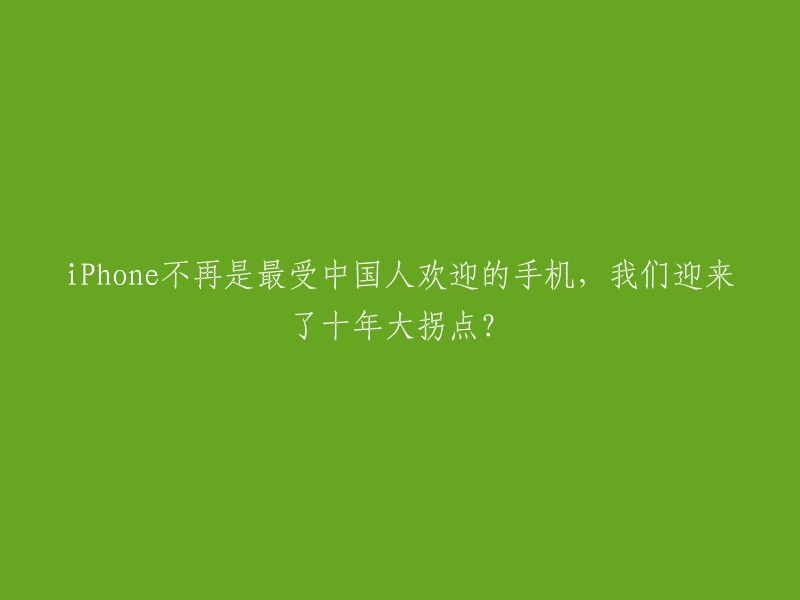在讨论相反情况之前,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这类人。他们并没有特别出色的精神能力,但他们的理智相对于一般人来说要多一些。他们在艺术方面的爱好仅限于粗浅的涉猎,或者只对某个科学的分支有兴趣,如植物学、物理学、天文学或历史。他们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能够找到极大的乐趣,当那些导致幸福的外在推动力一旦枯竭,或者不再能满足他们时,他们便会转向这些研究来取悦自己。可以说,这样的人的重心已经部分地存在于他自身之中了。
然而,这种对艺术一知半解的爱好与创造性的活动有很大的区别。业余的科学研究容易流于浅薄,而且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人不应该完全投入到这样的追求中,或者让这些追求完全充斥整个生活,以至于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唯有最高尚的理智能力,即我们称之为天资的东西,无论是将其生活视为诗的主题,还是视为哲学的主题,它都需要研究所有的时代和一切存在,并试图表达出关于世界的独特概念。因此,对于天才来说,最为迫切的是没有任何干扰的职业、自己的思想及其作品;他乐于孤独,闲暇为他带来愉快,而其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负担。
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他的重心完全存在于他自身之中。这就说明了,这样的人——尽管他们的性格非常优秀,但他们极少会对朋友、家庭或一般的公众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和兴趣,而其他人则常常如此。如果他们的内心只有自己,那么他们就不会为失去任何其他东西而感到沮丧。这使得他们的性格有了孤寂的基础,由于其他人绝不会让他们感到满意,所以这种孤寂对他们来说愈发有效。总的来说,他们就像是性格与众不同的人,因为他们不断地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差别,所以他们就像外国人一样,习惯于流离转徙,浪迹天涯,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思考,用“他们”而非“我们”来指称人类。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自然赋予了理智财富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主观世界要比客观世界和我们的关系紧密得多。因为无论客观事物是什么,它们只能间接地起作用,而且还必须以主观的东西为媒介。
卢西安认为,灵魂的富有才是真正的财富。他强调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外在的物质,而需要宁静、闲暇以及锻炼理智的能力来享受这种内在的财富。在他看来,一个人是否幸福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完成自己的使命,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因此,最有才智的人都会赋予无干扰的闲暇以无限的价值,就像它与人本身一样重要。苏格拉底也曾赞美过闲暇是最美好的事物之一。亚里士多德则指出,献身于哲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他认为,只要得到自由发挥,无论什么能力都是幸福的。
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也持相同观点,认为生来有天才并能利用这种天才的人在利用其天赋时会得到最大的幸福。然而,普通人的命运注定难得有无干扰的闲暇,因为他们需要终生为着自己和家人谋求生活必需品,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进行智力活动。因此,一般人很快就会对无干扰的闲暇感到厌倦。如果没有一些不真实、不自然的目的来占有它(如玩乐、消遣、所有癖好等),人生便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这个原因,它受到了种种可能性的威胁,正如这句格言所说的——一旦无所事事,最难的莫过于保持平静。
另一方面,理智太过超常也会变得不自然。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超常的理智,那么他便是一位幸福的人。他所需要的无干扰的闲暇正好是其他人认为令人感到难以负担、有害的东西;一旦缺少了闲暇,他便会成为套上缰绳的柏伽索斯(希腊神话中有双翼的飞马,是诗人灵感的象征)而不幸福。如果这两种情况——即外在的与内在的、无干扰的闲暇与极度的理智——碰巧在同一人身上统一起来,那将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如果结局一直令人满意,那么便会享有一种更高级的人生——免于痛苦和烦恼的人生、免于为着生存而作痛苦斗争的人生以及能够享受闲暇的人生(这本身便是自由悠闲的存在)。只需相互中和抵消,不幸便会远离他方。
然而,有些说法和这种看法相反。理智过人意味着性格极度神经质,因而对任何形式的痛苦都极其敏感。而且,这种天赋意味着性格狂热执著,想像更为夸张鲜明,这种想像如影随形不可分离地伴随着超常的理智能力,它会使具有这种想像的人,产生程度相同的强烈情感,使他们的情感无比猛烈,而寻常的人对于较轻微的情感也深受其苦。
世界上产生痛苦的事情比引起快乐的事情多。有人常常似是而非地说到,心灵狭隘的人实质上乃是最幸福的人,虽然他的幸运并不为人所羡慕。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在读者自己进行判断前表明我的看法,尤其因为索福克勒斯自己表明了两种完全相抵触的意见。他说:“思想乃是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在别的地方,他又说:“没有思想的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旧约全书》的哲人们也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同样的矛盾。如《圣经外传》上写道:“愚昧无知的生活比死亡还要可怕。”而在《旧约·传道书》中又说:“有多少智慧便有多少不幸,创造了知识就等于创造了悲哀。”
但是,我们说,精神空虚贫乏的人因为其理智狭隘偏执平庸流俗,所以严格地说,只能称为“凡夫俗子”(philister)——这是德语的一种独特表达,属于大学里所流行的俚语;后来使用时,通过类比的方法获得了更高的意义,尽管它仍有着原来的含义,意思是指没有灵感的人,“凡夫俗子”便是没有灵感的人。我宁愿采取更为偏激的观点,用“凡夫俗子”这个词来指那些为着并不真实而自以为实在的现实而忙忙碌碌的人。但这样的定义还只是一种抽象模糊的界说,所以并不十分容易理解,在这篇论文里出现这样的定义几乎是不合适的,因为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俗。如若我们能令人满意地揭示辨别凡夫俗子的那些本质特征,那么我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阐明其他的定义。我们可以把他们界说为缺少精神需要的人,由此可以得出:
第一,相对于他自身,他没有理智上的快乐。如前所说,没有真实的需要,便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凡夫俗子们并非靠了获取知识的欲望,靠着为他们自身着想的远见卓识,也不是依靠那与他们极其接近的富于真正审美乐趣的体验,来给他们的生活灌注活力。如果这种快乐为上流社会所欢迎,那么这些凡夫俗子便会趋之若鹜,但他们所发现的兴趣只局限在尽可能少的程度。
他们惟一真正的快乐是感官的快乐,他们认为只有感官的快乐才能弥补其他方面的损失。在他们看来,牡蛎和香槟酒便是生活的最高目的。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获取能给他们带来物质福利的东西。他们确实会为此感到幸福,虽然这会引起他们一些苦恼。即使沉浸在奢侈豪华的生活之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感到烦恼。为了解除苦恼,他们使用大量的迷幻药物、玩球、看戏、跳舞、打牌、赌博、赛马、玩女人、饮酒作乐,旅行等,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使人免于烦恼,因为哪里没有理智的需要,哪里就不可能有理智的快乐。
凡夫俗子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呆滞愚笨、麻木不仁,和牲畜极其相似。任何东西也无法使他高兴、激动或感兴趣,那种感官的快乐一旦衰竭,他们的社会交往便即刻成为负担,有人也许就会厌倦打牌了。舍弃那些浮华虚荣的快乐,他可以通过这些虚荣来享受到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快乐。例如,他感到自己在财产、地位上相对其他那些敬重他的人的权势及力量都高人一等;或者去追随那些富有而且权势显赫的人,依靠着他们的光辉来荣耀自己——这即是英国人称之为“势利鬼”的家伙。
从凡夫俗子的本性来看,他们缺乏理智的需要,只关注物质需求。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与那些能满足他们物质需求而非精神需求的人交往。在这些人眼中,从朋友那里获得任何形式的理智能力被视为无关紧要;甚至,如果他们碰巧拥有这种能力,也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和憎恶。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除了令人不快的自卑感外,他们内心深处还会感到一种愚蠢的妒意,但这种妒意必须小心隐藏,否则可能变成一种藏而不露的积怨。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考虑让自己的价值或财富观念与这些品质相一致。
庸夫们总是追求地位、财富、力量和权势,认为这些东西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他们渴望成为擅长谋取这些福利的人,这便是作为一个没有理智需要之人的结局。对理想毫无兴趣是所有庸夫们最大的苦恼,为了摆脱这种苦恼,他们不断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然而,实实在在的东西既不能让他们知足,也是危险的。当他们对这些东西失去兴趣时,他们会感到疲惫不堪。相反,理想的世界是广阔无边的、平静如水的,它是“来自于我们忧伤领域之后的某种东西”。
在上述关于幸福个人品性的论述中,我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自然和理智的本性。至于道德对幸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请参考我的获奖论文《道德的基础》(第2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