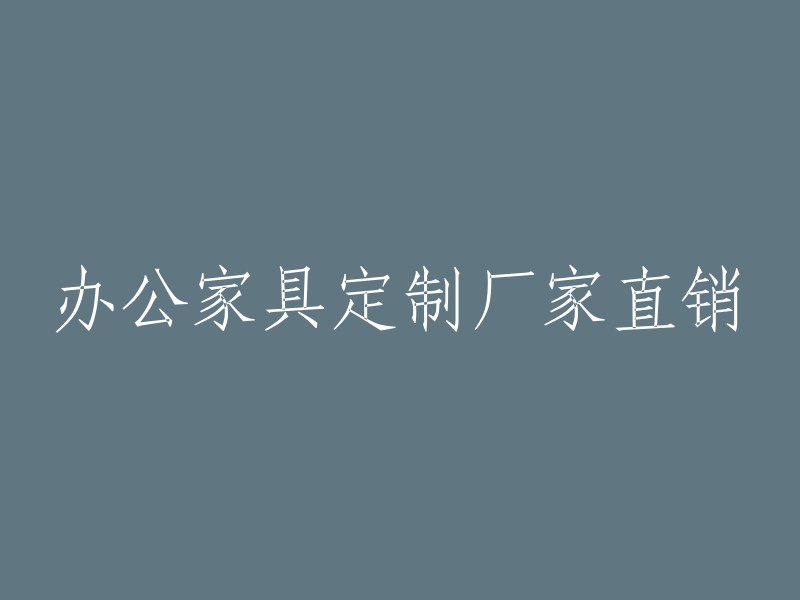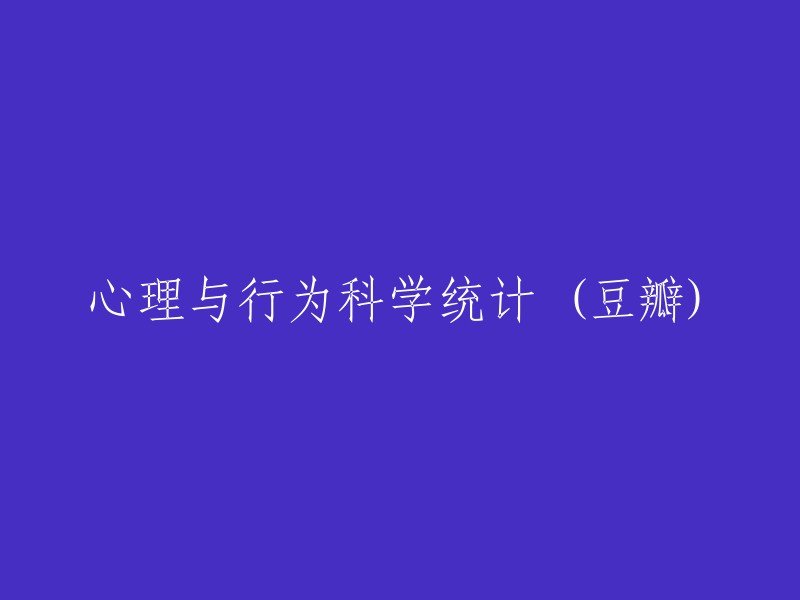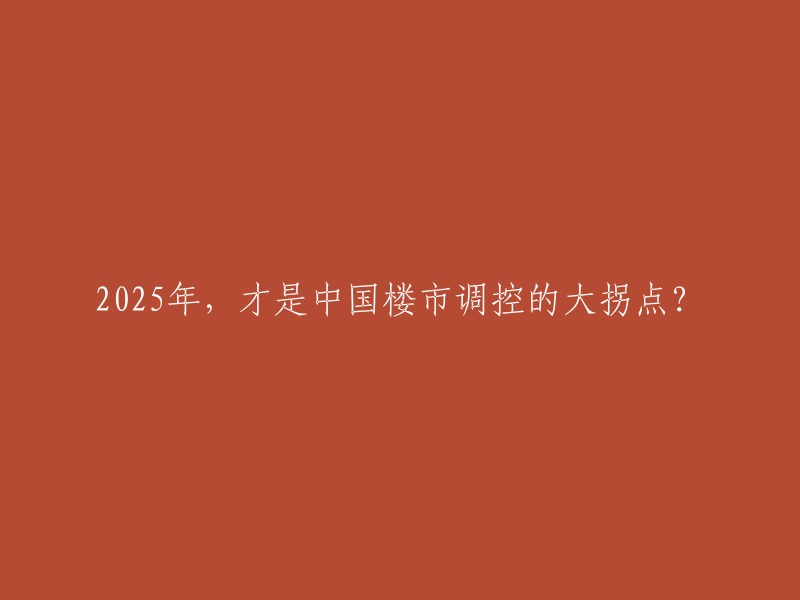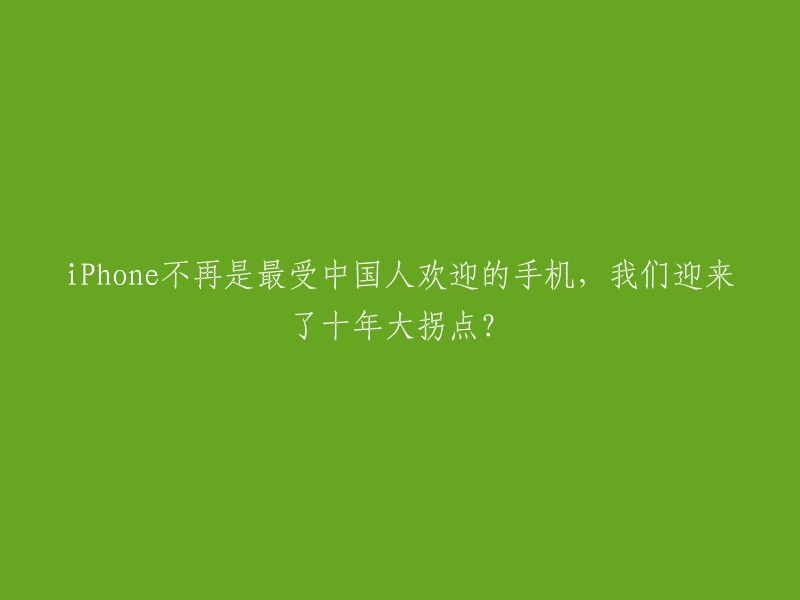译序:
2011年9月,我在购书时顺便购买了英国诗人罗宾·罗伯逊翻译的一本薄薄的托朗斯特罗姆诗集。这本书的可读性很高,于是我又抄出了勃莱的英译精选本《半完成的天堂》和罗伯特·哈斯编的英译本精选集《诗选》。在阅读这些诗歌后,我又上网订购了富尔顿的译本(《诗选》中有很多出自富尔顿之手)。当这位诗人获得诺贝尔奖时,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因为我已经不再关心他是否获奖。但当我的同事拿着电讯稿来问我是否知道这位诗人时,我说:“啊,他的诗集就在我的桌上!”因此,除了翻译电讯稿外,我还为这个特殊贡献翻译了一些诗歌,如《冬夜》,并随报道发表。随后,由于有报刊约请翻译,我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翻译了约三十首。当然,我在翻译过程中反复阅读了手中的三本诗集。
我不只翻译了这些诗歌,还有几首我不太满意,最后只好放弃。但收录在这个小集子里的,都是经过精心阅读、精心挑选和精心翻译的。我希望读者们在阅读这些诗歌时,只要觉得其中有几首是非常好的,就应该把其他诗歌当作至少同样好的作品来对待,仔细阅读,直至最后能够全部欣赏。当然,这最后的时间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年或八年!
译者:
2012年2月23日于香港
风暴:
行路者突然走到那棵古橡树:一头石化的巨鹿,它那宽如地平线的鹿角守卫着秋天大海暗绿色的围墙。一场来自北方的风暴。现在是花楸浆果的时节。夜里醒来他听见——在那棵巨橡高处——群星在马厩里踢蹄。
轨迹:
夜,两点钟:月光。火车停下在平原的中央。远方一座城镇的光点在地平线上寒冷地闪耀。如同一个人进入梦境那么深以致他想不起身在何处当他回到他的房间。又如同一个人病得那么重以致他从前所有日子都变成一些发光点地平线上一团微弱而阴冷的模糊物。火车静止不动。两点钟:遍地月光,几颗星。
情侣:
他们熄了灯,白色灯泡闪烁了一会儿像一颗药片在黑暗的杯中升起又降落然后溶解。他们周围酒店墙壁高耸而起溶入天空的黑暗里爱的戏剧已落幕他们在睡觉了但他们的梦将相遇如同颜色在学童潮湿的画纸里相遇彼此交融周围都是黑暗和寂静城市靠拢过来窗子纷纷关掉房子相继走近它们紧贴着挤成一团聚精会神这群没有面孔的观众C大调当他在约会之后来到大街上空气正与雪花一起旋转冬天在他们躺在一起时降临了黑夜照出白光他喜悦地快步走着整座城市都在下山一个个微笑从身边经过每个人都在竖起的衣领后微笑真轻松!
所有的问号都开始赞美上帝的存在。他这么想。一支音乐突然出现,并与长脚步一起,走在旋转的雪花中。路上一切都倾向C音。一个颤抖的罗盘指向C。一个小时,高于所有痛苦。真容易!在竖起的衣领后,每个人都在微笑。
从山上,我站在山上眺望海湾。轮船休息在夏天的表面上。“我们是梦游者。漂流的月亮。”白帆这么说。“我们滑过沉睡的屋子。我们轻轻打开房门。我们倾向自由。”白帆这么说。有一次我看见世界的意志群出海,它们走同一条航线——一支庞大的舰队。“我们解散了。不再护送谁。”白帆这么说。
锡罗斯岛:在锡罗斯岛海港,废弃的商船闲置着。一个又一个又一个船头,已停泊多年。开普里翁号,蒙罗维亚。克里托斯号,安德罗斯。斯科舍号,巴拿马。水上的黑暗油画,它们被悬搁一旁。如同来自我们童年的玩具,变得庞大无比,提醒我们我们从未成为我们曾经想成为的克塞拉特罗斯号,比雷埃夫斯。仙后号,蒙罗维亚。海洋已不再扫瞄它们。
但是当我们刚到锡罗斯岛时,已经是夜里了,我们看到月光下一个又一个又一个船头,心想:多么浩荡的船队,多么紧密地相连!在尼罗河三角洲,那年轻妻子在城里逛了一天,回酒店吃饭时就哭了。她在城里见到爬在地上躺在地上的病人和将因匮乏而死的儿童。她和丈夫上到他们的房间里去,房间里洒了水,使尘土不飞扬。他们没说几句话就各自上床。她睡得很沉。他醒着。在黑暗中外面有一阵喧闹鱼贯而过。抱怨声、脚步声、叫喊声、车辆声、歌声。它在贫困中继续着。它永无尽头。他透出一个“不”字便蜷缩着睡去。来了一个梦。他在海上旅行。灰色的水中升起一阵波动,一个声音说:“有一个善良的人。有一个可以看事物而不带憎恨的人。”
快板:我在一个黑色日子之后弹奏海顿,并感到双手有一种简单的温暖。键盘很愿意。柔和的槌击。声音是绿色、活泼和宁静的。声音说存在着自由,说有人不向恺撒纳税。我把双手放在我的海顿口袋里,假装用冷眼看世界。我举起海顿旗——它申明:“我们不投降。但我们要和平。”音乐是山边一座玻璃房子,那里石头飞翔,石头粉碎。石头直接撞穿玻璃,但房子依然完整。
半完成的天堂:消沉脱离它的航道;苦恼脱离它的航道;秃鹰脱离它的飞翔;热忱的光川流而出,就连鬼魂也喝一杯。我们的绘画见到日光;冰河时代洞穴里那些红野兽;
一切都开始四下张望。
我们这几百人组成的队伍,走在阳光下。
每个人都像一道半开的门,通往欢迎每个人的房间。
脚下是无尽的田野。
水在树林间闪烁着光芒。
湖面犹如大地的窗口,俯瞰四周。
冬夜
风暴张大巨口,对准屋子,企图吹出一个音调。
我翻来覆去,紧闭双眼,阅读风暴带来的文字。
小孩的眼睛在黑暗中瞪大,而风暴为他咆哮。
两者都钟爱那摇曳的灯火:
两者几乎快要交谈。
风暴拥有小孩的手和翅膀。
远方,旅行者急匆匆地躲避。
屋子感受到它自身密集的钉子正把墙壁固定。
在我们卧室里,夜色宁静无声,脚步的回声渐渐消失,如同池塘里的落叶。
但外面的夜色愈发凶猛。
一场更黑暗的风暴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世界。
它张大巨口,对准我们的灵魂,企图吹出一个音调。我们害怕,担心风暴会将我们吹得一干二净。
来自非洲的日记
在矫情的刚果艺术家们的画作里,那些人物瘦小如昆虫,他们的人类能量令人心生悲伤。
从一种生活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活方式并非易事。而抵达的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一名非洲青年发现一位游客在茅屋之间迷失方向。他犹豫不决,不知该与游客成为朋友还是勒索他。他的踌躇令他痛苦不已。最终,他们在困惑中分道扬镳。
欧洲人紧紧拥抱他们的汽车,仿佛汽车就是他们的母亲。蝉鸣之声强烈如雷鸣电闪。汽车载着他们回家。很快,可爱的黑夜降临,洗净了脏衣物。安眠。而抵达的人仍然要走漫长的路。也许,一群移民之间的握手会有帮助。也许,让真理逃出书本也会有所助益。我们必须走得更远。
这名学生通宵苦读,学习再学习,以期获得自由。当考试结束时,他已成为后来者的台阶,踏上一条艰难的道路。抵达的人仍然要走漫长的路。
致敬
沿着反诗墙行走。那堵墙。别看墙的另一边。它试图将我们的成年生活困于常规城市、寻常风景之中。艾吕雅轻轻按下某个按钮,墙便缓缓打开,露出花园。我曾时常带着牛奶桶穿越森林,周围都是紫色的树干。一个老笑话悬挂在那里,美丽如同一只许愿船。夏日午后诵读《匹克威克外传》。那种生活多么美好啊:安静的马车上挤满了兴奋的绅士们。闭上眼睛,换马。痛苦中涌现出童真的想法。我们在病床边祈求这场恐怖能够稍作停歇,如同一道裂缝,让匹克威克们得以挤过去。闭上眼睛,换马。我们很容易便喜欢上早已在路上的碎片:教堂钟上的铭文、历代圣徒的格言以及成千上万年的种子。阿基洛克斯!没有回应。群鸟在大海的粗皮上游荡。我们将自己和西默农锁在屋里,在连载小说的入口处感受人类生活的味道,感受真理的味道。敞开的窗子停止摆动在这树梢面前,
在这黄昏天空的告别信面前,正冈子规、比约林和翁加雷蒂用生命的粉笔在死亡的黑板上写字。那种完全有可能的诗,让我仰望当枝条摇荡时,白鸥正在吃黑樱桃。
阿基洛克斯,古希腊诗人,他的作品中提到了开放与封闭的空间。一个男人用他的工作来感觉世界,如同用一个手套。他在午间休息一会儿,把手套脱下来,放在架子上。手套就在那里增长、扩大,并把整座屋子内部变成一片漆黑。那座变成一片漆黑的屋子走开了,来到春风中间。“大赦,”一个低语在草丛中传开:“大赦。”一个少年随着一条朝着天空倾斜而去的看不见的线奋力疾跑,他那狂野的未来之梦在天空中飞翔如一个比郊区还大的风筝。向更北的地方,你从一座峰顶上能看见松林那无穷无尽的蓝地毯,那里云的阴影静止不动。不,在飞。
慢音乐中,这幢建筑物今天关门。太阳透过窗玻璃挤进来温暖那些强大得足以承受人类命运的写字台的表面。今天我们待在外面,在一个长坡上。很多人穿深色衣服。你可以站在阳光中闭着眼睛感到自己被慢慢吹向前方。我太少下来这海边。但此刻我在这里,在背面安详的大石中间。慢慢向后迁出海浪的大石。
几分钟后,沼泽中那棵低矮的松树顶着它的冠:一块黑暗的破布。但你所见算不了什么相对于它的根茎:分布广泛、秘密蔓延、不朽或半朽的根系。我你他她也伸出枝条。伸出我们的意志之外。伸出大都市之外。一阵骤雨从奶白色的夏日天空里落下。那感觉就像我的五官与另一个生物相连,那生物执拗地运动如同在夜幕降临的体育场里穿着鲜亮运动服的赛跑者。
七月的休息机会,那躺在巨树下的人也躺在巨树上。他把枝条伸入千枝万条。他荡来荡去,他坐在以慢动作向前冲的弹射椅里。那站在码头的人对着海水眯起眼睛。码头比人老得更快。它们腹中有银灰色的木桩和巨砾。眩目的光直接贯穿而入。那在飞驰于发光的海湾的敞舱艇里度过整天的人终将在他那盏蓝灯的阴影里入睡当一个个岛屿像巨蛾爬在灯泡上。
郊区,穿着跟泥土一样颜色的男人从水沟里出来。这是一个过渡性的地方,陷入僵局,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地平线上建筑起重机想一跃而起,但时钟跟它作对。散布在周围的水泥管道用冰冷的舌头舐着光。车身修理厂占据旧牲口棚。石头投下阴影,尖利如月球表面的物体。而这些场所不断变大像用犹大的银子买的那块地:“窑户的一块田,用来埋葬外乡人。”
起重机在建筑中升起楼房的过程,就像时钟的滴答声一样,需要逐步进行。这让我想起了《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故事:犹大出卖耶稣后,祭司给了他三十块银子作为报酬。犹大后来后悔了,把钱还给了祭司。祭司用这些钱买了一块田地,用来埋葬外乡人。这个引语突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郊区并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而是夹在两者之间的社会边缘地带,尤其是外乡人的居所和墓地。
给边境背后的朋友们:
我谨慎地给你们写信,但我不能说的话都充满了像热气球一样膨胀的情感,最终在夜空中飘散。现在我的信在审查官手里,他点亮灯火。在灯光下,我的文字像猴子贴着护栏网跳跃,把它撞得当啷响,还停下来露出牙齿。请领会言外之意吧,我们将在两百年后相见,那时酒店墙上的扩音器将被遗忘——它们终于可以睡觉,变成鹦鹉螺化石。
过街:
冷风袭击着我的眼睛,两三个太阳在泪水的万花筒里舞蹈。当我越过这条如此熟悉的街道时,格陵兰的夏天从雪池照射而来。街道巨大的生命在我周围旋转,它想不起什么,也不欲求什么。在交通下面,在大地深处,未出生的森林静静等待了一千年。我似乎感到街道能看见我。它的视力如此差,就连太阳也是黑色空间里一个灰色线团。但有那么一瞬间我被照亮。它看见我了。
舒伯特风格:
I
在纽约外的一个高处,你一眼就能收尽那些居住着八百万人类生命的楼房。前方那座庞大城市是一团忽隐忽现的漂游物,一个螺旋状银河系。在银河系内部,咖啡杯正被推向桌面另一端,百货商店橱窗在乞求,一大群鞋子不留下任何痕迹。走火通道向上爬,电梯门无声地关闭,防盗门背后传来一阵阵声浪。低头垂肩的身体打着瞌睡,在地铁车厢里,那飞驰的地下墓穴中。我还知道——不需要统计数字——某个房间里有人正在弹奏舒伯特,而对那个人来说此刻这些音符比任何事物都要真实。
II
人类大脑无尽的平原压皱又压皱,直到缩成一个攥着的拳头。四月的燕子准确无误地回到同一个镇子同一座谷仓檐槽下去年的旧巢。她从德兰士瓦飞来,经过赤道,在六星期内飞越两个大陆,准确无误地飞至这个消失在地块中的点。而那个把一生收集来的讯号变成一些颇为普通的和弦让五个弦乐音乐家演奏的人,那个使一条河流穿过针眼的人,是一个来自维也纳的胖嘟嘟青年,朋友们都叫他“蘑菇”,他戴着眼镜睡觉。
每天早晨准时站在高高的写字台前,他开始写乐谱。奇妙的蜈蚣便开始在纸上爬动。
当他沉浸在音乐中时,五件乐器在他的指挥下演奏出美妙的旋律。演奏完毕,他穿过温暖的树林回家,脚下的土地富有弹力,宛如未出生的婴儿般蜷缩着,轻飘飘地朝着未来滚去。突然,他明白植物在思考。
我们必须怎样不加思索地相信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不会突然掉进大地深处?相信一层层积雪会继续黏附在村子的岩壁上。相信未说出的诺言和同意的微笑,相信电报与我们无关,相信内心的利斧不会突然砍起来。相信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的车轴会继续运转在一群群放大三百倍的铁蜂中间。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不真正值得我们相信。
五件弦乐乐器说,我们可以相信一点别的东西,它们还陪着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如同楼梯上的灯泡熄灭了,那只手仍能跟着——相信——那道在黑暗中找到路的盲目栏杆。
我们挤坐在钢琴椅上演奏四手联弹的F小调,同一辆马车两个车夫,有点滑稽。仿佛这些手在把用声音做成的重量移来移去,仿佛我们在移动砝码,努力想改变大天平上那可怕的平衡:快乐与痛苦的重量完全一样。
安妮说:“这音乐充满英雄气息。”她说得没错。但是那些怀着妒意看别人行动的人,那些内心里为自己不是杀人者而鄙视自己的人在这音乐中将找不到自己。而那些买卖别人和那些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买的人在这里将找不到自己。不是他们的音乐。这首在其所有时而闪亮时而温柔时而粗犷时而豪迈时而是蜗牛痕迹时而是钢线的变奏中完整保存自己的漫长乐曲。这执拗的哼唱声,此刻它与我们一起升入深处。
打电话回家我们的通话外溢,进入黑暗中。在农村与城市之间闪耀,像刀战那样一团混乱。之后,我整夜神经过敏,躺在酒店床上度过。我梦见自己是一根罗盘针,某个定向越野比赛者带着它穿过森林,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来自79年3月厌倦于所有那些只有文字、文字而没有语言的人,我到那白雪覆盖的岛上去。荒野没有文字。空白的书页从四面八方摊开!我在雪中遇见小鹿的蹄迹。
语言但没有文字。
火车站列车驶进来。一节节车厢停下,但门都没开,也没人下车或上车。是根本找不到门吗?车厢里拥挤着被锁在里面的人,他们前后走动。他们从静止的车窗里向外望。外面一个男子带着一把锤子沿着列车走。他敲打车轮,车轮微鸣。除了这里!这里鸣响难以理解地膨胀:如霹雳,如教堂打钟,如绕地球一圈的回声,把整列火车和邻近的湿石都掀起来。
一切都在歌唱。你会记住这一刻。继续前进!
黑色明信片
I
日历满满的,但未来一片空白。电缆哼着某个被遗忘的国家的民歌。雪落在铅一般静止的大海上。阴影在码头上挣扎。
II
在人生中途,死亡来测量你。这次到访被遗忘,生活继续。但那套衣服已在悄悄缝制中。排钟女老板瞧不起客人,因为他们想住她那邋遢的旅馆。我住的是二楼角落里那个房间:一张寒酸的床,天花板一个灯泡。沉重的窗帘里有二十五万只尘蟎在行军。外面,一条行人街,有缓慢的游客,赶路的学童,踏着喀嚓响自行车的穿工作服男人。那些以为自己在使地球转动的人和那些以为他们在地球控制下无助地转动的人。一条我们大家都走的街,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房间唯一的窗口面对别的东西:狂野的集市广场,沸腾的场地,颤悠悠的宽阔表面,有时候拥挤,有时候空无一人。我内心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变成现实,所有的恐怖,所有期待。所有那些不可设想然而将会发生的事情。我的海滩很低,死亡升起六寸就会把我淹没。我是马克西米连。这是一四八八年。我被囚禁在布鲁日因为我的敌人优柔寡断——他们是懦弱的理想主义者而他们在恐怖的后院所做的事我不能描述,我不能把血变成墨。我也是那个踏着喀嚓响自行车的穿工作服男人。我还是那个被人看见在闲逛的游客,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让他的目光在旧油画那些苍白的月色脸孔上和汹涌的衣纹上流连。没有人决定我去哪里,尤其是我,虽然每一步都在它必须踏着的地方。在石化了的战争中到处闲荡,那里所有人都刀枪不入因为所有人都是死人!一堆堆满是尘埃的落叶,一堵堵有小孔的墙,一条条花园小径,在那里石化了的泪花在脚底下窸窣作响。意想不到地,仿佛我踏上了地雷拉发线,那座无名塔楼响起钟声。
排钟!布袋沿着缝合口裂开,乐钟回荡在整个佛兰德。
排钟!乐钟咕咕叫的铁、赞美诗和流行曲融于一炉,颤悠悠地写在空中。那个颤手的医生写出一帖没人看得懂的处方,但他的字迹将被认出......在草地和房屋上空,收获和市场上空,在机敏者和死者上空,排钟齐鸣。基督和反基督,分不清谁是谁!乐钟终于用它们的翅膀把我们驮回家。钟声停止了。我回到旅馆房间里:床、灯、窗帘。有奇怪的响声,地窖正吃力地上楼。我躺在床上,两臂摊开。我是一个锚,把自己往深处下,牢牢地稳住在那里漂浮着的巨大阴影......
那是伟大的未知,而我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显然它比我更重要。外面的通道就是那条街,我的脚步在那里消逝,连同写下的文字、我给寂静作的序和我那里面朝外的赞美诗。
—————
* “排钟”又可译作“组钟”。
* 马克西米连,指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德意志国王(1486—1519)。
弗美尔
这不是受保护的世界。噪音从墙另一边的小旅馆传来,笑声、争吵声、一排排牙齿、泪水、钟声,还有精神失常的大舅子,那人人心寒的死亡信使。巨大的爆炸,迟到的急救人员,运河上显眼的船只,偷偷进了口袋、进错了口袋的钱,一个又一个催逼堆积着,张大口的红花,花尖渗出对战争的预感的汗珠。然后从那里直接穿过墙,就是明亮的画室,和那些继续活上千百年的分秒。那些用了诸如《音乐课》或《读信的蓝衣女人》之类标题的油画。她怀孕八个月,两个心脏在她体内跳动。她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起皱的《未知世界》地图。轻轻呼吸。一种不知名的蓝材料被钉在椅子上。金头钉以天文速度飞入正好停在那里,仿佛它们一直是静止的。耳朵嗡嗡响,带着深度或高度。那是来自墙另一边的压力,使事实飘浮,使笔触坚实的压力。穿过墙会受伤,这令人讨厌,但我们没有选择。世界是一体。至于墙......墙是你的一部分。你要么知道这点要么不知道,但对大家来说都一样,除了小孩。小孩不存在墙。明亮的天空已经斜靠着墙。好像在向空虚祈祷。而空虚向我们转过脸低语:“我不是空虚,我是开放。”
———
* 小旅馆:弗美尔父亲遗下的小旅馆。
* 大舅子:弗美尔与母亲、岳母和大舅子,还有妻子和一大群孩子,一起住在一座三层大屋里,小旅馆也是大屋的一部分。
* 战争:荷兰从1665年开始,与众多敌人进行断断续续的战争。
* 爆炸:弗美尔一生居住的荷兰城市德尔夫特曾于1654年10月12日发生火药库大爆炸,该城市几乎全部被毁。一百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 “她怀孕八个月......”指《读信的蓝衣女人》。
* “一种不知名的蓝材料被钉在椅子上......”指蓝衣女人身旁一张椅子上用金头钉钉着一块蓝色织物,似是作为坐垫。
罗马式拱形
游客成群挤进这座庞大罗马式教堂的半黑暗里。一个拱顶通向另一个拱顶,看不到远景。几柱烛火闪忽着。一个看不清面孔的天使拥抱我他的低语贯穿我全身:“不要为自己是人类而羞耻,要自豪!
你内部一个拱顶通向另一个拱顶,无穷尽地。
你永远不会圆满,因为本来就该这样。”
在1882年底至1883年初,李斯特探访女儿科西玛和女婿理查德·瓦格纳。几个月后,瓦格纳逝世。李斯特在那时谱写了两首钢琴曲,题为《悲伤的凤尾船》。——作者原注
* 李斯特两首钢琴曲,又可以视作一首两个版本,第二个版本称为第二号。又译作《悲伤的船歌》、《凄凉的威尼斯船》等。
* 《帕西发尔》(1882)为瓦格纳歌剧,在瓦格纳逝世半年后首演。
* 索斯皮里,意大利语,意即叹息。
书目:
1.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诗选1954—1986》,罗伯特·哈斯编,艾科出版社,1987。从众多著名译者和译本中挑选编辑而成,有些是经过编者与译者的再商量和考虑之后重新修订的。
2. 《半完成的天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最佳诗作》,罗伯特·勃莱译,灰狼出版社,2001。勃莱译本的精选。
3. 《被删除的世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著,罗宾·罗伯逊译本,埃尼塔尔蒙出版社,2006。这是一个改写本,即改写别人的译本,尤其是罗伯特·富尔顿的译本,曾遭富尔顿质疑。
4. 《巨大的谜:诗集新汇编》,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著,罗伯特·富尔顿译,新方向出版社,2006。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拥有创造意象的奇异天赋,他运用意象似乎毫不费力。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他诗中感到辽阔的空间,也许是因为每首诗中那四、五个主要意象往往来自心灵中分布广泛的不同源头。他的诗有点像一个火车站,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驶来的火车都在同一个火车站小停。一列火车的底盘可能沾着若干俄罗斯的雪,另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可能摆着鲜花,车厢顶上可能落着一层鲁尔的煤烟。这些诗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诗中意象行驶了漫长的路程才抵达那里。马拉美相信诗中必须有神秘,并促请诗人们在必要时删去诗中那些与真实世界的场合建立联系的东西,以获得神秘性。
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中,与真实世界的场合建立的联系被固执地保留着,然而神秘性和惊奇感却不减,即使反覆阅读多次也依然如此。里尔克曾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诗人是“看不见的事物的蜂”。用看不见的事物造蜜,意味着艺术家依然紧贴着尘世的历史,但又朝着精神性和看不见事物的方向运动。作为一个艺术家,特朗斯特罗姆似乎受到这类努力的鼓舞,以及受到做同类努力的其他欧洲诗人竖立的树样的鼓舞。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是某个文化的好诗有能力旅行并抵达另一个文化的光辉榜样。如同特朗斯特罗姆在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匈牙利杂志《新作品》的一封致匈牙利诗人的信中所说的:“诗歌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优势......诗歌不需要拖着沉重的、容易受损的仪器到处走。”托马斯以好玩的态度写科技。他曾说,当他在五十年代初开始写作时,似乎仍有可能写一首不涉及科技的自然诗。如今,他说,科技创造的众多物件已几乎变成自然的一部分;而瑞典拥有高度发达的科技这个事实,则总是能够在他的近期诗作中看到。他既不排斥科技,也不让科技主宰诗。
瑞典社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它作为一个福利社会,事实上它是最完善的福利社会;它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个既有决心又有财富去断绝贫困的社会。但它也是一个与美国相似的科技社会,又是一个服膺世俗解决方案的社会。特朗斯特罗姆曾说,在瑞典,要与某种温柔的东西保持联系是何等的困难。美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罗伯特·勃莱是特朗斯特罗姆在英语世界的主要推介者。以上文字摘译自勃莱为他翻译的《半完成的天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最佳诗选》所写的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