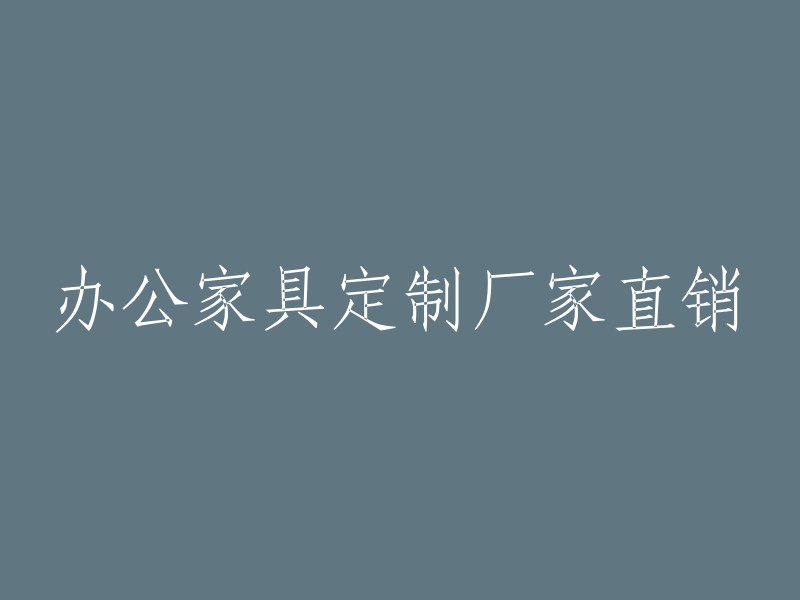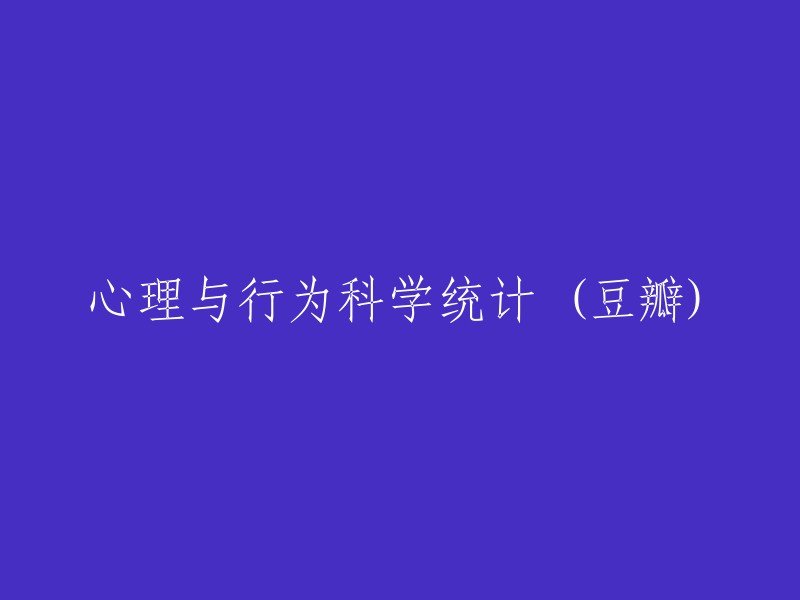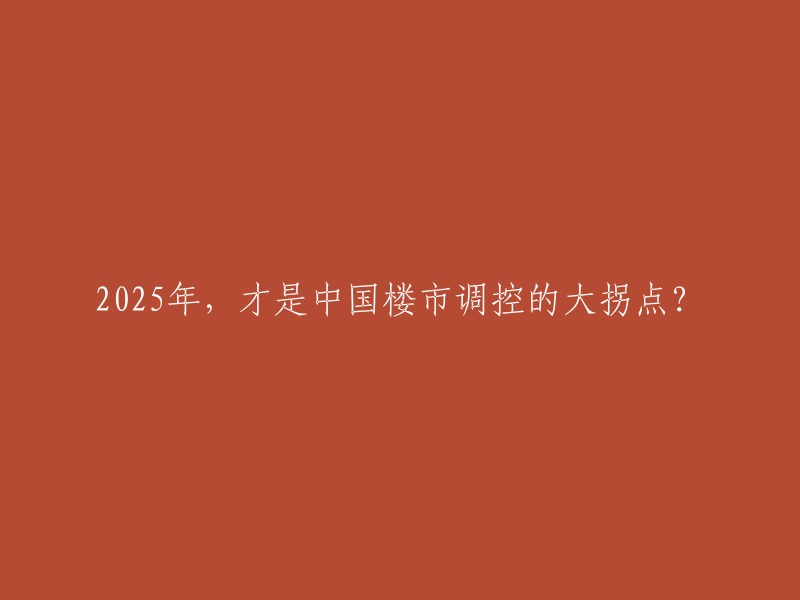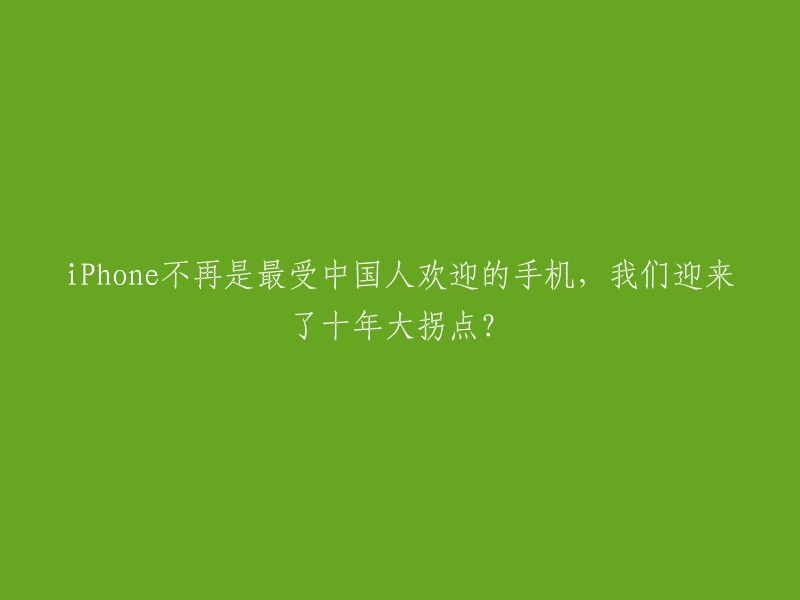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一位专程拄着手杖来到北京参加《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首发活动的瑞典诗人,在参加完北大的朗诵暨研讨会和瑞典使馆的酒会后,匆匆南下昆明。他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开了一家名为“特朗斯特罗姆画廊/酒吧”的场所。诗人从云南归来后,我们问他观感如何。特朗斯特罗姆夫人莫尼卡代他回答说,最大的收获是买了好几种白酒,因为他们现在每顿饭都离不开中国的高度数烈性酒了,在瑞典喝的伏特加可没这么来劲。为了追求形式的完美,他们还专门买了一套酒杯,就是餐馆里最常见的那种八钱小玻璃盅。与此同时,白发稀疏纷乱、面部线条分明的诗人用澄蓝色的目光注视着大家,流露出几分孩子般的欢快与得意。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一刻,我似乎获得了一个描述和理解这位来自波罗的海的艺术大师的角度:较之一个身怀绝技的外来和尚,他倒更像是一个与杯中物达成默契的饮者(隐者),一个行事疏放的盛唐诗人。作为饮者,他寻求隔绝外物的醉意;而在诗人眼中,这醉意乃是深层的迷醉,是祛除杂质、帮助他与自然和真实建立直接而紧密联系的捷径。特朗斯特罗姆有一首名为《孤独》的诗,写他所经历的一场幸免于难的车祸,在一阵非常具体的惊险、紧张、恐惧过后,他发现自己“仍系着安全带坐着/等待有人冒着风雪/看我是否安然无事”,灵魂出窍般的强烈的疏离感盖过了先前的那些感受;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诗的迷醉吧。
然而,假如他听凭一首诗止于迷醉,那托马斯就不是当今欧洲硕果仅存的诗歌大师之一的托马斯了。他在阐述自己的诗歌主张时曾说:“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息情绪’就完了。”就在这酒醒之后艰苦而漫长的劳作当中,迷醉逐渐让位于清醒、冷峻的刀砍斧削。还是同一首《孤独》,诗人接下来笔锋一转,用短促的语句和纷乱的语气描述起人类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来,然后不失时机地决然断言:孤独——无所作为——是一种必需的自我洁净的选择(一种隐约可辨的道家哲学);结尾处一句简洁的、具有巨大穿透力的“所有人都在对方那里排队”则创造出一种“惊悚”效果,使所有传达类似思想的诗句都黯然失色。
您好!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构筑了一个神秘而广大的世界:它首先不是一个情感或情绪的世界,也不仅仅是一个意义的世界;它同时也是一个模拟上帝头脑的意象世界,其中不乏造物的欣喜,冷眼观世的厌倦和鄙夷,甚至施惩罚的冷酷。当他写下“二月,活着的静静站立/鸟懒得飞翔,灵魂/磨着风景,像船/擦停靠的渡口”(《脸对着脸》),他是在用令人震惊的意象直指“偷挤宇宙的奶苟活”(《火的涂写》)的人类生存本质,从而进行严肃的拷问。在左翼思潮冲击下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瑞典诗坛,曾经有过一股讨伐特朗斯特罗姆的浪潮,激进的年轻诗人批评他的纯诗写作专注于个人世界而与社会格格不入;但十年之后,其中的一位专门写忏悔书向他致歉。我猜测,也许这位勇敢的诗人沉下心来,在托马斯的诗中读到了比他期许中更为广阔、丰赡的东西吧 。
特朗斯特罗姆说:“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这句话对于任何一个想在诗歌道路上走得更远的青年人来说,都是一句至理名言。雄辩并不一定是思维的子裔,但绝对是放纵宣泄的近亲,弃之并不足惜。这番话还解释了诗人的大多数作品何以均这样短小、凝练。据《诗全集》译者李笠介绍,特朗斯特罗姆1990年中风导致右半身瘫痪后,写作日益困难,所以近年所写都是俳句。想一想也不意外,用俳句写禅意、写机锋,隐者/饮者特朗斯特罗姆倒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给特朗斯特罗姆斟酒时,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谈笑风生。突然间,托马斯敏捷地捂住杯口,高叫道:“噢!”——原来诗人已经喝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