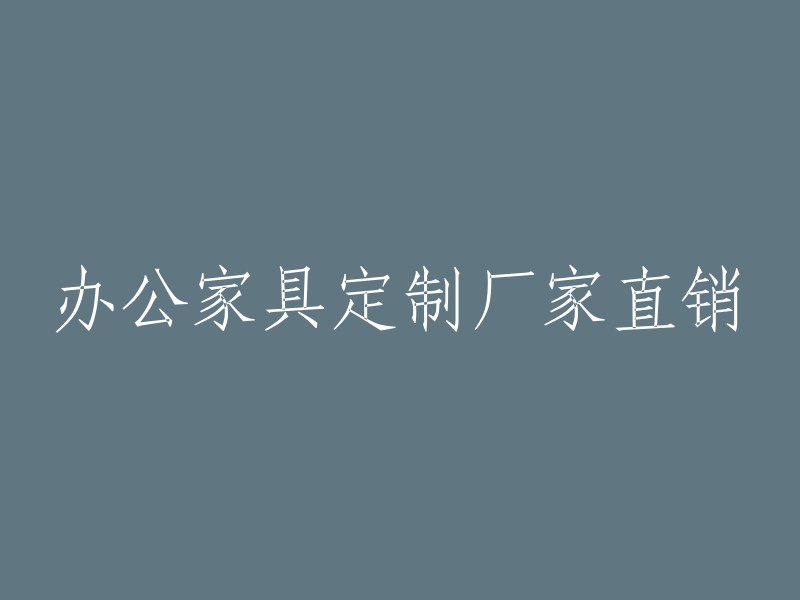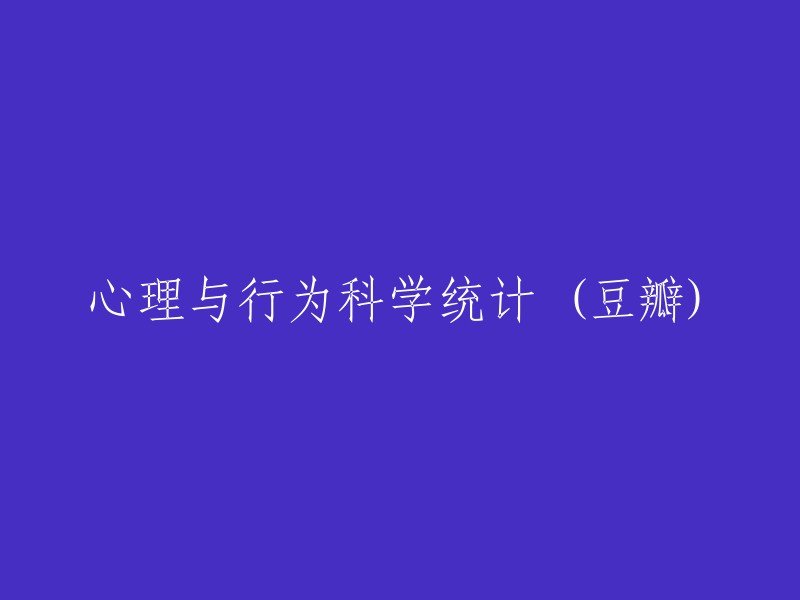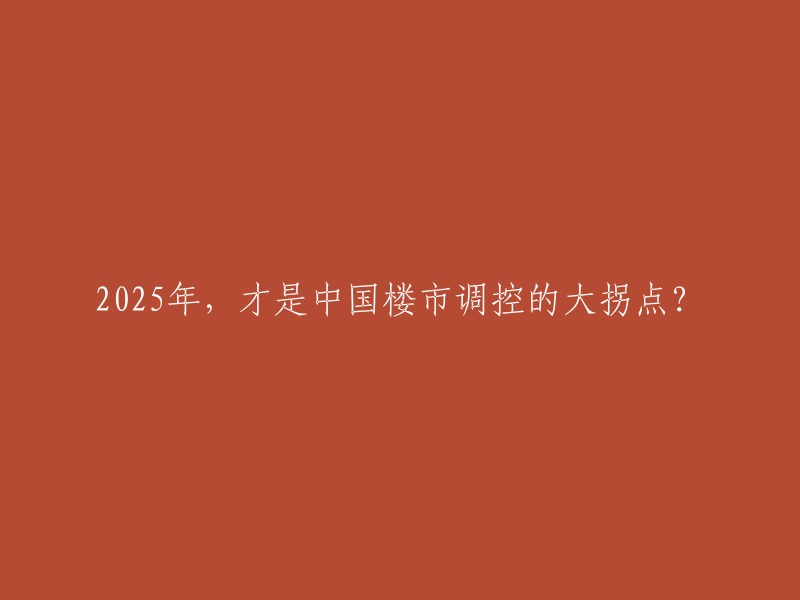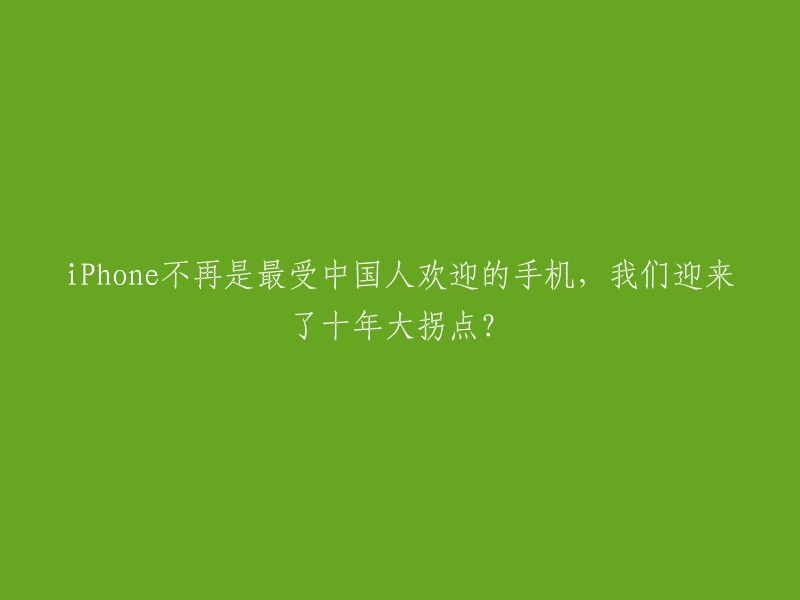忽然十年便过去,阿妙被束在座位上动弹不得。拥上来的小学生清一色蓝白校服,密密麻麻。小胖子的冰欺凌滴到胡子女孩的辫子上,眼镜小弟的辣条戳上发夹阿妹的书包,谁咯嘣嚼着干脆面猛地打个喷嚏呛得一圈小孩尖叫,大力推搡。“别挤!”“不是我!”“踩得很舒服啊!”
所以,每个下午掐秒表冲向站台、一猛子扎进公车不是没原因、能与附近小学的放学时间错开真叫谢天谢地。今天办公室全体被主任滞住训话,你看,这才十分钟功夫......
“注意点我帽子!”小胖墩脾气不小,护着一个袋子,反头剜一眼小胡子女孩。女孩毛发旺盛,眉毛睫毛胡子浓厚,却生得一副委屈相。被身后的人挤得快哭出来,瘪瘪嘴没说话。
“叫你别挤!羽毛压弯了!”新一轮的推搡令胖墩很光火。掏出帽子,小心地捋笔挺的羽毛。
“又不是我......”女孩也很生气,碍于体型差距不敢发作。
“明天我们管乐队要戴礼貌,挤坏了你赔吗!”
“明天又不升旗。”
反了!胖墩见女孩竟敢顶嘴质疑,眼眶瞪成铜钱。“我们管乐队又不是只有升旗才会奏乐!明天有外宾来,有外国人你懂不懂!我们还要穿制服!”边说边猛推,女孩个子小,被埋入人群拔不出来。
“师傅,永宁路停一下。”阿妙喊。
小胖墩回头,鸡贼地挪过来。没等阿妙起身,屁股不客气地蹭往座位一半。瞅他土财主的德行挺来气,阿妙一扭腰将他扫下去,把嵌在人群里的女孩使劲拎过来,“坐。”拍拍手下了车。
夜幕倾到超市后边,路边的烧烤摊如往常一样支起臭豆腐架。每个傍晚都令阿妙轻松,她大步朝前走。
“爱管闲事,缺心眼儿,没变啊。”
阿妙回头,撞见一张陌生男人的脸。微隆的肚子,手揣在夹克兜里,胡揸下巴,一脸严肃。
“我是小岳。”
阿妙立马弹开,眯起眼睛打量,在对方隆起的肚子上多停了几秒。
“王柏岳。”他闲踱上前,“以前住一个院儿,算起来咱俩还青梅竹马。”
“知道了。”阿妙撇撇嘴立马打断。
“招呼也不想跟我打,上哪儿去?”王柏岳饶有兴趣,“刚在公车上那个就瞅你眼熟。”
“......那个,见到你挺高兴的。我有急事,咱们交换下电话号码,有时间再联系行不。”
“你不像‘挺高兴’的样子。”
“......真有急事。”
几秒的僵持,对方呵呵笑起来,“来,号码拿好,有空叫我出来喝茶。”挥挥手朝反方向离开了。
阿妙松一口气。
王柏岳怎么会不认识她,他们可是从小学一路走到初中的同学。太可笑了,曾经那个面目可憎的家伙,竟然一上来就自称“小岳”,真是鬼跟你这么熟过。
此人的确跟自己住一个院儿,但父母交恶,两家小孩素以仇人相待。王柏岳个性顽劣,不论在院子还是在班里都是霸王,阿妙没少被欺负。五年级一次调座位,他坐最后一排,阿妙专门挑了离他最远的教室对角线位置,结果他举手,斜嘴笑,“老师我成绩差,让林家妙跟我坐同桌吧我要她帮助我。”阿妙死活不肯,老师皱眉头责怪她缺乏团结友爱精神。协调的结果是她勉强做到他前头。还记得自己抱着书包,穿越同学们的注目礼,沿黑板和走道走向倒数第二排,一脸悲壮。后来,揪住她辫子吼她拿作业过来给他抄,突然在起立时踢走凳子听她扑通掉落在地上惹全班发笑,去厕所抽烟的邀几个混混打趣她要不要来一根,这种事一天不知发生多少次。
不过自己刚刚是不是奇怪了点?大家都是成年人,谁会记得那些事,他又不会吃了自己。
“一共十七块五。”药店店员递来袋子。
“哦。”她回过神,低头翻兜里的钱,走出店门。
也没什么可惜,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与旧同学重逢。鸡犬升天的只懂显摆,转身被众人一齐嫌恶;江河日下的只能恭听,完了聚在一块儿嚼人舌根——这几是多年参加同学会了解到的真相。当然,外貌这东西能经受岁月洗礼的更是少数。彼时大家风华正茂,一转眼十年,七弯八路各自残。瞧王柏岳刚刚的模样就知道了。
“是不是拿错了?”数数袋子里的药,一盒健胃消食片一瓶眼药水,但眼药水不是妈妈要的那种。只好折回店,“好像弄错了,我要的是治沙眼的,不是防近视的。”
“剩最后一瓶,那个人拿了。”
阿妙转个头,顿时傻眼。
“你不是有急事要办吗?”
“......”
“这么快办完了。”
“啊是。”阿妙走着,把袋子装进包,砖头掩饰尴尬。“你沙眼?”
“我妈。”
“我也沙眼,感染的。嘱咐她别吃辛辣食物,不要经常揉眼睛。”顿了顿,“阿姨这些年还好吗?”
阿妙点点头。
不是反方向告别了吗,怎么还能遇到!哪怕这城市修再多环形路,也不能这么跟自己开玩笑啊......只好硬着头皮同对方“顺便散步回家”。也不知道这路“顺”到哪里,最好下个路口就是他家。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那年搬走,就来西城区了?”对方问。
“是啊。”
“城市这么大,挺难遇着的。”
“嗯。”阿妙心想,您下一句千万别归结真有缘分。
“真有缘分。十年没见了吧,在哪儿发财?”
阿妙冷笑,“我像能发财的人吗?”
“也是,不发财,就光顾着发福。”阿妙皱着眉头说。
“发福?!”王柏岳转头用凶光看着她,“我忍着没说你呢,看看你那肚子......”
“男人在外面应酬,难免的,女孩子家就不应该。我记得你小时候挺瘦的。”阿妙试图转移话题。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挺俊的呢!”说完阿妙差点跳起来扇自己嘴巴了,严防死守最后竟然莫名其妙丢出一句夸赞,真叫一个功力入门级。幸好他没有就这个话题深入,只是轻笑两声。
“我们家当年是逃荒还是讨债,走了也不知会一声。大家一个院子的,总归比外面人感情深,日后有困难大伙也能互相拉一把。”王柏岳继续说。
“奇怪,我们平凡人家过平凡日子,能有什么困难。不过你说得也对,谢谢你。”阿妙决定以不变应万变。既不打算透露自己确切信息,也不询问对方情况,只求快点结束这段路。
王柏岳也没再问,双方沉默地走着。隔壁小区的黑色雕花护栏投下影子,和树影拓在四方砖上,月光皎白。
路灯下,他指着翻垃圾桶的灰狗说:“这狗跟小浑蛋有点像。”
“不是我弄死的。”阿妙脱口而出。
小灰狗是她捡的土狗,脏兮兮,瘦骨嶙峋。小孩子哪管品种,喂了就生感情。王柏岳当它是宝,家里不让进就放养在院子里。院儿里有个比阿妙大不到一个月的女孩,很胖,算是姐姐但动不动就哭,外号小泥巴。有天放学,两人远远看到他们又在吹口哨训练狗,特意绕开。谁知,那狗朝这边笔直冲来。小泥巴“哇!”地大哭,朝前跑。阿妙也慌了。她叫小泥巴别跑,狗爱追运动的东西。小泥巴没停,狗果真朝她扑去了。阿妙见墙上靠着单位修窗子剩的金属管子,拽来就朝狗扔。食堂正炒菜的师傅冲出来,抄起铁锹拍上去了。
王柏岳他们赶过来,见小浑蛋倒在血泊中,傻了眼。有个大脑门的家伙跟王柏岳玩最铁,人称瘦猴儿,他朝阿妙瞪圆眼睛,“你把狗都咬死啦?”
阿妙瞟了眼王柏岳,竟在吧嗒吧嗒掉眼泪。他知道他心疼他的狗。果然,他走上前,“啪!”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扇了她一巴掌。恶狠狠一字一顿,“你死了吗?残了吗?没咬你,以后少管闲事。”
这一巴掌,阿妙现在想象还咬牙切齿。
接着他说:“我是想吓唬小泥巴。”
“吓唬他?!”既然提起往事,阿妙也懒得跟他客气,“小泥巴那么弱小你干吗吓她?她很自卑,什么都怕。你真是从小就缺德!”
“你打小就缺心眼儿。”
“你!”
阿妙在心里嘀咕:“原来她心机这么重呢。感情你是为了给我出气,牺牲了爱犬。”
“编些烂理由把自己从前的险恶行径推卸到一个不在场的人身上,所以我说你缺德了。”阿妙嘀咕道。
“你除了蠢,再加一条不知好歹。”立领夹克男子回应道。
“......当初一巴掌还没找你算账。”阿妙有些不服气地说。
“年少轻狂嘛,行事冲动。谁没个过去。”男子安慰道。
“是是,谁都有个过去,只是吃亏的一方比较记得。”阿妙哼了一声。
“又不是没跟你道过歉。”男子又说。
他道过歉?阿妙在脑子中搜索半天未果,狐疑地瞟了眼旁边的立领夹克男子。
“汽水那件事。”经他提醒,她终于想起关于汽水的回忆。
巴掌事件之后不晓得第几天,一个热得叫人发晕的下午,刚上完体育课,同学们叫苦连天。下一堂是班主任的数学,阿妙趴在桌子上,脸贴着稍微凉一点的木头桌面休息。有人敲她桌子,“想喝汽水吗?”是瘦猴儿。那伙人又想搞什么?她不愿搭理,脑袋翻过去。“岳哥派我问你喝不喝汽水。”还是不回答。对方没好气地猛拍下桌子,走向后排。不一会儿上课铃响了,起立,老师好,坐下。
“下面同学们把课本翻到......”老师讲课的声音传来。
“报告!”大家停下手里的书,齐刷刷朝门口瞧。王柏岳站在门口,上气不接下气,身板笔挺,胸脯和肚子撅得高高的。一件墨绿的T恤,皱巴巴地耷拉在身上。他手里握着直冒冷气的玻璃瓶,里头细心地插着根儿吸管。男生是不会用吸管喝的。老师问那是什么。他说橘子汽水。老师说“你滚到走廊去喝”。他就乖乖地出去罚站了。阿妙自己也惊奇,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他跑下去给阿妙买汽水。他站在门口,红色门框只切到他汗涔涔的鬓角和因喘气而翕动的鼻梁。外面太阳正晃眼,金光一片。
下了课,他走进来,经过阿妙座位时把汽水随手搁在她桌上。此时,她正给四周同学分糖果,那是爸爸去亲戚家吃喜酒带回来的。他从后面大力踢了下她凳子,阿妙不情愿地往后靠一下表示回应。
“每个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他不做声,继续伸长胳膊递给更前面的同学。
“每个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凳子又被踢了下,这回她差点从上面跌下来。她站起来,把书包里剩下的糖全抓起来,转身放到王柏岳桌上。
王柏岳抓起糖果一把扔到她身上,“我才不要你的。”大家都愣了。理所当然,放学后,那瓶莫名其妙的汽水也被阿妙砸进了垃圾桶。
“你那叫道歉?”阿妙笑起来,“对不起好好说不就行了,怎么会有你这种别扭的人。”
“大家都很幼稚。”男子安慰道。
“哈哈,幼稚的事不止一件。”阿妙说着,心里却有些感慨。
“是的。我知道,每当你觉得自己在某个时期变得更漂亮、瘦了或白了,你就会去拍登记照。现在你的抽屉里肯定已经积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照片。”
“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你暗恋班长的时候,每个星期六吃过午饭就骑自行车,顶着大太阳在他家所在的那条街上闲逛,试图见到他。至少坚持了一个学期。”
“哎呀!”阿妙笑着推了王柏岳一下肩膀。
这些从未向他人诉说的心事,他怎么会知道。看来她比较倒霉,偷偷怀上孩子竟然被敌人在暗处窥见。王柏岳当时肯定在心里嘲笑了自己无数遍。然而,如果不是他今天提起这件事,这么多年她可能早就忘记了。
“前面那栋楼,二楼左边亮灯的就是我前女友家。”王柏岳指着宠物店对面的一排粉红色楼房,“我前女友家。”
“罪过罪过,说到你的伤心事了。”
“大男人会在乎这些?”王柏岳哈哈大笑,“说说你自己吧,当时为什么要搬家?”
“我父母离婚了。我妈觉得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就带着我偷偷搬了出来。刚开始搬过来的两年挺艰难的。每天凌晨四点多起床,穿着白大褂扫大街,沙眼就是那时候得的。后来慢慢地好起来,她开了一家米酒铺,我也找到了工作。”
“原来是这样......你妈妈真不容易。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环保局。谈不上好坏,混日子呗。”阿妙抬起头伸了个懒腰,“我刚毕业两年,工资不高。你也知道现在都是合约制,没有编制和铁饭碗。上厕所都要说‘在路上’。”
“哈哈,你可以试试考公务员。”
“哎呀,怎么跟我妈一模一样!这半年,她老催促我考公务员,非要叫我考。她说考了就稳定了,考了她就放心了。我说‘娘亲啊,你不知道现在的世道,考上公务员的概率是多少你知道吗?况且,天黑路滑,人生复杂!你拼得过人家的卷面分吗?拼得过人家的社会人脉吗?再者,我一没管理天赋二没从政兴趣,叫我考公务员,简直比要我找男朋友还难’。”
“个人问题还没解决?”
“我是困难户。”
王柏岳笑着,面目慈祥和善。阿妙看着他其实也没变多少,除了下巴上多出来的肉,眉眼依然是那副眉眼。失去了少年人的锐气,被一股宽容之气包围着,也还过得去。
“我家到了。”阿妙指了指身后的米酒铺子,“我们去坐一会儿吧。”王柏岳点点头。
“妈!”阿妙把系着围裙的母亲拉了过来,“你猜这是谁!”
即使刚从油烟中把她拉过来,阿妙的母亲看起来依然干净利落。头发扎到脑后,额头光亮。
“小岳来了。”
“妈!您什么火眼金睛啊,长这么胖你也认识!”
王柏岳向她问好,她笑着点头回应。他们被引到靠里的桌子旁,“我先去忙了,有什么想吃的跟阿妙说。”
店里的棕红餐具整齐摆放,显得沉稳悦目。客人们来来往往,阿妙的母亲和一个伙计端着盘子在穿梭。
“百合米酒、桂花米酒、糊汤米酒、银耳米酒,你要哪一种?”阿妙问道。
“我要吃饭。”王柏岳回答。
“噢,我也饿了。”阿妙叫来伙计。
“今天遇见你挺开心的。”阿妙笑嘻嘻地朝对面的人说,“你也住西城区?工作?”
“算是吧,在这边干了有半年了。我们跑销售的,没固定地方。”
“你卖什么?”
“按摩器。我不负责卖,我负责一边组织职员去联络按摩器公司,一边派人向单位和个人推销。相当于一个中介......哎,说了你也不懂。”
“拉皮条还拉出道理来了。自己吃自己的饭”阿妙低头扒几口。
“你个人问题真没解决?”王柏岳似笑非笑。
“干吗呀。”
“跟你讲,我给你写过情书。”
阿妙往后靠,歪脑袋瞅他,“这又是哪一出,我不记得。”
“初一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初三的满脸痘的家伙给你递过情书?就是那个。那时他是我和瘦猴儿的头,学校抗槽的,我们谁都不敢惹他。哪只他看上了你,非逼着同班的我和瘦猴儿给构思。没辙,之后由我起草,右瘦猴儿传送。”他扬扬筷子。“文笔不错吧。”
“少恶心了。什么‘我们的回忆像薰衣草,在空气中留下淡紫的余香......’我又不认识他,哪儿来的回忆。”
“所以说,是你和我的回忆,不是你和他的回忆。”
“哈哈,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阿妙觉得这个夜晚太神奇了,其余的364天哪一天都比不上。年少的搓人搓事,一件一件拾起来,只觉得可爱。想到自己眼下的生活,不算一团糟,但也平淡空乏。“我有一个男朋友,一年前分手了,现在回来找我复合。另外有个男同事,对我挺好的,油嘴滑舌我也不知该不该信他。两个都说喜欢我。”
“一个女孩儿开始问‘该选谁’,表示她哪个都不中意,你觉得对吗。”王柏岳问道。
“说说那些人吧,像......小泥巴,还住在院子里吗?”阿妙想起小时候没有朋友的日子,对小泥巴还是有感情的。胖姑娘一方面怯懦,一方面却管不住嘴,总是讲人坏话招人嫌。为了保护小泥巴,阿妙额外受了许多苦。
“她后来长漂亮了,精明又会来事儿,去深圳当歌手。再后来,在高级夜场做领班了。”王柏岳继续说。
“那是个什么意思?”阿妙好奇地问。
他起身,走到前面和阿妙母亲道别。
“阿姨,别累着自己。我跟你讲,您怎么对待身体,身体就怎么对待您。所以没事儿您就和广场的阿姨们跳跳舞什么的,别老顾着生意。钱嘛,总是赚不完。”
她微笑看着眼前的人,末了,扬扬头让阿妙送他。
“干吗呀,跟我妈叔那些。”
“最幸苦就是你妈了,我瞅着心疼。”
两人在街边并排站着,沉默了小会儿。阿妙感觉今天夜里的空气比往常好多了,神清气爽。
“上小学,上初中,每天背着书包上楼,看着墙壁上抠得乱七八糟的灰、刻得稀烂的字;每天午睡的时候听见楼下叔叔篮球咋滴的砰砰声;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在阳台写作业,楼上小泥巴的妈妈经过我家和我妈一起打毛衣说会儿话再回家做晚饭。”阿妙并腿蹦到矮石阶上,又下来,“我那时候心想,日子怎么没有尽头啊,又长又难挨啊,以为我会永远这么过下去。”
“不知不觉一切都变了。”
“想起来还是不知道怎么发生的。我爸妈离婚的时候,我满脑子只想着离家出走。提了书包,去车站晃悠,每次都没走成。以至于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阿妙转过脸,若有所思地对他说,“成长起码有一个好处。想去任何地方的时候,你能掏出一张车票钱。”
“所以听你妈的话,考公务员吧。”
阿妙翻个白眼,“跟你交流有困难,我对那玩意儿没兴趣。我的意思是......”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作家不能等有了灵感再创作,学生不能等有了状态才学习’。这告诉我们任何事都勉强得来,贵在一个坚持。话糙理不糙,你这么大了,应该懂你妈的苦心。”
阿妙哑然。
“时间不早了,快回去给你妈帮忙。”王柏岳笑着拍拍她的头。
你变这么懂事,我快不认识你了,也不知道这十年都受了些什么苦。阿妙想说什么又没说,只是咕哝一句“知道了”。
眼前这个人早不是从前的顽劣恶少了,走在她前头好多步。
走回铺子,阿妙擦起桌子。她母亲抓过抹布,说“不用了,你上楼烧开水把暖壶满上。”
阿妙撑着桌子,歪头看母亲来来去去的背影。她想起自己上初二的那年,除夕夜里,她和母亲吃完年夜饭早早躺在同一个被窝里头。爸爸那年称工作忙,已是第三年没回家。阿妙倒觉得没什么,因为自小和他接触甚少,感情浅。
一个早年看过的电影结尾了,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十几岁的女孩半夜蹭上母亲的床,对着黑漆漆的天花板说:“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她妈妈翻了个身,迷迷糊糊的声音答:“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她听到窗外烟花爆响,嫌时间太早,向母亲提议说能不能先去外面和大家放会儿烟花再回来。母亲不说话。阿妙气坏了,心想玩一会儿都不准,不可理喻。牛头盯着母亲近在咫尺的脸,紧闭的眼和唇、紧锁的眉头,愤愤地入睡。
那一晚,是母亲肚子承受父亲抛弃他们的消息,不忍心告诉她的一晚。阿妙不知道母亲那个晚上睡着过没有。
“妈,这么多年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母亲掂了掂抹布,走去放水桶的角落,没理她。
“我决定考公务员。”
母亲还是没应声,把抹布晾到外面的横梁上,走回来瞧见愣在远处的阿妙。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光说呀,还不快上楼看书。”
阿妙朝她粲然一笑,显得更加懂得人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