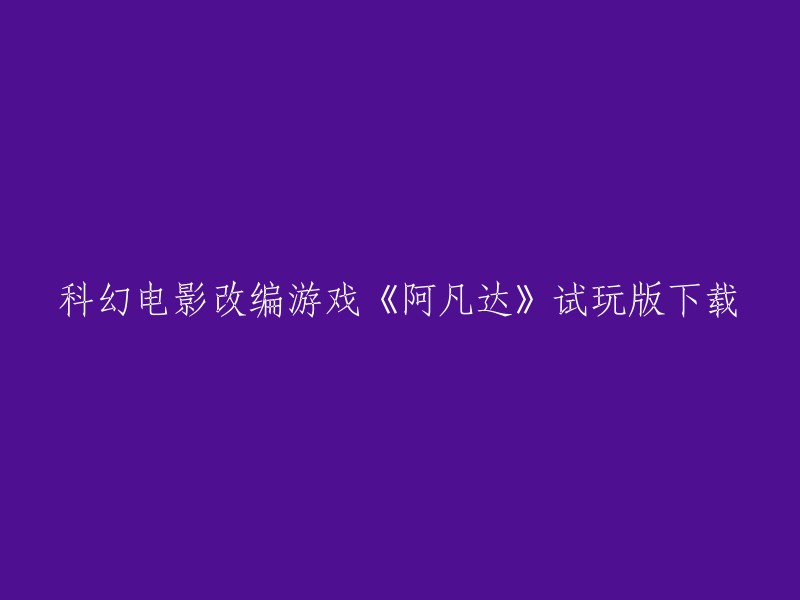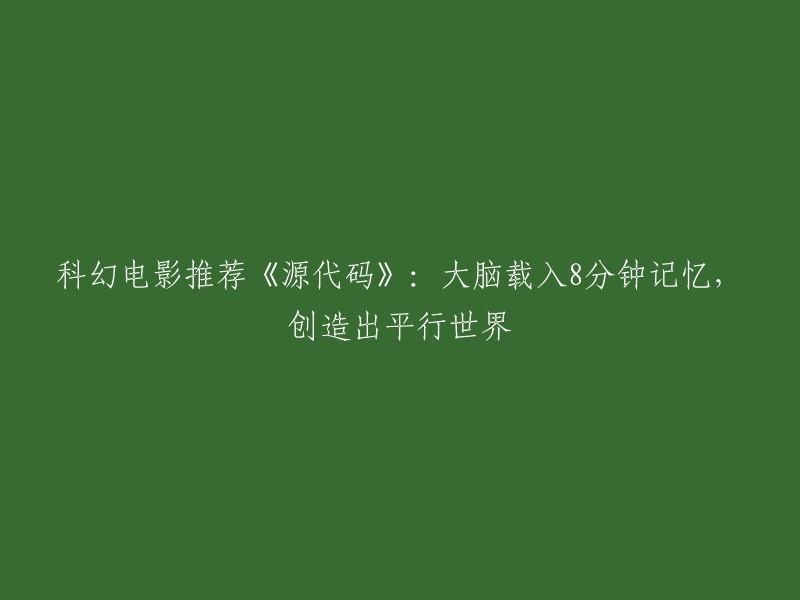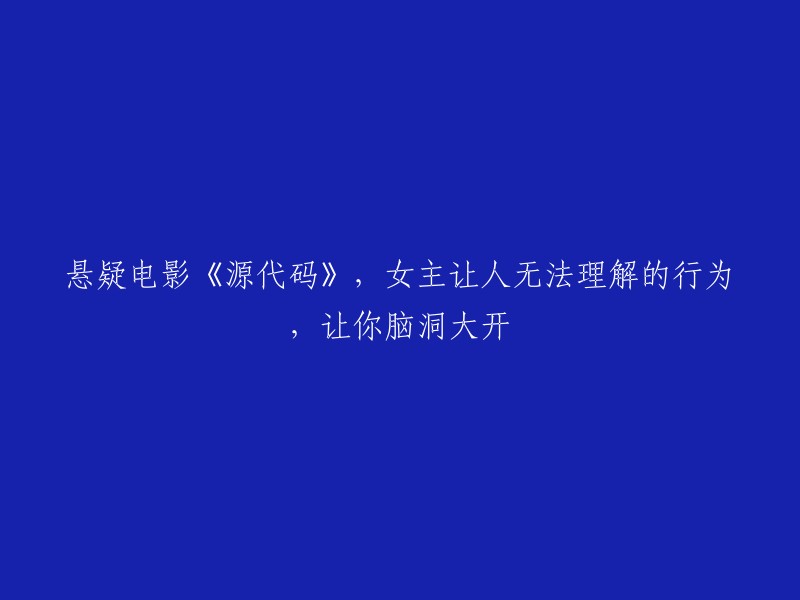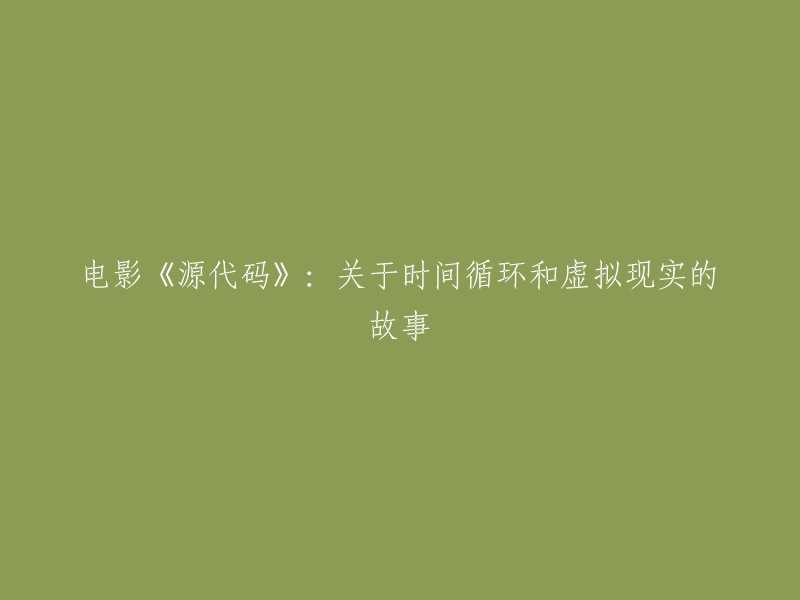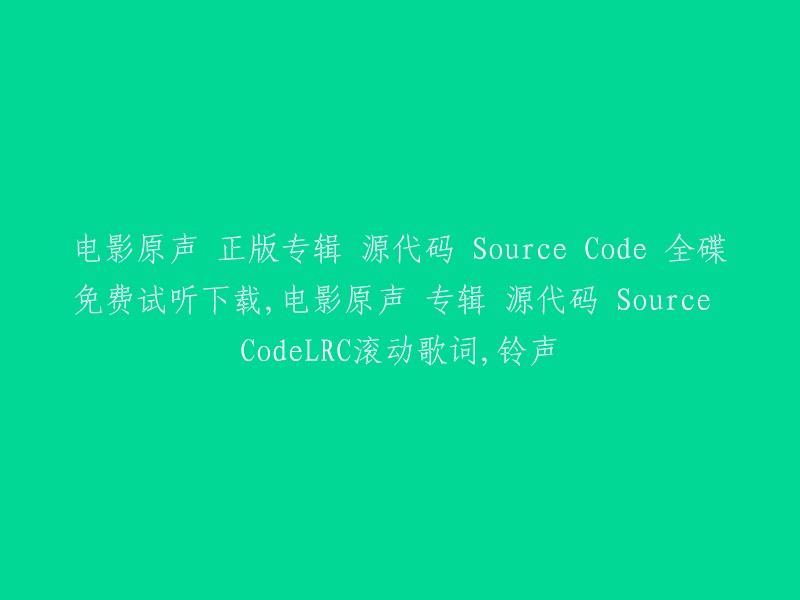在时隔近8年后,乌尔善导演终于带来了新作《封神第一部》。这部神话史诗电影自2014年首次策划会以来,历经种种原因的延宕,最终于今年7月正式上映。然而,对于一位商业片导演来说,这长达8年的空白期似乎过于漫长。
在拍摄《封神三部曲》之前,乌尔善曾先后执导《画皮II》(2012年)和《寻龙诀》(2015年),不断创造票房神话,被视为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代表。他的电影类型明确,特效绚丽夺目,制作流程标准化且国际化。当时,世界正处于上升期,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奇幻题材充满兴趣,喜欢看天马行空的故事和永不屈服的冒险精神。
然而,近10年来,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流浪地球》系列书写了关乎宇宙、未来和人类命运的史诗,成为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新标杆;《我不是药神》、《漫长的季节》等现实主义影视作品通过探讨社会议题和时代痛点,收获广泛共鸣。在年轻人的注意力被现实焦虑占据的当下,他们还会愿意去电影院看一个三千年前的神话吗?
《封神第一部》上映前一个月,记者在上海和北京与乌尔善两度见面。这个宽脸的蒙古族男人戴着红框眼镜、银质耳环和项链,与粗犷外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温和与耐心。我们向他抛出了上述问题。
乌尔善坚信自己的判断:「3000年来社会制度变化有多大,社会问题差异性有多大,但人性变了吗?我更关心人最本质的价值选择,善恶判断、精神成长的历程。」他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需要重新追溯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时期往往会产生史诗电影、神话电影。「中国人到底因为什么而成为中国人,经历过什么不一样的历史,形成了现在的性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是乌尔善迫切想知道的问题。现在,他用《封神第一部》做出了回答。
1972年,乌尔善出生在内蒙古,4岁随父母迁到北京。少年时他不爱说话,喜欢画画和写诗,枕边书是《荒原》和《北回归线》。他也热爱中国中世纪前的艺术,见到李成、范宽的山水画,整个人激动又震撼;读《史记》,看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欣羡古时的人那样英气勃发、光彩夺目。加上蒙古族血统赋予的属于游牧民族的宏大与浪漫,他似乎天然就应该拍神话史诗的大制作。
拍摄《封神三部曲》是他最大的梦,乌尔善多次说过。与之相应的,是巨大的风险。交谈中我们感到,眼前的这位电影创作者有着无比坚定的内在自我。乌尔善并不担心观众和市场对《封神第一部》的反馈。「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坏的打算」,他早已准备好面对一切可能。
乌尔善曾经说过,神话是公开的梦,而梦则是私人的神话。他将神话呈现在银幕上的梦境中,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神话。以下内容根据乌尔善的讲述整理而成。
1. 乌尔善表示,《封神第一部》可能会受到观众的不同期待。有人可能认为这部作品不切实际,无法完成;有人也许觉得这是一部烂片。然而,他非常迫切地希望将这部作品呈现给观众,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长什么样,不再猜测。
2. 该项目于2014年正式立项,乌尔善早年间便对《封神演义》的小人书充满热爱。小时候看书时,他总能脑补出许多画面。后来学习艺术,接触了大量艺术史、人类学和宗教方面的书籍、绘画、艺术品,对奇幻恢弘的神话世界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完成《寻龙诀》后,技术和资源上都有了一定的积累,使他有能力拍摄一部更具规模的神话故事,于是有了《封神》的想法。
3. 2012年,乌尔善曾宣布过一个名为《龙之战》的封神项目,主角为哪吒。然而,他在打羽毛球时不慎受伤,不得不在轮椅上坐了三个月。在这期间,他重新阅读了一遍《封神演义》小说,并决定将其整个故事拍摄出来。因为这部作品非常完整,讲述了两个家族之间的斗争,最终姬发家族战胜纣王家族,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方向。这条线索非常清晰,因此他认为将整个故事完整呈现是最好的选择。
4. 当时的腿伤让乌尔善产生了紧迫感。在无法动弹的时候,人们会思考身体与外界的关系。他认为,艺术创作的核心在于内在的元气。如果身体不行,能量不足,那么表达就会变得虚弱。尤其是《封神》这样一个故事体量很大,计划将其拍成三部曲的神话史诗片,技术复杂且浩大。没有强健的体力,是无法完成这个项目的。趁着自己还算年轻力壮的时候,抓紧实现这个梦想吧。
5. 第一次策划会议,乌尔善请来了许多学者,希望通过梳理《封神》的故事内核,找到可以与现实对话的部分,以及它与当代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他确定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善恶斗争与英雄成长。这种永恒的故事是不会过时的。
6. 前期筹备花费了很长时间,正式开机时间已经到了2018年8月。第一场戏拍摄的是电影的结尾,主角姬发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在朝歌当质子,目睹兄长被杀、父亲被囚;发现曾经视为英雄和父亲的商王殷寿原来是个暴君;自己也历经险境后终于叛出朝歌,骑马回到故乡西岐。也就是说,演员需要靠想象补足前面的所有情节,将返乡时那种痛苦、挣扎、醒悟、愧疚和勇气勃发交织的复杂状态呈现出来。
这段文字讲述了电影《封神三部曲》的拍摄过程。在新疆拍摄期间,新人演员们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从未演过戏,而且要穿上沉重的铠甲,骑着马,现场有很多人围着。导演要求情绪要饱满,摄影说你必须进入焦点位置,灯光、录音各部门都有要求。第一天上午拍完后,演员表现得挺稳的。中午吃饭时,制片人和新人演员碰了杯酒,算是庆祝。一年多的拍摄历程就这么启动了。
制片人预估整个项目需要8年到10年。如果失败了,可能得用之后的10年去还债。他把情况如实告诉了太太,太太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喜欢就去做。制片人给孩子买了保险,保证就算他破产了,他们的教育和生活也不会受影响;把父母接到家里住,方便就近照顾。家人都安顿好了,他就可以放心去冒险。
在新疆拍了一周后,当地的戏份结束了。最后一天早晨,剧组拍了些空镜后动身离开,下山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雪。远处的天山前一片白茫茫,很快,大雾也四面升起,什么都看不见。制片人特别庆幸幸好都拍完了,时间稍推后一点都不可能完成。后来几年里,项目遭遇了不少意料之外的情况《封神第一部》也没按原计划在2020年上映都是不可抗力制片人并不感到焦虑每个项目都有它的命运得接受命运就像面对新疆的麦田和大雪
许多人觉得制片人的电影路顺风顺水第一部商业电影《刀见笑》投资只有600多万接下来就是投资1.2亿的《画皮II》再然后是《寻龙诀》三级跳就上去了其实制片人也有过艰难的时候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制片人做了近10年广告导演和当代艺术参加过不少艺术展也拿过广告奖项之所以改弦易辙来拍电影源自两件小事
一件事是2006年某一天制片人偶然逛到电影院想看个电影结果发现上映的都是美国和香港的片子质量也不怎么样制片人挺震惊的平时他不去电影院觉得去那里看不到想看的电影他想看的电影都在盗版盘里那天突然觉得大量普通观众像他的家人朋友老师同学他们看什么呢?
况且,看盗版盘也不算个正经渠道。我又不是盗版盘学院毕业的,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电影哪去了?后来回电影学院做讲座我也跟学生们说,不能老活在盗版盘的世界里,拍的电影只在国外电影节被放映过,电影院才是我们真正的战场。
电影院里应该出现好的主流娱乐电影,它要兼具精神质量、制作品质和娱乐效果。我想看到这种电影,但当时没有,就想自己做。不久后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和太太去参观天文馆,在馆里看了一部短片《神奇的宇宙》。那是部纪录片,没有故事情节,就是展现宇宙万物,但给我的体验感太强烈了。那是我在其他艺术形式里完全找不到的力量,看舞台剧、小说、绘画都没有。我觉得自己一下理解了电影为什么是电影,就在于它创造体验,令人沉浸的能力。
从天文馆出来,我跟太太说,我知道要拍什么样的电影了。我要拍有强烈电影感的作品,它要创造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有强大的视听力量,磅礴的视觉效果,震撼的声音和丰富的情感。观众不可能在现实中经历,但会在精神上神往的。有了大方向,我很快确定了自己要做的具体类型,就是武侠、幻想和史诗类型的电影,并且要拍中国的故事。
我是1972年出生的,青春期正值西方文学、哲学、艺术思潮涌入中国,大家沉浸其中都如痴如醉。但慢慢地我产生了疑惑,「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难道仅仅是别人所创造的智慧的享受者和跟随者吗,我们自己在哪里?
后来做当代艺术的过程中我体悟到,创作者的价值,在于吸纳各色养分后产生的独特性,那一定和创作者内在的文化基因有关。作为一个中国创作者,我要把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讲清楚。
2007年我开始全力做电影项目,参加各种创投单元,被到处挑毛病。你这不行,这是什么啊,类似的话我都听过。其实很正常,你在电影行业是个新人,所有人都会对你指手画脚,你也应该接受,因为你的确没有作品。虽然我在2004年拍过一个独立电影《肥皂剧》,获得了釜山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但没有上映过,没有票房成绩证明自己。跟人家辩论是没用的,只能自己先做出作品来。
我启动了4个项目,磨剧本,找投资。《刀见笑》最终被选中,正式投入拍摄,是在两年后了。说起来也算是段不短的时间,但没觉得怎样艰难,包括被否定的时候。我做了十年广告,要满足甲方的各种需求,心理素质很好(笑)。
我一直在学习建立科学的工作方法,有机会拍幻想和冒险类型的题材后更是如此。在拍摄《封神三部曲》时,片场井井有条,大家每天按时上下班,有人说这是真正的工业化。实际上,我在拍摄《画皮II》和《寻龙诀》时已经开始探索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并非个人创造的,而是整个行业长时间积累出来的。因此,我和整个制片团队非常关注东西方那些高难度的电影,看了很多幕后花絮,了解他们的制作方法、质量标准、工作模式和团队组织。
例如,在拍摄《画皮II》时,我设置了概念艺术家,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概念艺术家在创作前期非常关键,他要确定电影的整个美学原则和视觉呈现的基本方向。没有概念艺术家提供的共同想象,创作会散乱。这就是制作的工业化:工种的细分、团队的配合、工作流程的科学。
更基础的是创作层面的工业化:弄清观众的需求是什么,电影的类型定位是什么,要实现这个类型,应该设置哪些基本的结构和主题。在拍摄《寻龙诀》时,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做剧本,类型研究和剧本写作同时进行。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事就是找到了「冒险」类型最适合表达的主题:讨论勇敢的人有没有恐惧。后来我把这个思考写进了《<寻龙诀>与类型电影创作实践》。最后才是新技术应用的工业化。工业化是这三个层面的,只谈特效就太局部了。
在筹备前期,确立《封神三部曲》电影的主线是最重要和困难的工作之一。《封神演义》原著里有众多人物和关系,但有什么是史诗级别的,能承载如此体量的故事与情感?我想了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它的元素太丰富,有大量视觉想象的奇观,很容易造成干扰。
后来我闭上眼睛去想,「封神」里哪一件事最打动我,我最想拍的那场戏、那个人、那件事是什么?如果没有很多钱能让你做特效,没有很多时间能拍战争场面,我会留下什么?我想到了两组人物关系,都是父子,一组是姬昌和姬发、伯邑考,慈爱的父亲和两个善良、正直的儿子;另一组是商王殷寿和殷郊,邪恶暴虐的父亲和叛逆的儿子。借由这两组关系,可以探讨丰富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最终,我决定将这两组关系作为贯穿三部曲的主线。
商王殷寿(费翔饰)向伯邑考(杨玏饰)赐酒。图源网络
我从小就是这样,重大选择关头总是坚持做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
我4岁那年,跟着父母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在军区大院度过了童年时光。从小,我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还记得,那时候的我非常淘气,但只要一拿起画笔,就能坐上一整天。中学时期,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来又顺利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系。当时的油画系是隔年招生,每届只招8个人,竞争激烈,非常难考。我的父母一直以我为傲,觉得我已经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然而,大二的时候,因为绘画理念与老师发生分歧,我在一次考试中成绩惨淡,被学校劝退。当时,我不想让父母担心,所以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而是选择出去租房住了一段时间。三个月后,父亲去学校找我,却在公告栏上看到了我的劝退通知。他一下子愣住了,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孩子。
上大学后,我干脆住在画室里,每天都从早到晚地画画,把所有能画的东西都用上,甚至把颜料盒的底部都画满了,满墙都是我的作品。晚上,我会点着蜡烛,和朋友们一起喝啤酒、听音乐、聊艺术。这样一个孩子怎么会被劝退呢?我的父亲想不通。
他去找老师询问原因,老师告诉他:“你的孩子太倔强了,我们公布处罚后,他都没有露面。如果他愿意去恳求的话,还是有可能留下来的。”父亲找不到我,也无计可施,只好出了学校去雍和宫找朋友倾诉。朋友安慰他说不用担心,孩子会有学上的。父亲这才放心地骑着车回家了。
事后回想起来,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在这件事上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那段时间过后,我回到了家里,他们没有责怪我,也没有过多干涉我的选择。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事,而且如果我愿意去恳求留在学校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再也无法从事艺术了。
于是,我在电影学院毕业后,开始了长达10年的当代艺术生涯。尽管当时有很多重大的选择要做决定,但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是否继续上美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捍卫了自己的准则。
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重大的选择,这个决定将影响接下来的10年工作方向。当时,我也曾经想过拍《画皮III》、《寻龙诀II》这样的电影,毕竟这些作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是最难以复制的,尤其是作为导演,40岁到50岁这个阶段是从体能、创作能力到市场信誉都走向成熟的阶段。
时间宝贵,我想还是要选择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有挑战性的工作。只有喜欢的事情才能让我充满激情;而有挑战性的事情则能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调动所有能量去完成。如果重复做已经成功过的事,我可能会变得懒惰,那就浪费了时间。半生的经历告诉我,生活无常,我们得先挑重要的事去做。
2019年冬天的一个雨天,我在青岛完成了《封神三部曲》的拍摄。整个拍摄历时一年多,很多剧组成员都不舍得马上离开,纷纷张罗着相互请客聚餐。虽然后期还有大量的剪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但我并没有什么结束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离完成还早呢。
能顺利完成拍摄,有些超乎我的预料。《封神三部曲》采用的是三部连拍的方式,这是我们做了大量考察和分析后确定的,可以节省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成本,也能保证年轻演员形象上的统一性。难点在于,拍摄周期会比常规的电影项目长得多。
筹备期间我去新西兰和《指环王》三部曲的导演彼得·杰克逊见面,他告诉我,自己拍《指环王》时快疯了。《指环王》就是三部连拍,工作量太大了,他崩溃地倒在沙发上,还被无数人围着问问题。他说他想放弃,不拍了,心想下次一定要挑一个自己特别想拍的题材,才能受这份罪。想来想去发现自己最想拍的就是《指环王》,才又有了力量。
听完彼得·杰克逊的话我就想,我拍《封神三部曲》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惨状」。安顿家人也有这个原因,怕自己中途身体垮了。我还交代助理准备好躺椅,万一不行了,就倒在躺椅上拍,真就是「倒演」了。
最终《封神三部曲》A组拍了342天(总拍摄日438天),超过了《指环王》的286天。我没有倒下,甚至比以前更健康了。原因在于的确学到了科学的工作方法,安排得更合理。剧组每天拍摄10小时,拍摄6天休息一天。我则是每早8点起床,大约凌晨12点结束工作,听听音乐放松后休息,不觉得多辛苦。
乌尔善给演员讲戏。这么多年做《封神三部曲》项目下来,我确实像当初期望的那样,学到了很多。在「术」的层面,我了解了神话史诗类型的电影应该做到什么标准,主题要达到什么深度,应该具备怎样的通俗性。从「道」的意义上,我重新把历史、神话学、心理学这些学科重温了一遍,理清了很多原来没想明白的问题。比如神话是什么,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和核心价值是什么。还有,支撑中国人的精神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伦理,是亲情关系。在这个基点上讲故事,我觉得能打动观众。
做文艺青年的时候,可能会被那些花里胡哨的论点、主张,以及当下的片段信息干扰,但到了我这个年纪,最终会确认一些价值。生命的意义何在,什么是真实,为什么要追求真实,我是在做《封神三部曲》的这10年里确认的。在危机面前,什么东西真正产生力量,不是权力,不是武器,不是愤怒,也不是对抗,是人最本质的善意。尤其是经历了过去三年后,这些问题不再只是抽象的思考,而是日常的感受和实践。神话史诗其实就是在重述这些经典价值,提醒我们哪些东西是恒定的,是永远值得追求的。
小时候,我们大院每周都会放露天电影。我印象最深的第一部电影是香港拍的《三笑》,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第一周看过了,第二周重播时,我专门从全托幼儿园跑回大院又看了一遍。因为这部「白月光」,后来我对其他三笑题材的电影都很抗拒。之后看《少林寺》,着迷到每天支个锅练铁砂掌,还想过离家出走去少林寺学武。电影制作完成不是结束,观众来感受它,把它印在记忆里,这个电影才结束。像《三笑》和《少林寺》烙印在我记忆里那样,我希望自己的电影也能留下印记。接下来还有10年的壮年期,我还能拍技术复杂的电影。
等65岁后,我想去拍文艺片。低成本,工作强度不大,甚至像伯格曼那样,整个团队不到10个人,但可以探讨更尖锐、极致的主题。电影是丰富的,多层面的,不是说有了《少林寺》就不需要塔可夫斯基,或是反过来。我有个目录,已经列好了5年、10年、20年内想做的电影,我希望,能用它们来标注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