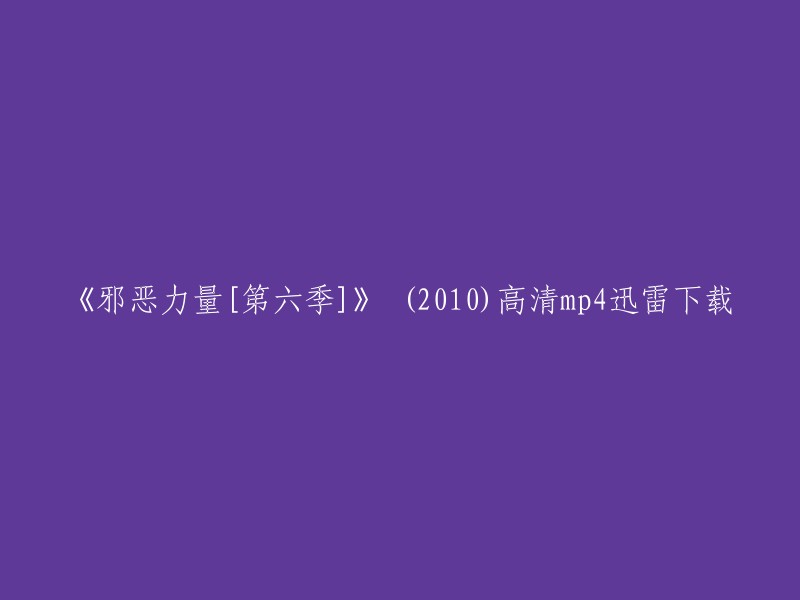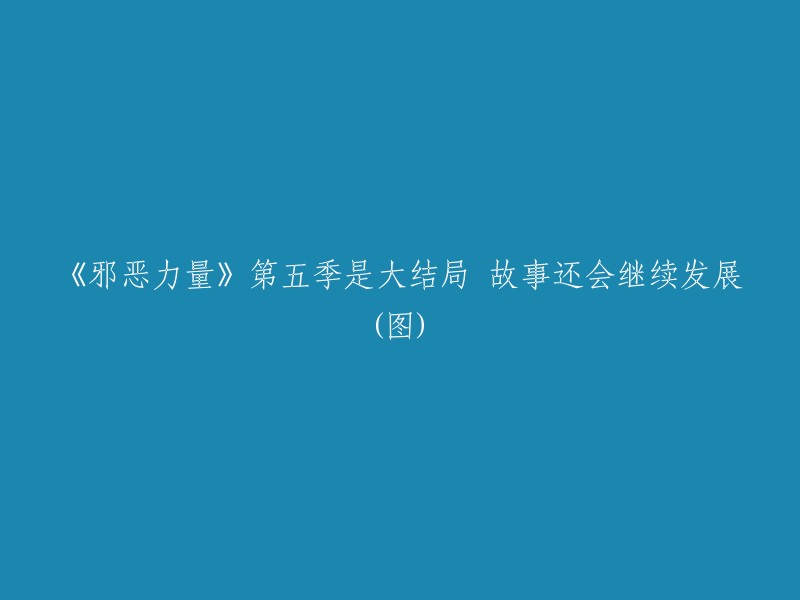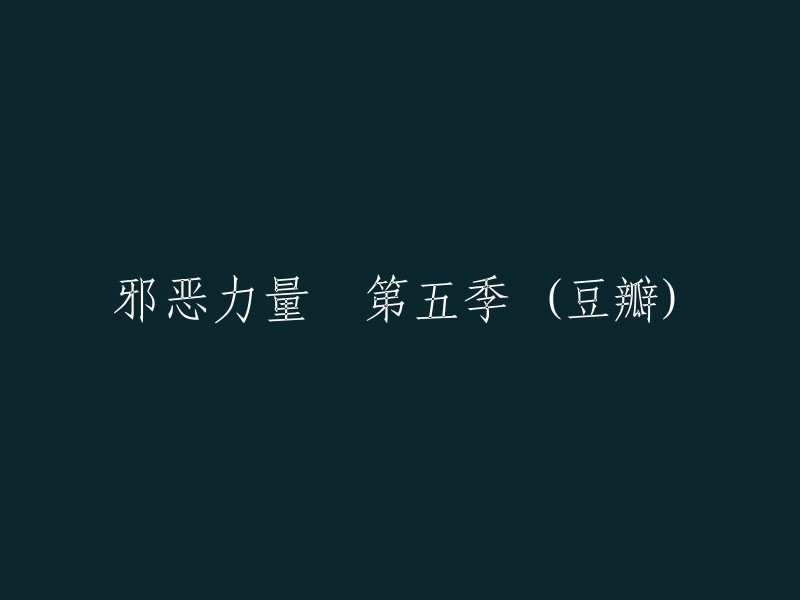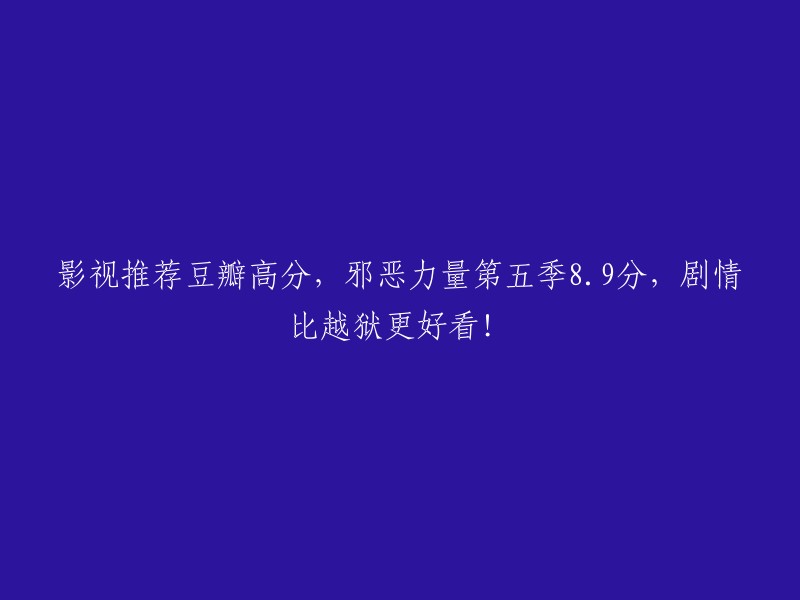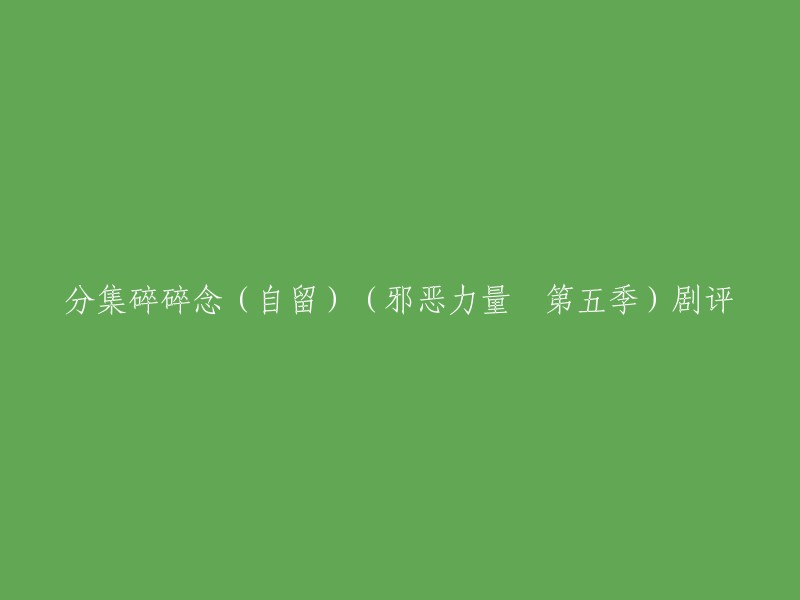公白飞第一次遇到艾潘妮,是在一个雨天。那天,她穿着男装衬衫和一条红色裙子,敲开了他那扇有点掉漆的公寓门。雨水顺着她的头发梳成一绺一绺,让她看起来有些狼狈。
“请问这里只有你是绿漆门吗?”她问,声音不算太好,毛渣渣的像那些叫声嘶哑的夜行鸟。
公白飞点了点头,这一栋房子只有他一户是绿漆门,热安挑的颜色。“你要进来坐一会儿吗?”他问。
“有人让我把东西给你,”她掏出一个小信封塞到公白飞的手上,“我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做,我先走了。”
两个月后,公白飞知道了那个姑娘叫艾潘妮。临近圣诞节,人们都愿意花一些钱让自己开心一些,即使商店里再也没有那些精致的小玩意儿,没有了雕花精美、颜色各异的糖果,挂着各色灯泡的巨大圣诞树,但总有方法让这个节日变得丰富多彩。
公白飞依然穿着得体,他穿着一件厚实的外套,里面是一件毛织背心,圆顶帽是三十年代末的款式。他站在散伙的人群中间,旁边是成双对的情侣、抱着花束的卖花女、到处招呼客人的自行车司机。他走到一侧没有什么人的地方,艾潘妮就在那里等着他。
“我喜欢话剧,而且我也不喜欢把钱花在娱乐上。”公白飞说,“你今天很漂亮,我应该给你买束花。”
“可是现在没有什么好看的花,四月份的郁金香不错,我喜欢白色的,带红条纹的也成。”艾潘妮今天找人借了一套衣服,从扎着丝带的夸张帽子到时新的大衣和连衣裙,她第一次穿上了尼龙丝袜和高跟鞋,走路还有些摇摇晃晃的。干枯毛躁的头发用发油和水梳顺了,虽然在灯光下还有些粗糙,但至少像个有学识有工作的姑娘而非街上的游孩。她的手上提着一个大号的行李箱,看起来份量不小。
公白飞明白那些资料和情报传递的规矩,因此没有提出来要帮她提箱子。他自然而然地挽住艾潘妮的手,向检查哨岗走去。
“等一会儿过去的时候,装得像一些。”公白飞低下头,凑到她耳边悄悄说。
公白飞和艾潘妮手牵手走在昏暗的街道上,两人身边都是沉默已久的砖石和房屋。他们在街口分别,公白飞要去找安灼拉商讨最近的任务,而艾潘妮也要把一些委派任务完成。然而,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却是同一个地点。
安灼拉打开门,取走了箱子,和艾潘妮道了晚安。公白飞坐在沙发上,看着今天的报纸。安灼拉看起来很沉默,他把手提箱打开,箱子里装的是一个红色丝绒贴面的箱子,还有一本厚书。
“关于你的父亲......我很抱歉。”安灼拉说。
“请不必,”公白飞回答,“他也是个不可理喻的人。”
一年很快过去。他们的任务越来越多,接头地点换了又换。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还没有被其他人代替。
艾潘妮的情报非常多,她有着一个沉在地下的由三教九流组成的情报网。她每晚都会去洗衣妇街和姑娘们交换情报,偶尔也做一些端酒倒茶的活赚些外快。洗衣妇街就像一个平民版的利兹酒店,是一个隐藏着的情报集散地,在这里试图找乐子的下层军官永远都会留下不少不该留下的秘密。
“周四不要去缪尚。”艾潘妮坐在安灼拉家那张旧沙发上,看着正在喝水的两人。茶叶配给少得可怜,安灼拉一罐放了很久的英国茶喝了将近一年,现在也见了底。但他依旧谢绝了艾潘妮从黑市里带回来的茶叶和糖。
“为什么?”安灼拉问。
“还能为什么?有人查呗!沙龙里那几个姑娘听到的,这几天会查几家疑似有工作点的咖啡馆,缪尚是其中之一。上一次的事我原谅你啦,这一次再不听我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给你弄情报了。”
安灼拉点了点头,他还有其他事情,便戴好帽子出了门,把他们两个留在公寓里。
“名单我可以在这个星期之内给你。”艾潘妮说,“我认识不少人。”公白飞知道她口中的“名单”是什么,艾潘妮穿梭于三教九流之间,因此她最适合去刺探那些更深处的情报,而公白飞的任务则是把他们整理出来。
两人沉默地喝着茶,窗外又响起了刺耳的军乐声。公白飞关窗把噪音隔绝在窗外。“你们认识马吕斯?”艾潘妮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端详着一张挂在墙上的照片。ABC都有这张照片的备份,安灼拉把这张照片挂在了一个有些发黑的银质相框里。这是战争前他们最后一次聚会的合照。在这张照片里还活着的人已经所剩无几。
“你也认识他?”公白飞问。
“之前他住在我家旁边,算是个朋友。”艾潘妮抓着她的红色粗布裙子。“他上了战场。”
“他应该过得还不错。”公白飞摸了摸鼻子,别开眼睛。两人一瞬间就抓到了对方无意识的撒谎。
“带你去个地方,你会喜欢的。”艾潘妮岔开了话题。
晚一些的时候,艾潘妮带着他去了一个仓库,里面堆满了木条箱,标签上写着货品是美国黄香烟。仓库里和灰尘一起扑面而来的是烟草的香气,公白飞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惊喜呛到了,猛地咳嗽。
“天啊!”公白飞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这里是德纳第的地盘,而我很不巧也姓这个。不过相对于这里,我更喜欢马吕斯喜欢的那个姑娘搞的妇女互助会。”
公白飞叹了一口气,掏出火柴和自己卷的玉米花丝烟卷,深深地抽了一口。在烟草配给少到几乎没有之后,公白飞把烟戒了,改抽没有味道的花丝烟卷。
“你们有学识、有目标、不怕死,还领领导着一个小组,我没理由不喜欢你们。可惜我们差太远啦,我只是无数个走街串巷的姑娘中的一个,我死了就会有另一个人给你们提供情报。但跟你们一起走就跟重新活着一样。和你们走在一起的那个大学生姑娘第一次去酒吧找我的时候还很害怕呢。那个金发大个子也是,不过小伽弗洛什倒很喜欢他。”
露天咖啡馆里依旧有很多人,但是气氛开始变化了。人们交头接耳的内容变成了贴在墙上的抵抗运动海报,变成了盟军会来巴黎,变成了胜利在望。两个人走在路上,其他组织的成员在街角发表演讲,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也有不少人在分派传单。有几个认识他们的人向他们打招呼,甚至有个年轻的德军士兵试图停下来听他们的演讲。
艾潘妮哼着歌,公白飞不用猜都知道还是那首《八月时光》。街上卖花的小姑娘向过往行人推销着她的鲜花。八月即将过去,对于巴黎来说,痛苦即将结束,一切都将烟消云散。他们为此准备了四年,仅差最后一击。
古费拉克冲进房间时,留在酒吧里的姑娘们正热烈讨论着外面发生的事。一夜之间,巴黎人纷纷建起街垒,拿起枪支和弹药,起义来得如此突然,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艾潘妮!我需要一点羊肠线!”古费拉克喊道。艾潘妮知道那是什么,她敢肯定认识的人里有人受伤了。这个皮肤晒得红黑的年轻记者坐在吧台前喝了一口水,艾潘妮给他清点好东西。加入了互助会的姑娘们和其他妇女有不少在街道上的街垒里,帮忙运送砖石、治疗伤员。这家小酒吧只留下了寥寥几人。
“公白飞怎么样了?”艾潘妮把东西打包好,递给古费拉克。
“他很好,我回来的时候他在组织撤退。”古费拉克说,“不过现在别出去,对谁都好。我们打算转移,和工科大学他们合并。”
艾潘妮点了点头,攥紧了裙子口袋里的纸片。如果再不能交给公白飞,她想,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艾潘妮拿了一瓶装在香槟瓶子里的鸡尾酒*,把它扔进了一台对着街垒的装甲车里。公白飞看着她被射倒,血散了一地,就像四月份开放的郁金香花瓣上鲜艳的红色条纹。装甲车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照在地面上,把渗进沙地的血液改成了一种诡异的颜色。
安灼拉试图拉住他,街垒外太过危险,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他不希望公白飞死在这里。但公白飞挣脱了,他翻下街垒,冲到了马路上。艾潘妮还活着,白色的衬衫已经被血浸了大半。公白飞冒险把她翻了过来,他看到了射到肋骨的弹孔。
他脱下外套试图止血,但渗出的血浸透了外套流到他的手上。公白飞用沾满鲜血的手轻轻拨开被血和汗浸湿的头发。
公白飞在两天前临时组成的担架队很快赶到,他们把艾潘妮抬到了伤员集中营。这里伤员太多,医护太少,呻吟声和尖叫声不绝于耳,临时组成的医疗队和志愿者四处奔波。公白飞有行医资格,但他不敢冒这个险取子弹。在这里取子弹,一旦失败就等于立刻杀了她,但成功的几率太小,这个数与零无异。
“我要死了,是吗?”艾潘妮忽然睁开了眼睛,“公白飞,我渴了。”
公白飞抓住她冰凉的手。每一股鲜血都在带走她的生命,“别说话,会有人来救你的。我叫了人过来,再坚持一下,不要说话,你会活下来的。”
“我渴了......我会死吗?你的名单......我......我放在口袋里......马吕斯的事不用瞒着我,结束了......一切都烟消云散。”艾潘妮继续说,但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嘈杂的声音里。每一句话的间隔越来越长,越来越慢。
这个时候公白飞忽然希望她能说上一两句话。说什么都好。但她却再也说不出来了,连告别也没有说。公白飞掏出沾了些许血迹的麻纱手绢,轻轻盖住她的脸。他拿走那张已经被鲜血浸湿的纸,回到了街垒里。
“她还好吗?”古费拉克问。
“很不好。”
结束了,结束了,一切都烟消云散。*莫洛托夫鸡尾酒,即土制燃烧弹
“他们在何方,我们再也不能相见。
结束了,结束了,一切都烟消云散。”
《八月时光》的歌词,我在波伏娃的《名士风流》里面看到的,觉得合适就用了(瞎用示范)
看资料,那几天巴黎天气并不好,间或小雨(所以他们唱小雨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太巧了就让他随风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