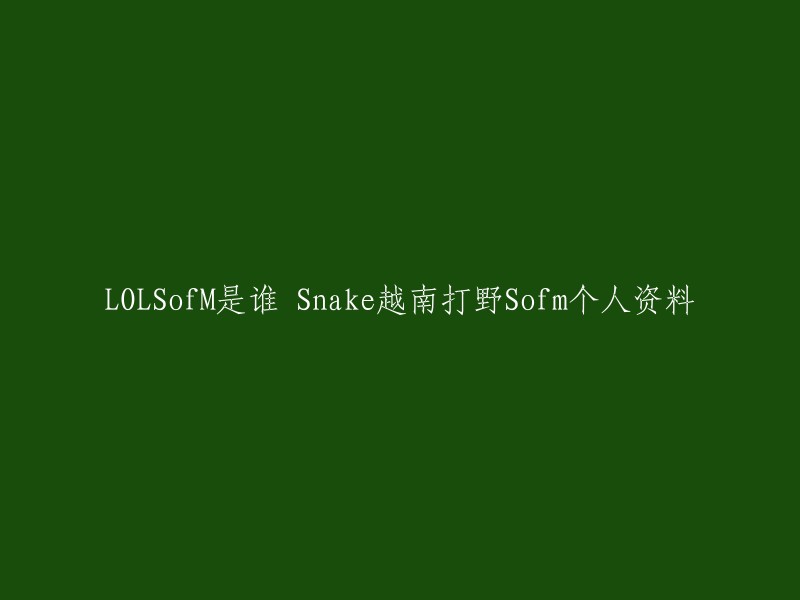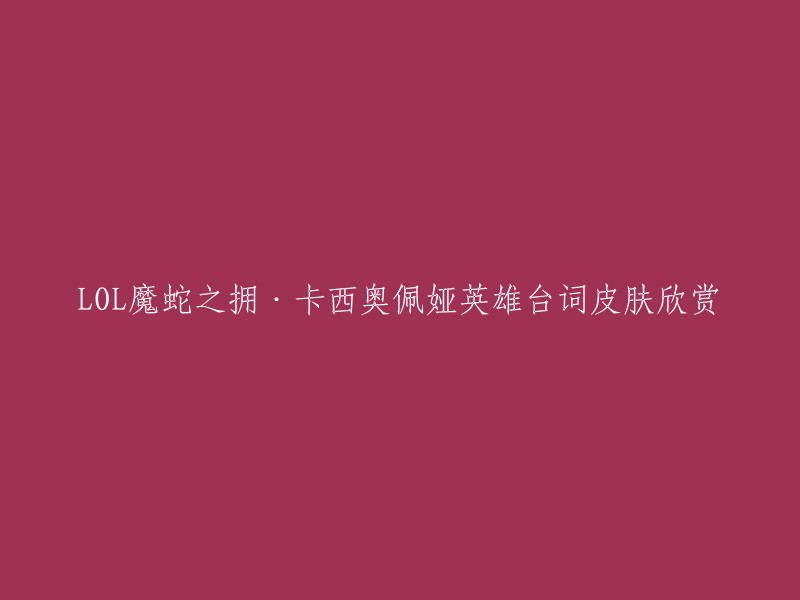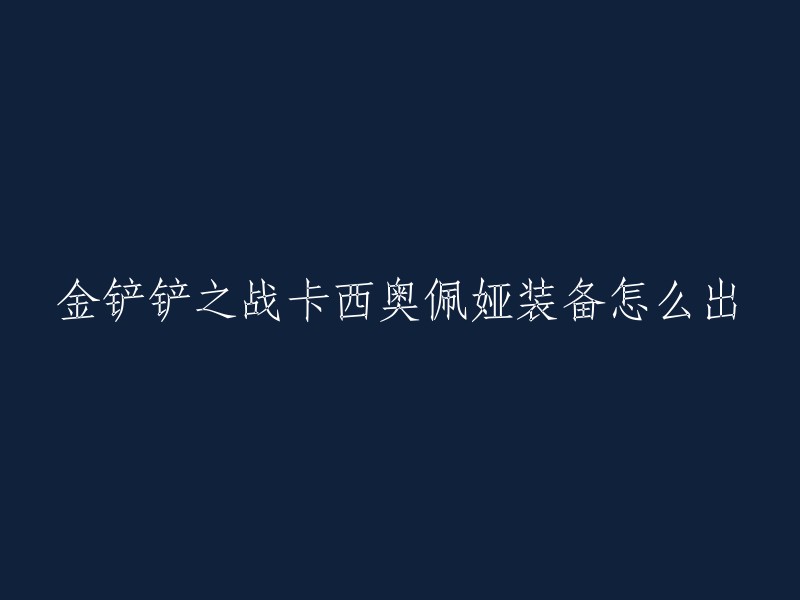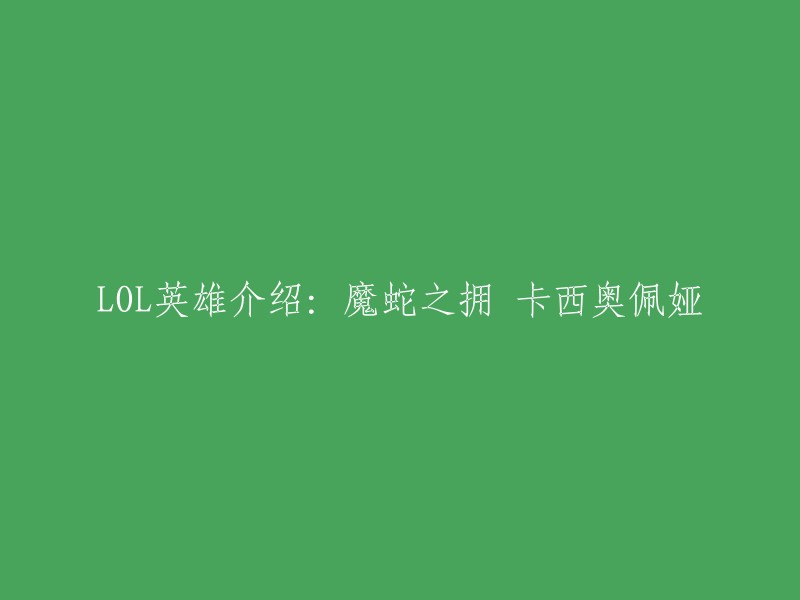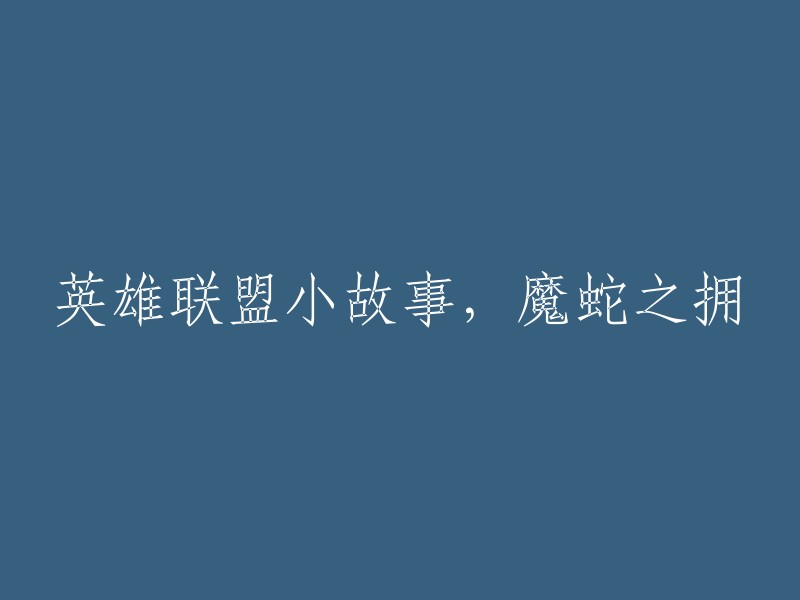香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调料,但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却很少。当我们看到胡椒、丁香、乳香、沉香、旃檀、肉桂等香料时,我们可能一无所知——不知道它们是如何生长的,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香料成为了我们最熟悉的味道,也是最陌生的存在。
就像胡椒一样,它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香料,仅看名字,我们可能知道它是从异域传来的,只是不知道这个“胡”具体所指。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弗在他的名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详细勾勒了胡椒的传播路线:“胡椒属于植物最初生长在缅甸和阿萨姆,先是从这些地区传入了印度、印度支那以及印度尼西亚,然后,又由印度传入波斯,再由波斯语檀香木和药材等一起运转到中世纪的亚洲各地。”因此可以推断出胡椒之“胡”,指的是印度;更具体地说,胡椒乃是产自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的胡椒树果实。据说,胡椒传入中国的时间至迟不晚于晋代。从它进入中国开始,其异域情调就革新了菜肴制作方式,立刻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调料。由于香料稀缺性大增,胡椒也成为衡量财富尺度之一(在这方面中西都是如此)。显然,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也有原产香料,但因为热带地区才能产出高品质香料,所以中国香料质量远不如热带地区。前文提到的众多香料主要依赖于海外进口,如同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一样,尤其是南中国海承担了主要的香料进口贸易。
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遇见了一个对他来说很意外的卡里卡特商人。当他们问起达·伽马来到这里寻找什么时,他的回答是:“基督徒、黄金与香料。”由于东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积弱不振,人们总是认为达·伽马等航海家发现了东方,并引发了大航海时代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这是认识上的极大误区。简单地说,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亚洲以中国与印度为中心就有着非常频繁的经济往来。或许因为香料太微小了而被忽略掉吧;又或许因为西方话语体系下的认识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们时常忽略它们的存在;就像我们常常忘记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实际上就是香料搜寻者一样。其实也没有人能否定香料的伟大之处:它们几乎见证了一部人类伟大贸易图景啊!
南洋贸易史是指自唐朝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的贸易往来。在唐朝时期,中国的贸易势力就大规模地扩张开来,尤其是在683年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朝(the Kingdom of Sri Vijaya)建立前后。当时印度输出的主要产品便是香料。宋元时期从南海进口的商品中,香料约占70%。《宋会要》就记载了绍兴三年进口品总计212种,其中香药177种、珍宝11种、手工业品14种,其他资源性商品10种。学者弗兰克就直言,一直到19世纪初,在亚洲,包括印度洋,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过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则根本无权置喙。
由于当时世界的航海还没有解决在季风中逆向航行的技术问题,所以航行还非常依赖于季风。因此从中国出发向南航行的船只,必须凭借11月到次年3月间的东北季风;而从印度出发的船只,只有依靠4月到10月间的西南季风方可抵达马六甲海峡。而马六甲的西岸特别适合船舶避风停泊,在地理上成就了马六甲当时重要的现货交易中心及贸易中心的地位。在这块亚洲水域,中国的渔民和商人遇到欧洲人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这儿探索了一千年。这一千年来,从南洋返回家乡的中国平底帆船船长,必须要让自己在季风到来的时候尽快扬帆,好让自己在台风到来前平安到家。
香料在中国古代宗教仪式、祭祀庆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苏合香不仅作为佛教仪式中的香料,甚至还演变出一种舞蹈。唐代时期的教坊记首次记载了“苏合香”的曲名。著名戏曲艺术家欧阳予倩主编的《唐代舞蹈》一书中,董锡玖执笔的《苏合香》一文详细描述了苏合香舞的历史和由来:“《苏合香》是印度的音乐,印度阿育王有病,服了苏合香,马上就痊愈了。
阿育王大喜,就命臣子育偈作《苏合香曲》及舞蹈,以苏合草业为胄。日本有《苏合香》舞,为六人或四人舞,服装和左舞(日本称唐代传去的舞为左舞)的一般装束相同,冠上戴着苏合草叶,香气四溢,以驱邪气,他们说这个舞是经由中国传去的。”虽然《苏合香》舞在唐代记载后便失传,但曲子在宋代仍有流传。然而,南宋之后,《苏合香》之曲已不再出现在中国。
在中国与印度之间,由香料衍生的典故不胜枚举。无论是古代的古印度、古埃及还是中国的宋朝时期,香料都是宗教仪式、祭祀庆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以室利佛逝为集散地的乳香,在北宋时期大量输入中国,类别竟然达到十三种之多。原来北宋一朝皇帝多好道,而乳香就成了道家的仪式用香。
爱德华·谢弗总结:“佛教与外来的印度文化为中国的寺庙带来了大量的新香料,而众多的有关焚香和香料的习俗和信仰也随之传入了中国,从而加强和丰富了中国古老的焚香的传统。”传统中国是一个诗歌的王国,新鲜事物的融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书写。如杜牧所写《赠别》:“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赫尔曼·黑塞,一个世界公民,在《东方之行》中写道:“我的一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从事印度与中国的研究——并非要谋取学者之名,不过是习惯于汲取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和那虔诚的芬芳。”1911年,34岁的黑塞和他的画家朋友汉斯·施图尔岑埃格结伴前往亚洲,亲身去感受萦绕他大半生的“芬芳”。在一段描写印度印象的文字中,他回应了之前的“芬芳”:“在那里,我看见了棕榈树和寺庙,闻到梵香和檀香的味道。”
对于德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或许显得过于遥远。然而,在中国人眼中,香料的美妙之处,正如戴望舒笔下那“丁香一样的姑娘”。尽管作家和诗人的想象往往停留在美好的隐晦之中,难以揭示更多的意象,但现实中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却有着无数被隐藏的故事。
例如,在丝绸之路上,我们对印度的古吉拉特市场、卡里卡特港以及东南海域的马六甲、巴达维亚港等了解甚少。这里无需重述大航海时代的历史,17世纪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开始出现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这条香料之路上,开展跨境贸易。然而,从19世纪开始,历史已经被船坚炮利重新定义。正如汉学家卜正民所说,在17世纪及之前的历史坐标中,欧洲的航海家只是亚洲主导的航海大戏的配角,他们并没有几项技术比亚洲对手先进。
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了解得太少,以至于在面对卜正民的论述时,很多人会感到心虚或虚妄。我们不知道巴达维亚港在季风亚洲的海洋上统治着一个扩张的、贸易的商业帝国;而对于扮演中华帝国海上门户长达两千年的广州,我们又知道多少关于城市面对海洋的紧张与向往?
相对于卡尔维诺笔下的“看不见的城市”,这条香料之路上的城市更像是“看得见的城市”。或许是因为印度的香料、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甚至还有英国人带来的鸦片,这些城市以及越南沿海、中国海域、马来群岛等地将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