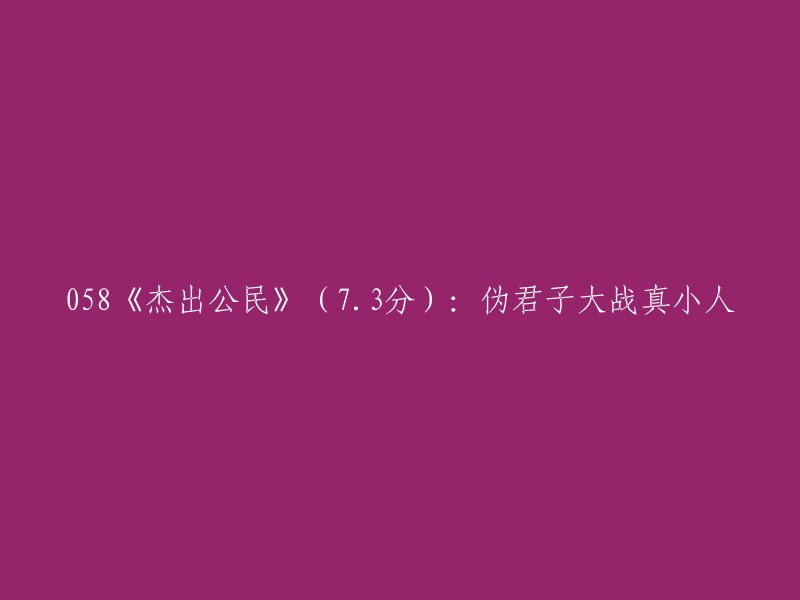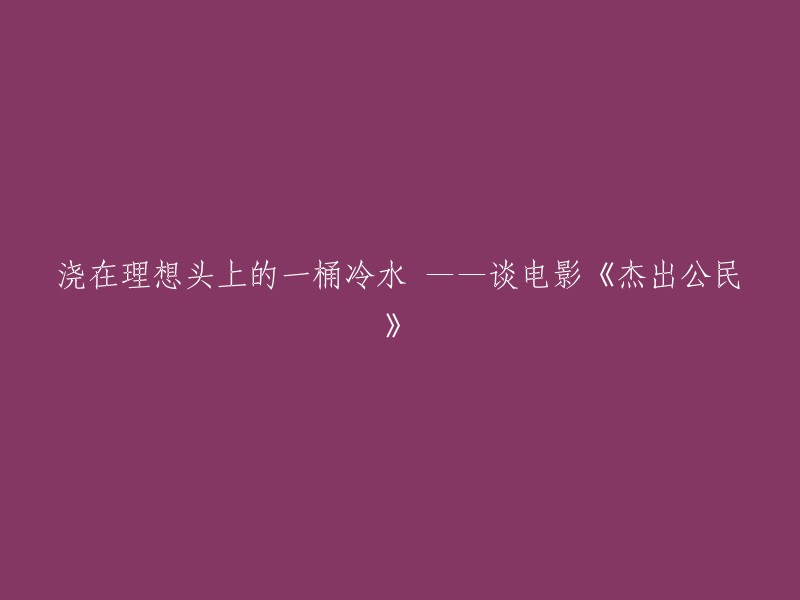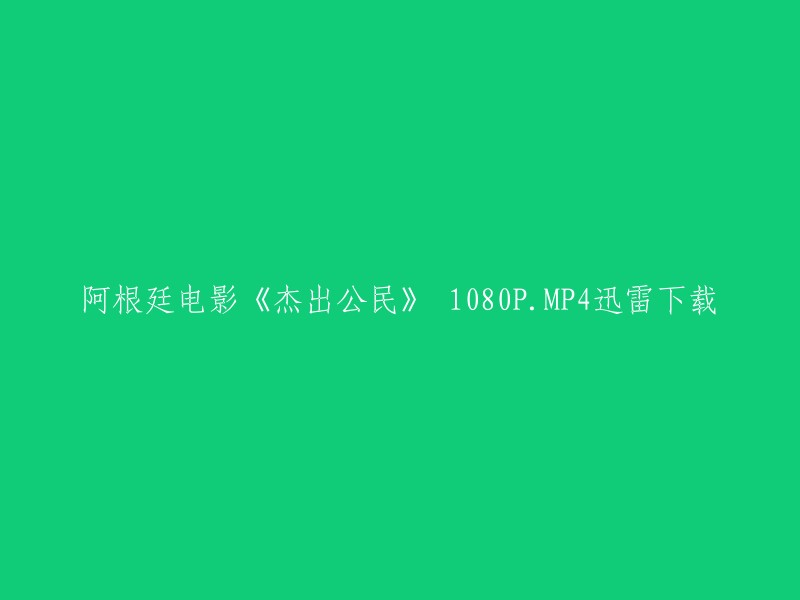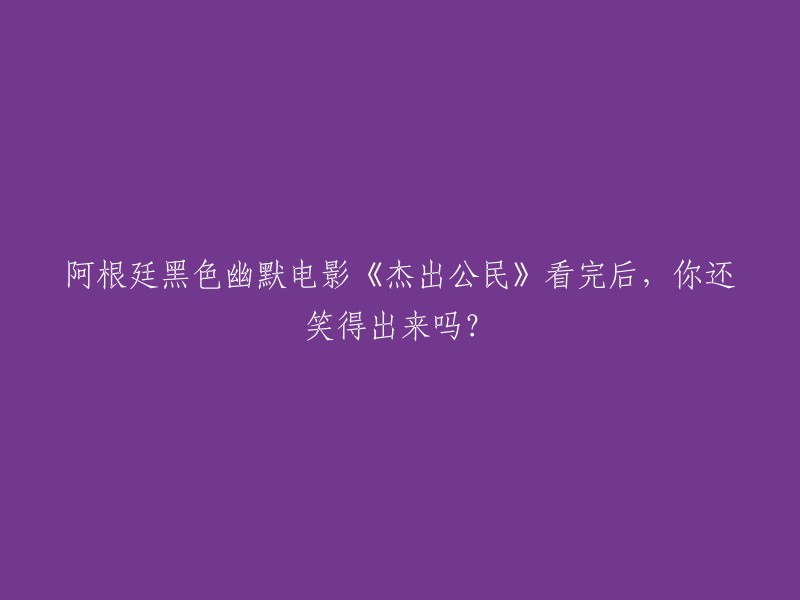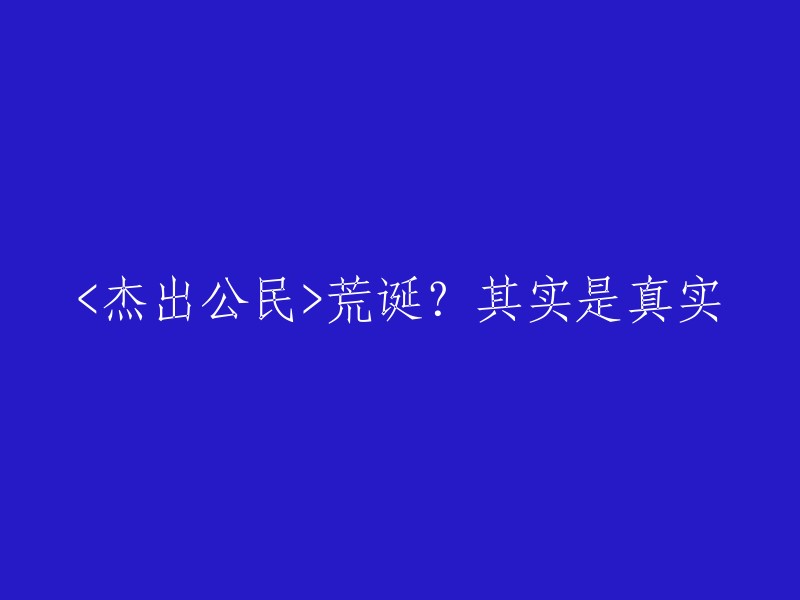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
这篇序言的一部分摘自我在1977年为《路边野餐》(The Dispossessed)撰写的一篇评论,那年这本书的英语版本首次发行(1)。我想把那个时代读者的一些反应记录下来。当时,苏联最糟糕的日子依然历历在目,而苏联小说在智慧和道德上仍旧趣味盎然,散发着勇于冒险的魅力。同样是在那时,对苏联科幻作品的正面评价在美国还很少见,基本上都是关于它们的政治声明,因为美国科幻界那些参与冷战的人士认为,生活在铁幕(2)之后的每一位作家都是敌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为了保持道德的纯洁性,这些保守派拒绝阅读(保守派们向来如此),这样他们就不必注意到这个事实:多年来,苏联作家一直在用科幻的形式书写相对不那么受其现实影响的作品。
无论何种现状,科幻小说都很容易运用想象力加以颠覆。那些官僚和政客不懂得如何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往往认为里面不过就是些射线枪和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只适合给孩子看。作家可能只有像扎米亚金(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我们》(We)中那样对乌托邦公然批判,才会招致审查机关的镇压。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既没有公然批判乌托邦,也从未(据我所知)直接批判他们政府的政策。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写得仿佛对意识形态完全不感兴趣,我当年觉得这是最令人钦佩之处,现在仍然这样认为,而我们许多西方国家的作家都很难做到这一点。这二位就像自由之人一样写作。
《路边野餐》讲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第一类接触”类的故事。外星人造访地球,随后便离开了,在地球上留下几个着陆区(现在被称为“造访区”),里面到处都是他们丢下的垃圾。野餐的外星人已经走了,驮鼠一样的人类虽然高度警惕,但同时也充满好奇,他们靠近皱巴巴的玻璃纸、啤酒罐上闪闪发光的拉环,试图将其驮回自己的洞穴。
大部分垃圾碎片都令人费解,且极度危险。其中一些被证明很有用(比如为汽车提供动力的永续电池),但科学家们始终都不确定,他们对这些装备的应用方式是否恰当,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把盖革计数器当作手斧,把电子元件当作鼻环。他们搞不懂这些造物的工作原理及其背后的科学问题。一家国际研究所资助了这方面的研究。交易垃圾的黑市繁荣起来。“潜行者”潜入禁区,冒着各种骇人的致残或死亡风险,偷取外星人的垃圾,把东西带出来,然后卖掉,有时甚至还会卖给研究所。
在《路边野餐》中,那些来自太空的造访者即便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对沟通也显然毫无兴趣。也许在他们看来,我们就是野蛮人,或者与驮鼠无异。他们不予交流,我们无从了解。
但是,人类需要了解。那些造访区影响着每一个与之相关的人。对造访区的探索滋生了腐败和犯罪;逃离造访区的人,灾难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潜行者的后代基因发生变异,变得不像人。虽然基于这一晦暗设定,作者却将故事写得真实生动,走向令人难以预测。
这段文本讲述了一部俄国小说,其中提到了作者用讽刺、滑稽且富于同情心的基调表达了一个有趣的想法:认为“更高等”的生物可能对人类完全不感兴趣。在小说后半部分,一位科学家和一名心灰意冷的研究所员工展开了一番精彩绝伦的辩论,作者在伦理道德和智慧上的超高修养由此跃然纸上。然而,故事的核心是个体命运,主人公雷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们关心他的命运,因为他的生存和救赎都处在危急关头。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将莱姆关于“人类理解论”的讨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人类处理外星人遗留物品的方式”是一种考验,或者,如果雷德在最后那可怕的一幕中经受了残酷考验,那么,考验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到底通过了没有?究竟何谓“理解”呢?
最后的许愿“希望每个人都幸福、自由”,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然而,这部小说绝不仅仅是关于苏联解体,或者基于科学的“普遍认知论”之美梦破灭的寓言。在书中,雷德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上帝说的,也可能是对我们说的:“我从未将灵魂出卖给任何人!它完全属于我,还有未泯灭的人性!你自己搞清楚我想要什么吧,因为我知道,我的愿望不可能是邪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