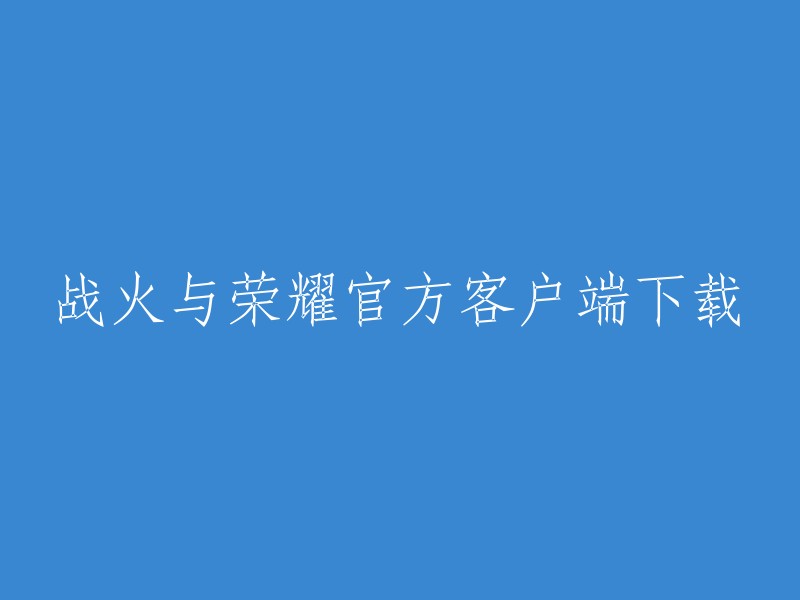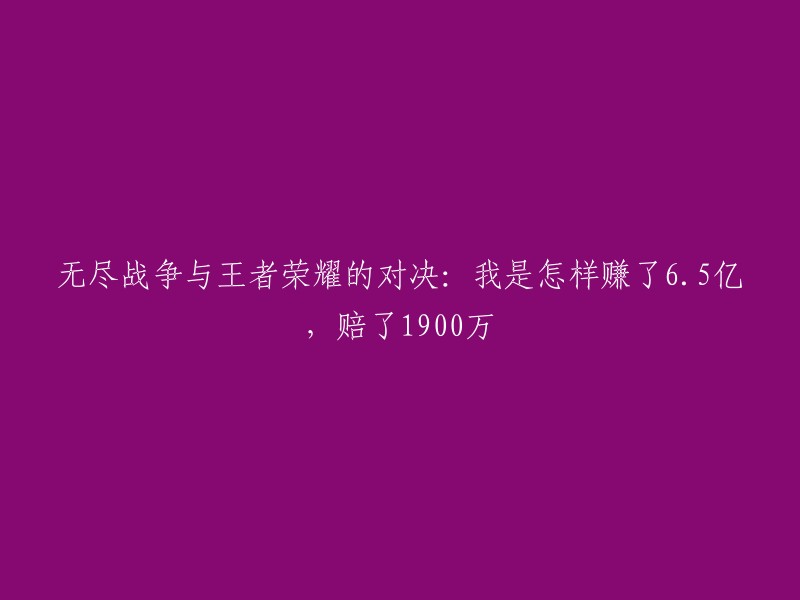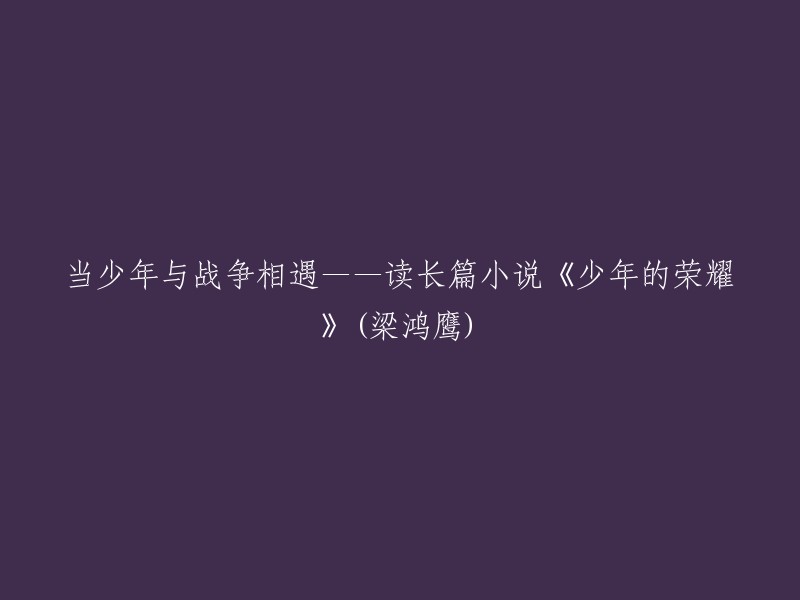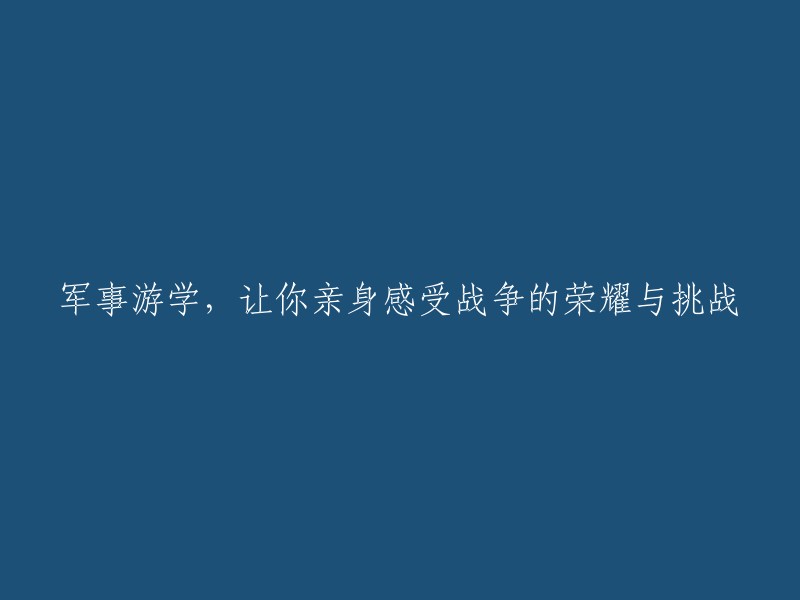《武则天研究》是一部由20余篇论文结集成的论文集,中国历史学者普遍以这种形式出版专著、汇总学术成果。但特别的一点是,这又是一部结构精巧的类传记式论文集,20余篇论文以武则天的生命轨迹为时间线索,串起武则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并且旁及与之有关联的时代背景、学术争议、相关人物等等,构成一副主次分明、层次丰富的初唐至武周政治图景。
孟宪实教授既做隋唐史,也治敦煌吐鲁番学,近年来精力似乎更多投入于后者。在西域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中,他与北大荣新江和人大李肖等诸位先生合作,捧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些不入于大众视野的成就,其实极为重要,是为学术研究奠定基石的工作。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一小拨历史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孟宪实是其中一位。
武则天称帝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的性格和才能。武则天是一个非常有野心和决心的女人,她在政治上非常聪明,能够看到机会并抓住它们。此外,她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能够在文学、音乐和其他艺术领域表现出色。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唐高宗去世后,唐朝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动荡。这种混乱为武则天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她能够利用这种情况来夺取权力。
总之,武则天称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性格和才能。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关陇集团”有着清晰的阐释,“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 ”
但是,孟教授认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他认为,政治权力与具体集团利益的关系并不能准确地对号入座。陈寅恪先生和胡先生对一些具体史实的解释,也并不能很好地佐证自己的观点,有时失之牵强。
关于武则天称帝的深层原因,阶级论只是学界的一种观点。也有学者从性别角度分析,认为北朝女性地位远比中原高,唐朝比较开放,也继承了北朝传统,中原男尊女卑不再那么强烈了,便为女皇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还有一种观点指向制度,认为是士族门阀消亡,皇帝-士大夫政治重新开始,为武则天称帝提供了制度性支持。孟教授认为这两种观点也站不住脚,具体原因兹不赘述。
孟教授认为武则天称帝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事件,应该把观察的视野收束到庙堂之上,单纯以政治的视角来分析。武则天的权力首先是唐高宗赋予的,由于对太子不放心,高宗去世后留下的遗诏中,明确“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后来中宗失言,被武则天废黜,此举获得了大臣的支持。新立的皇帝睿宗并不掌权,“政事决于太后”。此时,武则天已经充分验证了自己的最高权力,并且得到了拥护。接着她便开始着手改朝换代。此时位高权重的中书令裴炎表现出对李唐家族的忠诚从支持武则天跳到反对方...
孟宪实教授认为,武则天称帝虽然有着社会性因素,但本质上是一场宫廷政治斗争。而发生的一切都与前代后代的政权变更大同小异,至于她的性别,在整个权斗过程中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在唐王朝的制度中,是有这样的缝隙存在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武则天的研究史料,局限于几本传统史书,包括正史《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国家档案《唐会要》等。这些史料被历代历史研究者翻来覆去引用、辨析、利用,从各朝史官的微言大义中,从不同记载的矛盾对立处,解读出不同的观点。但是,考古出土的新史料为当代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带来了史书上所没有记载的新信息。
孟教授利用上官婉儿墓志,深入研究了她的爷爷上官仪的生平。他发现,墓志不仅记录了上官仪的传记,还包含了他的上三代、兄弟姐妹等家族信息,为研究家族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结合传世文献后,孟教授对上官仪的历官情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进一步证实了他与唐高宗之间深厚的友谊。
然而,关于上官仪之死的原因,历代研究者仍存在争议。孟教授认为,武则天政治道路上遇到的一次危机——麟德元年的“废后风波”,使得高宗差点废黜武则天的皇后之位。尽管武则天最终保住了地位,但上官仪却因此被杀。孟教授认为,这并非因为上官仪出身关陇集团而反对武则天,而是因为唐高宗在反悔废后决定后,将责任推给了上官仪。
孟教授在研究武则天时代时,持一种非常平视的态度。他不以女皇身份猎奇化,也不以当代流行的性别视角审视,而是把她当作中国封建王朝400多个皇帝之一来看待。在这个过程中,孟教授的最大对手其实是历代史官。中国古代历史始终承担着以古讽今的使命,为了警示当下的帝王,史官多次篡改前代帝王的形象和事迹,为其失败寻找根源。孟教授努力寻找不同史书中的矛盾之处,还原武则天的本来面目,这是20世纪新史学的责任所在。
与传统史学区分善恶、盖棺定论的做法不同,当代历史学家致力于还原事实。正如孟教授所说:“有关武周的历史记载主要来自唐史,文字记载的方向基本是否定和批判。如果说,自我表扬的文字记录表达了一种倾向的话,那么批判文字往往表达了另外一种倾向。作为历史研究,研究者不得不在两种相反的倾向中保持平衡,努力求取历史的真相。”
然而,在分析孟教授的观点时,笔者认为其论证力度存在不足之处。在史书记载尚未涉及的领域,孟教授常常依据普通人的心理和行为来推测,提出他认为更符合逻辑的看法。然而,由于资料的匮乏,这些推断实际上只能被视为假设,用人之常情来论述虽然能满足心理预期,但并不具备强有力的论证力。或许这种急于得出结论的心态,也是作者在讲故事过程中的一种反应。
当然,学者有权利提出任何观点,后人也会对其进行否定、修正或支持。正如孟教授否定了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没有价值。事实上,他的研究启发了几代学者,并将继续影响未来的发展。新史学正是在这种不断探索和修正的过程中,逐步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