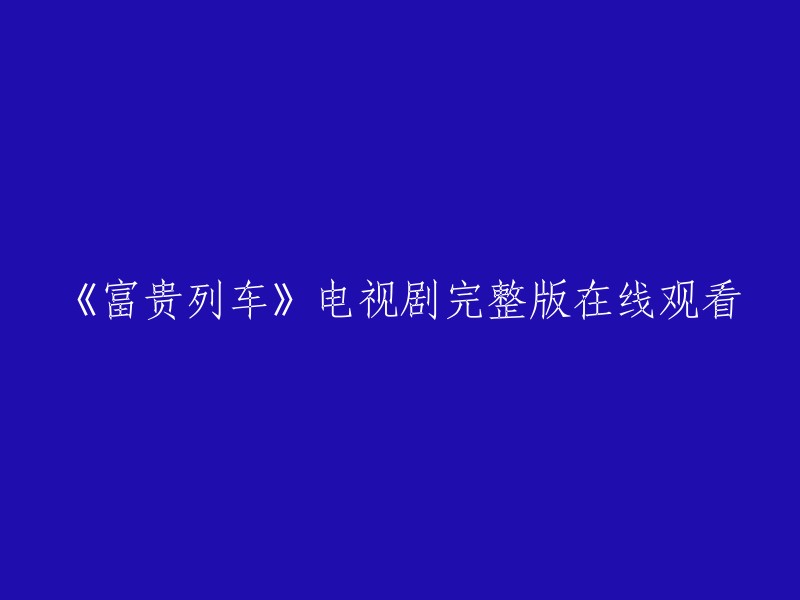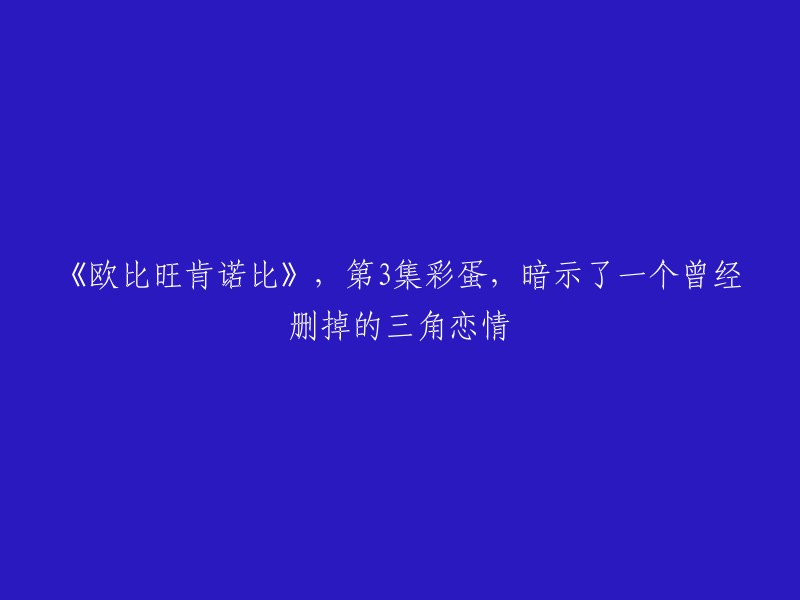方应物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他环顾四周,发现这是上花溪村的一个村民家。窗外传来几声鸡鸣,天色已经蒙蒙亮了。方应物感到非常困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方应物原本是二十一世纪的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硕士高材生,具有明清史专精。然而,在千岛湖旅游时落水后,他竟然穿越时空,变成了这个明代成化年间同名同姓的少年人。这究竟是灵魂附体还是转世?方应物脑海中涌现出大量关于这位明朝少年的记忆碎片,这些信息似乎都属于他。现在,这两个时空的方应物已经合二为一。
在翻阅记忆的过程中,方应物首先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名叫方清之,八年前考中秀才,但在成化七年和成化十年的两次乡试中均未能中榜。于是,他两年前离家游学至今未归。尽管如此,方应物暂时不必担心与父亲见面的问题,因为父亲目前仍处于失踪状态。
方应物对母亲的记忆并不深刻,只知道她在他出生时因难产去世,让他感到十分惋惜。她似乎来自同一个村庄的其他家庭。方应物的父亲有一弟一兄,两人都以务农为生。然而,祖父祖母去世后,他们并未分家,仍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
方应物的父亲是个典型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多年来,他在县学中独自攻读学问,一心追求进步。即便在他没有出远门游学的时候,也很少回家。因此,方应物从小在叔父家里蹭吃蹭喝长大,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这样的生活让他饱受叔父婶娘的抱怨和牢骚。寄人篱下的生活,其中的辛酸难以言表。
回想起前世身为高材生的自己,方应物心里很不舒服。他不想再继续挖掘这段记忆,于是便起身走出房间,想在外面透透气。
走到院子里,方应物发现整个村子都是由黄泥土墙砌成的,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在这个半山坡上的村落里,几十户人家的房子几乎都是这种样子的。只有用砖瓦建造的房子才能算是山村里的大户人家。
方应物回到东厢房内,发现屋里只有三件家具:一张摇摇欲坠的木床、一个掉漆的木柜和一个落了一层土的木桌。凳子却不见了踪影。看来这些家具都是十几年前父亲成亲时打造的。
叹了口气后,方应物重新回到床上躺下,思索着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他必须尽快适应这个新的身份,寻找回到现代世界的方法。而这一切,都将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场冒险。
方应物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样的生活条件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无精打采地站在房间里,这个家简直就是家徒四壁,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掉漆的柜子。
正当他想要把柜子里的东西翻个底朝天时,突然发现了几本书,其中还有一张纸笺。打开一看,原来是他父亲出远门游学前留给他的。纸笺上写着:“由于我儿已经长大,明白事理,家中长房的事务将由我儿代理,事后我会告诉你们详情。希望亲朋好友能给予一些帮助,以此为信。”
方应物不禁摇了摇头,心想这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留下这样的纸条有什么用?他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怎么可能处理好家族的事务?而且现在长房根本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代理。
正在心中嘀咕的时候,听到外面有人叫道:“大哥!去社学吗?”
这声音应该是他叔父家的堂弟方应元的,年纪比他小两岁,大概是来叫他一起去上学。方应物放下心中的烦恼,应了一声,便随同堂弟走了出去。
他们所在的山区地势狭小,不利于大村落聚居,多是零散的小村落和田地分布在平缓的地方。山间有一条河流,名叫花溪,属于浙江西部新安江的小支流,因此有了上花溪村、中花溪村、下花溪村的名称。
实际上,这三个村子非常接近,只是因为地势的原因不能聚集在一起。方应物要去的社学位于中花溪村,社学的屋子是用一处没落的神庙改建而成的。
从八岁开始,方应物就在这个社学里读书识字习文。七年来,他已经背过百家姓千字文,读过四书五经,还学过对偶比兴等文学技巧,甚至还模仿过几篇八股文。
这个社学是由官府发起的,但是平常也需要靠学生的束脩和大户的善款来维持运转。据说去年的头号赞助人就是中花溪村的王昇王大户家。王大户有两个特点,他是花溪两岸这些穷村落里最富有的人,同时也是花溪两岸最有名的美人出生的地方。
一想到王大户家,方应物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丝痛苦的感觉,仿佛他非常不愿意回忆起这段往事。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深入挖掘什么线索,两人已经来到了社学门前。
正当他们要走进去的时候,一名社学杂役却拦住了方应物,带着几分无奈地说:“馆中的老师发话了,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来了。”
方应物微微一愣,疑惑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杂役解释道:“现在已经是四月了,你今年的束脩还没送到,也没有向先生求情过。老师说这是不敬之举,礼尽则恩断,所以你不能再进学堂听讲了。”
尽管方应物被拦住了,但他的堂弟方应元却顺利地进入了学堂。看到这一幕,方应物心中暗想:束脩就是学费吧?他和堂弟两人的束脩一直是叔叔负责送来的,难道今年叔叔只给堂弟送了束脩,却没有给自己送?
方应物感到一阵窝火,因为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叔父会阻止他上学,却还送自家儿子过去。这种厚此薄彼、断人前程的小动作让他无法忍受。在当今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不能读书就意味着失去了上进的道路,只能回家种田或者经商。对于曾经的高材生方应物来说,这无疑是他不愿意接受的。
然而,在社学这里大吵大闹没有用处,方应物决定去叔父家理论。不久后,他按照记忆找到了自己的叔父方清田所在的上花溪村。当他走到自己家的宅院门口时,看到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强壮男子从门口闪出,身穿粗布褐衣,头戴遮阳斗笠,脸面粗糙,显然是终年农事风吹日晒的原因。这个人就是他的叔父方清田,职业是农夫。
方清田手持农具站在院子门口,看上去正准备下田。方应物走上前去质问:“叔父,你为什么截断了我的束脩之礼,却没有告诉我?我一度不明所以。”
方清田早有准备地回答:“这件事是我忘了告诉你,今天想起来的时候你已经去了社学。看你渐渐长大成人,但读书似乎没什么成就,理应为家里分忧。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和我一起下田吧!”
方应物心里一阵震惊,难道要让自己当农民去种田吗?或者说要逼迫自己下田当苦劳力?他顾不得继续质疑叔父阻止自己上学却还送自家儿子过去的小心思,先吃了一惊,仿佛听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前世他作为靠着成绩混迹于校园的优等生,虽然因为孤儿身份不至于饭来张口衣来张手,但也具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优良传统。面朝水田背朝天的田园劳动?抱歉,只在电视上看见过,但从来不是他现实生活中的选项。
方家共有八亩田地,都是祖传的家业。如今长房方清之、二房方清田两兄弟没有分家,故而也就没有详细的划分产权,只算是两家共有。长房方清之一直在县学吃皇粮暂时不用靠田地糊口,但二房一家三口加上方应物一共四口人,生活基本都指望这八亩地,外加若干养蚕收入,日子很紧巴巴。
眼看着大侄子成年,方清田便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南方水田比不得北方,需要精耕细作,八亩地须得用俩个劳力。过去是他们夫妇二人下田,而今年他将主意打到了大侄子身上。这大侄子方应物年纪渐长,越大越能吃,还用得着读什么书?他已经可以充当一个劳力了。如果方应物开始卖两把子力气种田,便不用他那口子浑家下田务农,就能彻底解放出来去养蚕缫丝,多赚点钱财,还能剩下一笔束脩,堪称两全其美。
在极其不情不愿中,方应物被叔父强行硬扯着下了山坡,来到山脚下一方水田边上,田里有的地方已经插好了几排苗。
四月阳光照耀下的水田,波光粼粼,映出方应物俊秀的身影。他手里攥着一把秧苗,站在叔父分给他的半亩地上,犹豫不决。
四月份是本县农家最忙的时候,月初收割春花田并种稻谷,月末插秧。在以农为纲的时代,没有什么比种地更重要的事情了。知县甚至以不能耽误百姓农时为理由,四月份拒绝受理一切百姓的诉讼请求,这叫做息讼期。
叔父塞给方应物一把秧苗,催促道:“农时很紧,你先在这里插秧,我去另一处田地。”方家的八亩地分成两股,没有成片集中在一起。
方应物不服气地说:“那我......”
方清田瞪了他一眼,责骂道:“你这偷懒鬼白歇了多少年,再偷懒连晚间的饭也没有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农民位居第二,是公文纸面上极受重视的高等公民。然而,对于方应物来说,他已经不再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的高材生,而是大明朝的高级公民。
叔父要求他今日完成半亩地的工作量,这是很繁重的劳动。方应物擦了擦汗,第一次感到四月份的阳光如此暴烈。半亩地说起来轻飘飘的,但可能要天天半亩直到农时结束。而且插秧这种农活很苦很累,会把腰折断,也会把脚泡烂,水里还会有蚂蝗......方应物怎么能忍得了这些?
想到这里,方应物举起紧紧攥着秧苗的拳头,忍不住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时代强音:“我不是来种地的!”这一幕被写入了《明史·方应物传》。
不过在此时,只有几位路过的乡邻恰好听到了方应物的不肯向命运屈服的强音,便一齐笑道:“秋哥儿发什么呓语,不想种田还能作甚?除非效仿你的父亲,也考上个秀才,但那可比种田还难!”
秋哥儿是方应物的小名,大概是生于秋季的原因,所以从小就有个秋哥儿的小名。随后又有个人调笑道:“你若与邻村王大户家的小娘子成了亲,到时少不得吃香喝辣,还用和我们一样当泥腿子么。可惜,可惜啊。”
可惜什么?与王家小娘子?刚想到这个名字,方应物的头又痛起来,还是那个潜意识作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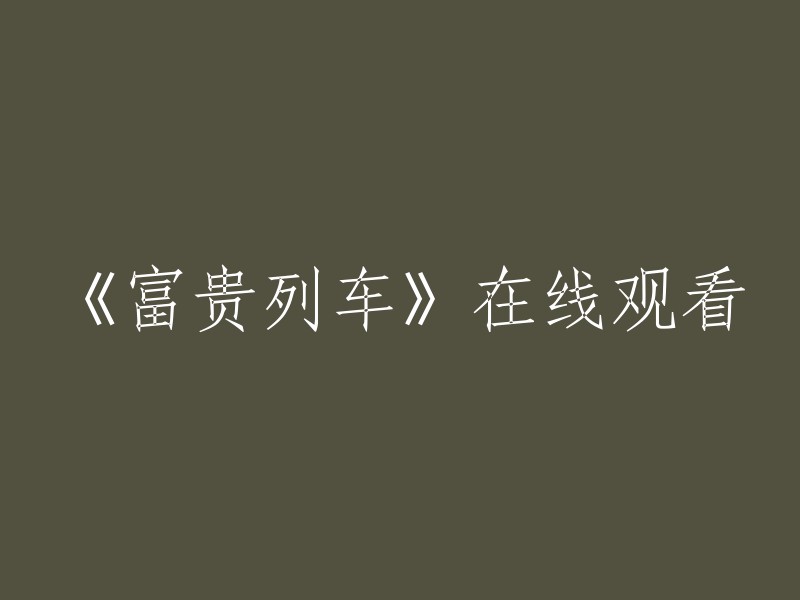
![[百度云] 富贵列车(107分钟完整版)【1986】[BDRip.1080P.x264.AAC.MKV/3.20G][双语字幕]](https://er5-1251572603.cos.ap-shanghai.myqcloud.com/uploads/202409/25/a5490546b3712253.jpg)